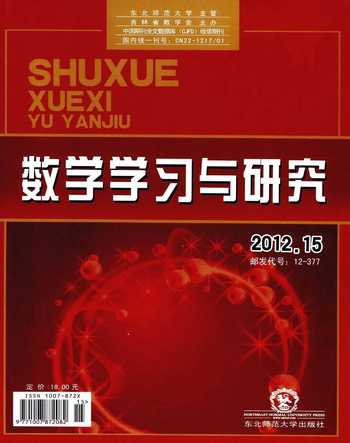偶數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偶數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
《王元論哥德巴赫猜想》168頁介紹:命r(x)為將偶數表為兩個素數之和的變法個數(即偶數內對稱素數的個數),144頁介紹:求解孿生素數的常數。
r(x)≤7。8∏p|xp-1p-2∏p>21-1(p-1)2xlog2x;
∏p>21-1(p-1)2=∏p>2p(p-2)(p-1)2≈0。66。
該公式是陳景潤證明的偶數哥德巴赫猜想上限公式,將7。8改成2就是在23頁介紹的哈代和李特伍德給出的偶數哥猜的近似解公式。122頁、127頁介紹:不超過x的素數個數為π(x)。
π(x)≥x∏si=1pi-1pi;π(x)≥xlogx;x2∏i>1pi-1pi≈xlogx;∏i>1pi-1pi≈2logx。
素數中去掉不滿足“偶數=兩素數和”的素數的篩法:給定偶數除以各個平方根內的奇素數,得到各種非零的余數。如果較大素數除以較小素數得的余數與給定偶數除同一小素數得的余數相同時,偶數減該素數的差數會是合數,將素數中的這種素數去掉,剩下的素數才滿足“偶數-素數=素數”。偶數的因子不含平方根內素數的特種偶數,x=2n,以根內的所有奇素數為參數P,把x數內包含的奇數,全體P數,每P留下(P-1)個數的數量,全體P數,再每(P-1)留下(P-2)個數的數量,或者把x數內包含的奇數,全體P數,每P留下(P-2)個數的數量。就是x數內對稱素數數量。孿生素數的常數內涵素數全縮小成對稱素數的常數與數全縮小成素數的常數的比例:
∏p>2p(p-2)(p-1)2≈∏p>2(p-2)(p-1)∏p>2pp-1≈∏p>2(p-2)(p-1)×logx2≈0。66;∏p>2(p-2)(p-1)≈1。32logx。
素數縮小成對稱素數的常數與數縮小成素數的常數的比例,稱為再全縮小素數的常數。
由連乘積求素數個數的算式與對數參數的素數個數的算式的等式,兩邊同乘以再全縮小素數的常數,得到兩種形式的對稱素數下限的數量。
r(x)下限≈x2∏i>1pi-1pi∏p>2(p-2)(p-1)≈xlogx×1。32logx;兩邊同乘以∏p|xp-1p-2。
r(x)≈x2∏i>1pi-1pi∏p>2(p-2)(p-1)∏p|xp-1p-2≈xlogx×1。32logx∏p|xp-1p-2;p|x表示p整除x。
r(x)≈x2∏i>1pi-1pi∏p⊥xp-2p-1≈(1。32)xlog2x∏p|xp-1p-2;p⊥x表示p非整除x。
r(x)≈x2∏p|xp-1p∏p⊥xp-2p≈2∏p>21-1(p-1)2?xlog2x∏p|xp-1p-2;左邊是哥猜愛好者愛用的連乘積形式的公式,右邊是數學家愛用的對數形式公式,都認可公式是個時有起伏但總是階段增加的函數。青島王新宇發現的∏[(P-2)/(P-1)]≈1。32/log(x),與兩種素數個數公式的乘積,統一了數學家與愛好者的偶數哥德巴赫猜想的下限解的公式。
哥德巴赫猜想的解的公式的創始人哈代曾說過:“如果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天被證明,其方法應該類似于我和李特爾伍德的方法,不是圓法無力,而是我們的分析工具不夠。我們不是在原則上沒有成功,而是在細節上沒有成功。”現在來看看公式的細節:
2∏pi>21-1(pi-1)2≈21∏π(x)∪∞i=2pipi-1∏π(x)∪∞i=2pi-2pi-1≈(logp2max)∏pi>2pi-2pi-1≈1。32,∏pi>1pi-1pi≈1eγlogpmax≈1(0。5)eγlogp2max≈1(0。89)logp2max≥1logx; π(x)≈x2∏π(x)i=2pi-1pi;x數的主體區解公式用的參數的pmax=pπ(x),下限解公式的pmax為任意大或選用pπ(x),公式中∏的下標、上標變化的原因是公式的特殊需要,求x數的主體區的解,參數是“不大于x平方根數的素數”,求x數的較準確的解,參數是“小于x平方根數的素數,可補償主體算式的誤差”,求x數的下界限的解,參數是“大于x平方根數的素數”,求x數的吻合對數形式公式的解,參數是“無窮多的素數”,下標只用》號就可以了,對數參數的公式適合求下限,連乘積公式適合(用計算機)求準確解。因為素數公式缺少平方根內的解,對稱素數公式缺少首尾兩個平方根內的解,各公式參數P特為超過x,又減少了解,還特為采用了分母為大于(0。89)logx的logx參數,多層次減少了解。特為選用不含小素數因子的偶數(讓公式去掉了只增不減的參數),簡稱為下限。特為為了去除公式與實際的差距,又再去掉1。32,進一步減少了解,簡稱為底限。所以公式下限、底限都是可靠解。分析工具的升級:
偶數x用冪數代替,對數用指數代替,若底數不一樣,要用轉換系數。取xlog2x≈e10n102n≈1010nlog10-2n≈100。4342×10n-2n≥100。2171×10n≥1。e10102為104。34-2>102。17,e1001002為1043。4-4>1021。7,e100010002為10434-6>10217。細節成功:公比是10的等比數列的項減去公差是2的等差數列的項,其差數大于被減數的一半。指數減一半等于求平方根數。2011年,青島小魚山的王新宇用冪的指數差運算發現了數學家求解偶數哥德巴赫偶數猜想公式的底限。偶數x大于104。3,r(x)的底限大于x。
底限公式函數y=x/(logx)2在坐標系中的圖像,在x=e2時,有最低點,e2/22≈2。7182/22≈1。84。例:eee2≈15。187。39>2,e2(2)2≈4。12>2,取x=e2m,e2m(2m)2≈21。442×2m22m≈21。442×2m-2m>1,函數往右增大,往左也增大,對數形式的求解偶數哥德巴赫偶數猜想r(x)底限大于一。
x連續擴大成平方數時下限公式的解:
1。32×102m/((log10)×2m)2≈1。32×102m/((5。3)×4m)≈102m-0。6m-0。6。
102-1。2≥100。8,104-1。8>102,106-2。4>103,指數差是公比為2的項與公差為0。6的項的差。偶數x≥104,r(x)公式的下限大于x。
π(x)≥2時,r(x)底限公式大于一的證明:
xlogx≈12(x)xlog(x)≈x×π(x)/2π(x)≥2≥x,xlog2x≈1xxlogx2≈(π(x))2xπ(x)≥2≈(x)2x≥1,π(x)≥2,r(x)公式底限≥1。
xlog2x≈14xlog(x)2≈(π(x))24π(x)≥2≥1,π(x)≥2,r(x)公式底限≥1。
連乘積形式的下限公式大于一的證明:
x2∏π(x)i=2pi-2pi≈x2133557911…Pπ(x)-1pπ(x)≈x2971513…xpπ(x),x≥π(x)。
用兩個x代換x,其中一個x放最大分母上面,其分子及各分子都順延放左邊分母上面使得小于分母參數的各項轉換成全是大于等于一的分數的連乘積,自然有x4,r(x)下限大于一。
哥德巴赫猜想公式誤差問題的解決:數學家認可r(x)誤差為O(loglog(x)/log(x)),取x=eex,Ologlogxlogx≈nen,een(en)2÷nen≈een-n-logn>e1。6>1,e10n(10n)m≈100。4342×10n-mn≥100。2171(10n)。x夠大時,公式中分母的次數遠大于2次也不影響解大于x。由1043。4-21。6≥1021。7,知m=10,有43位數減4位,多減16位,仍大于21位;知m=105,有434位數減6位,多減210位,仍大于217位。r(x)的誤差比loglog(x)/log(x)大,也不影響“解數大于偶數平方根數”。數學家由{奇數r(x)與誤差的比}大于一,認可奇數哥德巴赫猜想證明。現證明了{偶數r(x)與誤差的比}大于一,且誤差大也不影響偶數r(x)大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