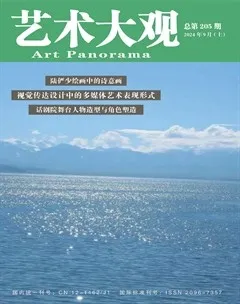牡丹綠葉扶,崖石靜水激
摘 要:拉赫瑪尼諾夫,20世紀(jì)早期俄羅斯音樂(lè)巨匠,以其聲樂(lè)浪漫曲中精湛的鋼琴伴奏著稱(chēng)。當(dāng)前研究多聚焦于其作品的創(chuàng)作技法、音樂(lè)風(fēng)格及情感表達(dá)。然而,關(guān)于其藝術(shù)歌曲與鋼琴伴奏之間的深層關(guān)聯(lián)及藝術(shù)解構(gòu)仍待深入。本文以拉赫瑪尼諾夫藝術(shù)歌曲概覽為始,解析了其聲樂(lè)演唱的藝術(shù)特點(diǎn),探討了鋼琴伴奏的關(guān)鍵技法,進(jìn)而揭示兩者相輔相成的藝術(shù)奧秘。
關(guān)鍵詞:拉赫瑪尼諾夫;藝術(shù)歌曲;鋼琴伴奏;藝術(shù)解析
中圖分類(lèi)號(hào):J62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6-7357(2024)25-00-03
“牡丹綠葉扶,崖石靜水激”,此番意境,正如拉赫瑪尼諾夫音樂(lè)作品中聲樂(lè)與鋼琴伴奏的和諧共生的景象。聲樂(lè)如牡丹般綻放,而鋼琴伴奏則如綠葉般扶持,二者相互依存,共同營(yíng)造出深邃而動(dòng)人的音樂(lè)世界。“聲動(dòng)琴靜相映美,樂(lè)起伴落共纏綿”,聲樂(lè)部分如同崖石般堅(jiān)實(shí),為整首曲子奠定旋律的基石,而鋼琴伴奏則宛如靜水在旁激蕩,為聲樂(lè)部分增添和聲色彩。這種聲樂(lè)與鋼琴的完美結(jié)合,旋律與和聲的細(xì)膩交織,正是拉赫瑪尼諾夫藝術(shù)歌曲的精髓所在。
一、聲樂(lè)琴音共鳴:拉赫瑪尼諾夫藝術(shù)歌曲概覽
(一)琴聲悠揚(yáng)初展露,歌曲濫觴顯才情
俄羅斯作曲家謝爾蓋·瓦西里耶維奇·拉赫瑪尼諾夫(Sergei Vasilievich Rachmaninoff,1873—1943)生于19世紀(jì)末的俄羅斯,此時(shí)歐洲音樂(lè)正經(jīng)歷從浪漫主義向現(xiàn)代主義的過(guò)渡。然而,他選擇堅(jiān)守俄羅斯民族音樂(lè)傳統(tǒng),創(chuàng)作出了獨(dú)具特色的藝術(shù)歌曲。俄羅斯廣袤的疆域、多樣的民族文化以及動(dòng)蕩的歷史命運(yùn),對(duì)他的音樂(lè)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中充滿(mǎn)了對(duì)祖國(guó)的深情和對(duì)人生的深刻思考,展現(xiàn)出憂(yōu)郁而內(nèi)省的藝術(shù)氣質(zhì)。拉赫瑪尼諾夫的藝術(shù)歌曲創(chuàng)作始于1890年,他為萊蒙托夫(Mikhail Yurievich Lermontov)的詩(shī)歌譜寫(xiě)了《在修道院門(mén)前》(《Уворотобителисвятой》)。同年,他又創(chuàng)作了《我什么也不會(huì)告訴你》(《Яничегонескажутебе》)和《我的心,你再次跳動(dòng)了》(《Сердцемоё,тысновазабилось》),并將這些作品編為《三首浪漫曲》(Op.4),標(biāo)志著他在藝術(shù)歌曲領(lǐng)域的初步探索。在這一時(shí)期,他深受柴可夫斯基(PyotrIlyich Tchaikovsky)和格林卡(Mikhail Ivanovich Glinka)的影響。1893年,他完成了《六首歌曲》(Op.8),其中包括《夢(mèng)》(《Сон》)和《晨》(《Утро》),這些作品以?xún)?yōu)美的旋律與深情的表達(dá),奠定了他在藝術(shù)歌曲領(lǐng)域的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深受俄羅斯文學(xué)巨匠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ch Pushkin)、托爾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y)和萊蒙托夫的影響,多取材于俄羅斯著名詩(shī)人的詩(shī)歌作為歌詞,使音樂(lè)更具文學(xué)性。拉赫瑪尼諾夫的早期作品體現(xiàn)了俄羅斯藝術(shù)歌曲的發(fā)展趨勢(shì),鋼琴伴奏逐漸從簡(jiǎn)單的和聲支持轉(zhuǎn)向更為獨(dú)立的藝術(shù)表達(dá),與聲樂(lè)部分形成了深度的對(duì)話。他的音樂(lè)融合了俄羅斯民族民間音樂(lè)的元素,旋律中常見(jiàn)俄羅斯傳統(tǒng)調(diào)式和音階的影子,這一點(diǎn)也印證了他于俄羅斯民族文化的深刻認(rèn)同與由衷熱愛(ài)[1]。
(二)歲月沉淀精技藝,琴歌交融映心聲
20世紀(jì)初,拉赫瑪尼諾夫的創(chuàng)作進(jìn)入了黃金時(shí)期,他的藝術(shù)歌曲在浪漫主義情懷的驅(qū)動(dòng)下,風(fēng)格更加多樣化,表現(xiàn)手法也日臻完善。1902年,他在與表妹娜塔莉亞·薩廷娜(Natalia Satina)結(jié)婚后,創(chuàng)作了《十二首歌曲》(Op.21),其中第五首《丁香花》(《Сирень》)以細(xì)膩的旋律和絢麗的鋼琴伴奏,描繪了春日丁香盛開(kāi)的美景。鋼琴伴奏運(yùn)用了琶音和音型的變化,營(yíng)造出輕柔而浪漫的氛圍。這一時(shí)期,豐富的旅行經(jīng)歷也為其作品增添了東方色彩,拉赫瑪尼諾夫善于融合俄羅斯民族音樂(lè)元素和外來(lái)風(fēng)格,使作品更具獨(dú)特魅力。1906年,他完成了《十五首歌曲》(Op.26),其中《悲歌》(《Элегия》)和《基督復(fù)活節(jié)》(《Христосвоскрес》)等作品,表達(dá)了他對(duì)人生、宗教和社會(huì)的深刻思考。鋼琴伴奏在這些作品中更加突出,采用了復(fù)雜的和聲進(jìn)行和多變的節(jié)奏,增強(qiáng)了音樂(lè)的戲劇性。1912年誕生的《十四首歌曲》(Op.34)中,最后一首《練聲曲》(《Вокализ》)是一首無(wú)詞歌,純粹依靠聲樂(lè)旋律和鋼琴伴奏的交織,傳達(dá)出深邃的情感,成為聲樂(lè)藝術(shù)中的經(jīng)典之作。1916年,他的最后一組藝術(shù)歌曲《六首歌曲》(Op.38)問(wèn)世,其中第三首《雛菊》(《Маргаритки》)和第四首《捕鼠人》(《Крысолов》)風(fēng)格新穎,和聲大膽,展現(xiàn)了他對(duì)現(xiàn)代詩(shī)歌的理解和音樂(lè)語(yǔ)言的創(chuàng)新[2]。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不僅繼承了前輩的創(chuàng)作手法,更融合了他獨(dú)特的民族性和敘事性,使其藝術(shù)歌曲達(dá)到了藝術(shù)上的巔峰。
二、綠葉扶花之韻:聲樂(lè)演唱的藝術(shù)解析
(一)旋律細(xì)膩塑情感,宣敘詠嘆融一體
拉赫瑪尼諾夫的藝術(shù)歌曲以細(xì)膩的旋律處理和深刻的情感塑造而著稱(chēng),他在作品中巧妙地融合了宣敘調(diào)和詠嘆調(diào)的元素,創(chuàng)造出獨(dú)特的聲樂(lè)表達(dá)方式。旋律不僅是音樂(lè)的主線,更是情感的載體,細(xì)致地刻畫(huà)出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和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例如,在《別再唱了,美人》(Op.4No.4)中,拉赫瑪尼諾夫以宣敘調(diào)的手法開(kāi)始,全曲以升f小調(diào)寫(xiě)成,旋律線條采用“旋律音相鄰重復(fù)”的方式展開(kāi),音程以小二度和大二度為主,體現(xiàn)主人公內(nèi)心的憂(yōu)郁與渴望。隨著音樂(lè)的發(fā)展,旋律逐漸進(jìn)入詠嘆調(diào)的抒情表達(dá),音域擴(kuò)大,情感愈加濃烈。歌曲中運(yùn)用基音環(huán)繞的技巧,即圍繞主音進(jìn)行裝飾,使旋律更加豐富和富有表現(xiàn)力。在高潮部分,旋律出現(xiàn)大跳上行,通過(guò)音程的突然擴(kuò)大,強(qiáng)化了情感的爆發(fā)力。演唱者需要準(zhǔn)確把握從“pp”(極弱)過(guò)渡到“f”(強(qiáng))的力度變化,以及速度上的細(xì)微調(diào)整,才能充分展現(xiàn)作品的情感層次。再如,《春潮》(Op.14No.11)是拉赫瑪尼諾夫最著名的藝術(shù)歌曲之一,詞作者為費(fèi)奧多爾·丘特切夫。歌曲描繪了冰雪消融、春潮涌動(dòng)的景象,象征新的生命和希望。鋼琴前奏以傳統(tǒng)分解和弦的方式展開(kāi),并加入了半音下行的音型,營(yíng)造出春水奔騰的動(dòng)態(tài)畫(huà)面。聲樂(lè)部分的旋律富有節(jié)奏感,運(yùn)用了曲首冠音配合正三和弦音,開(kāi)篇以強(qiáng)有力的音符引入主題。演唱者需要在聲音上體現(xiàn)力度的變化,兩次從“pp”過(guò)渡到“f”,表現(xiàn)春潮由靜到動(dòng)的過(guò)程。旋律中頻繁的音階下行和大跳上行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歌曲的戲劇性和情感張力。在第12小節(jié),鋼琴伴奏在五音的重屬和弦上重復(fù)三連音下行,直接推動(dòng)音樂(lè)走向高潮,展現(xiàn)勝利的信號(hào)。
(二)字音相映繪聲色,伴奏和聲共成輝
拉赫瑪尼諾夫通過(guò)精妙的旋律和和聲處理,使歌詞的字音與音樂(lè)相映成趣,營(yíng)造出獨(dú)特的聲樂(lè)效果。同時(shí),鋼琴伴奏不僅為聲樂(lè)部分提供支持,更與之共同構(gòu)建完整的音樂(lè)形象。在《這里好》(Op.21No.7)中,歌詞描繪了寧?kù)o美麗的大自然景象,旋律線條簡(jiǎn)潔流暢,緊密貼合俄語(yǔ)的語(yǔ)音和重音。拉赫瑪尼諾夫通過(guò)精確的音符時(shí)值和節(jié)奏安排,使每個(gè)字音都能在音樂(lè)中得到充分表達(dá)。演唱者需要關(guān)注俄語(yǔ)的發(fā)音特點(diǎn),準(zhǔn)確處理重音和輕音,使聲音與旋律融為一體。鋼琴伴奏采用了柱式和弦的手法,以和弦形式為聲樂(lè)部分提供支撐,同時(shí)營(yíng)造寧?kù)o祥和的氛圍。和聲進(jìn)行中運(yùn)用六和弦、七和弦以及延伸和弦等豐富的色彩和弦,以增加音樂(lè)的層次感。鋼琴的音色需控制在“pp”到“mp”之間,與聲樂(lè)部分的“p”力度相匹配,達(dá)到和諧統(tǒng)一的效果。在《夢(mèng)》(Op.8No.5)中,拉赫瑪尼諾夫通過(guò)復(fù)雜的和聲和精細(xì)的鋼琴伴奏,描繪出夢(mèng)幻般的意境。鋼琴部分運(yùn)用半音下行的和聲進(jìn)行以及分解和弦的伴奏音型,營(yíng)造朦朧神秘的氛圍。演唱者需要注意歌詞的發(fā)音,尤其是元音的處理,使聲音具有連貫性和流動(dòng)性,與鋼琴的旋律線條相呼應(yīng)。《孤獨(dú)的人》(Op.21No.6)中,鋼琴伴奏以低沉的音域和沉重的和聲,運(yùn)用和聲小調(diào)的進(jìn)行和切分音的節(jié)奏,烘托出孤寂壓抑的情感氛圍。
三、靜水激石之合:鋼琴伴奏的互動(dòng)演繹
(一)琴音涌動(dòng)映潮聲,指尖跑動(dòng)展技藝
以拉赫瑪尼諾夫的藝術(shù)歌曲《春潮》(Op.14No.11)為例,鋼琴伴奏需要以其高超的演奏技巧,生動(dòng)地描繪春天冰雪消融、河流奔騰的景象。演奏者面對(duì)復(fù)雜的半音階、八度和弦、琶音等技術(shù)挑戰(zhàn),需要通過(guò)慢速練習(xí),鞏固指法,建立肌肉記憶。指法選擇上,應(yīng)遵循舒適性和連貫性的原則,避免不必要的跳躍。手指的觸鍵應(yīng)根據(jù)音樂(lè)的需要,選擇指尖或指面觸鍵,控制下鍵速度和深度,以獲得理想的音色。
樂(lè)曲開(kāi)篇,鋼琴前奏在第1至第4小節(jié),以連續(xù)的八分音符琶音展開(kāi),右手在高音區(qū)進(jìn)行快速的半音上行音型,左手以傳統(tǒng)的分解和弦支撐。這種半音階的上行模進(jìn),模擬了冰雪融化后流水逐漸加速的感覺(jué),仿佛聽(tīng)見(jiàn)春水潺潺。演奏者在此需要具備手指的獨(dú)立性和靈活性,右手的指尖需準(zhǔn)確觸鍵,手腕放松,確保音符清晰而連貫。在第8小節(jié),音樂(lè)進(jìn)入第一個(gè)高潮,力度從“pp”(極弱)逐漸加強(qiáng)至“f”(強(qiáng)),左手出現(xiàn)了降六級(jí)和弦,右手以半音上行的音階推動(dòng)音樂(lè)的發(fā)展。這里的半音階進(jìn)行要求演奏者對(duì)指法的選擇極為謹(jǐn)慎,通常采用舒適性和連貫性的指法原則,如使用“1-2-3-1-2-3”或“1-3-1-3-1-3”的指法模式,以確保快速而準(zhǔn)確的彈奏。第12小節(jié),鋼琴伴奏在五音重屬和弦上,右手以三連音下行的方式,直接將樂(lè)曲推向高潮,象征著春潮的洶涌澎湃。演奏者需注意和弦的準(zhǔn)確性,手指間配合緊密,手腕保持靈活,下鍵速度要快而有力,以獲得飽滿(mǎn)的音色。這里的力度標(biāo)記為“ff”(極強(qiáng)),要求演奏者在保持力量的同時(shí),控制音色不至于生硬。第18小節(jié),再次回到核心動(dòng)機(jī),力度標(biāo)記為“mf”(中強(qiáng)),通過(guò)柱式和弦的運(yùn)用,使春天的氣息更加濃烈。柱式和弦的彈奏需要手掌保持自然的拱形,手指堅(jiān)挺,手腕以支撐點(diǎn),手臂放松,確保和弦的齊奏和音色的統(tǒng)一。
從第22小節(jié)開(kāi)始,音樂(lè)調(diào)性轉(zhuǎn)為E大調(diào),鋼琴伴奏回到潮水流動(dòng)的旋律,右手以流暢的分解和弦和琶音,與人聲的長(zhǎng)音部分相互補(bǔ)充。這里的伴奏再次強(qiáng)調(diào)手指的靈活性,尤其是在快速的音符跑動(dòng)中,手指的獨(dú)立性決定了音樂(lè)的連貫性。演奏者應(yīng)采用指面觸鍵的方法,手指自然彎曲,觸鍵點(diǎn)集中在指腹,手腕保持平穩(wěn),以獲得柔和而富有歌唱性的音色。在第28小節(jié),柱式和弦再次出現(xiàn)于第二段的鐘聲主題中,表達(dá)了對(duì)春天的贊美和期待。演奏者需要掌握好力度,從“f”過(guò)渡到“ff”,手指在和弦的彈奏中,要保持放松,以獲得明亮而有彈性的音色。手腕的靈活性在此非常重要,避免因過(guò)度用力而導(dǎo)致音色生硬。樂(lè)曲的尾聲部分,從第34小節(jié)開(kāi)始,鋼琴通過(guò)模進(jìn)式的連續(xù)三和弦下行展開(kāi),描繪了春潮漸行漸遠(yuǎn)的意境。這里的八度和弦要求演奏者具備良好的手指張力和手腕的彈性。手掌需保持自然的弧度,手指間距適當(dāng),手腕以小幅度的上下運(yùn)動(dòng)支撐手指下鍵,確保音符的清晰和連貫。演奏者在此應(yīng)注意突出高音聲部的旋律線條,保持音量的均衡。
(二)聲伴交織塑春景,主導(dǎo)平衡共演繹
在《春潮》中,鋼琴伴奏與聲樂(lè)部分緊密互動(dòng),共同塑造出春天萬(wàn)物復(fù)蘇的美麗畫(huà)面,鋼琴與人聲在作品中呈現(xiàn)出從屬、平衡、主導(dǎo)三種關(guān)系。
在樂(lè)曲的開(kāi)篇(第1至第7小節(jié)),鋼琴伴奏處于從屬關(guān)系。鋼琴以分解和弦和琶音的音型,營(yíng)造出春水初動(dòng)的氛圍,力度標(biāo)記為“pp”到“p”,音色輕柔。人聲進(jìn)入后,唱出主要的旋律線條,鋼琴在下方提供和聲支撐。演奏者需控制音量和觸鍵力度,手指以指面觸鍵,手腕放松,確保不蓋過(guò)人聲的音量,使鋼琴成為人聲的有力襯托。從第12小節(jié)開(kāi)始,鋼琴與人聲進(jìn)入平衡關(guān)系。音樂(lè)進(jìn)入第一個(gè)高潮,力度增強(qiáng)至“f”,人聲和鋼琴共同推動(dòng)音樂(lè)的發(fā)展。鋼琴伴奏的織體變得豐富,右手進(jìn)行快速的半音階上行,左手以和弦支撐,營(yíng)造出激動(dòng)人心的氛圍。演奏者在此需與人聲保持音量和情感上的協(xié)調(diào),手指觸鍵有力而不生硬,手腕靈活,確保與人聲的平衡。指法選擇上,應(yīng)確保手指的連貫性,快速音符的準(zhǔn)確性,以及與人聲的同步。在第20小節(jié),鋼琴伴奏逐漸占據(jù)主導(dǎo)關(guān)系。此時(shí),鋼琴以強(qiáng)有力的八度和弦和柱式和弦推進(jìn),力度標(biāo)記為“ff”,人聲的旋律與鋼琴的旋律線條相互獨(dú)立,但彼此呼應(yīng)。鋼琴在這里展現(xiàn)出宏大的音響效果,象征春潮的洶涌澎湃。演奏者需充分發(fā)揮技巧,手掌堅(jiān)挺,手腕以支撐點(diǎn),手臂放松,彈奏出飽滿(mǎn)而有力的音色。手指在八度和弦的彈奏中,要確保音準(zhǔn)和力度的均衡,突出鋼琴的主導(dǎo)地位。
從第22小節(jié)開(kāi)始,鋼琴與人聲再次回到平衡關(guān)系。音樂(lè)情緒稍有緩和,調(diào)性轉(zhuǎn)為E大調(diào),鋼琴伴奏以流動(dòng)的分解和弦和琶音,描繪春水奔流不息的畫(huà)面。人聲以長(zhǎng)音和抒情的旋律,與鋼琴的旋律線條相互補(bǔ)充。演奏者需在音量上控制在“mf”到“f”之間,手指觸鍵柔和,手腕保持穩(wěn)定,與人聲形成和諧的音響效果。在樂(lè)曲的尾聲部分(第34小節(jié)以后),鋼琴伴奏再次占據(jù)主導(dǎo)位置。尾聲以連續(xù)的三和弦下行模進(jìn)展開(kāi),力度保持在“mf”至“f”,表現(xiàn)春潮漸行漸遠(yuǎn)的意境。人聲已停止演唱,鋼琴獨(dú)自完成樂(lè)曲的收尾。演奏者在此需展現(xiàn)高超的技巧,八度和弦的彈奏要求手指的獨(dú)立性和手腕的靈活性,手掌保持自然的拱形,手腕以小幅度運(yùn)動(dòng)支撐,確保音符的清晰和連貫。
四、結(jié)束語(yǔ)
拉赫瑪尼諾夫的藝術(shù)歌曲,以深刻的情感表達(dá)、細(xì)膩的旋律處理和精湛的鋼琴伴奏,構(gòu)筑了獨(dú)具特色的音樂(lè)世界。聲樂(lè)部分如牡丹綻放,絢麗多姿,鋼琴伴奏則如綠葉扶持,精妙襯托。正如“崖石靜水激”,拉赫瑪尼諾夫的音樂(lè)在聲與琴的交織中激蕩出無(wú)限的情感與意境,給人以精神啟迪,給藝術(shù)以不朽的靈魂。
參考文獻(xiàn):
[1]蔡德智.拉赫瑪尼諾夫藝術(shù)歌曲伴奏之和聲研究[J].黃河之聲,2024(17):52-55.
[2]楊倩.美從“悲”中來(lái)——淺議拉赫瑪尼諾夫藝術(shù)歌曲創(chuàng)作的悲劇情懷[J].美與時(shí)代(下),2024(05):62-64.
作者簡(jiǎn)介:李瑞強(qiáng)(1994-),男,貴州六盤(pán)水人,博士,從事鋼琴伴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