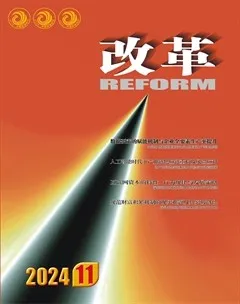數字治理革命與新型生產關系:基于技術、組織、制度三重視角的分析
摘 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但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性及其內涵尚未得到充分討論。以索洛提出的生產率“悖論”為分析起點,指出技術革命不會自動轉變為以全要素生產率普遍提升為標志的產業革命,二者缺口需要通過在各個層面改變利益相關方合作關系的治理革命來彌補。治理革命主要包含技術路線、組織結構、制度規則三個維度的多重可能性探索,這在當前又主要體現為數字技術多重路線的演化選擇、“數字后福特”作為組織變革的迭代進化、包容性和開放性數字制度的探索變遷。它們共同構成數字治理革命的基本內涵,也是數字革命時代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內涵。
關鍵詞:新型生產關系;新質生產力;治理革命;數字治理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543(2024)11-0028-12
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雖然在當下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已經得到普遍認可,相關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但新型生產關系的改革與重塑尚未得到全面闡釋。
值得指出的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適應并非自然形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技術革命并不必然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而能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的技術革命,卻又往往會遲滯很長時間才會顯現這一效應。羅伯特·索洛在1987年面對當時正興起的計算機革命時,便提出過著名的“索洛悖論”,指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計算機,但就是沒有在生產率統計數據中”[1]。事實上,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計算機革命,直到21世紀初才體現出較明顯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其效果顯現遲滯了40年[2]。索洛所描述的生產率悖論,對于當代中國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技術革命到能夠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的產業革命,二者之間的缺口正是由被稱為“治理革命”的生產關系改革與塑造。歷史上的數次技術革命,都需要通過治理革命才能走向產業革命,但同時諸多因素又會限制并約束治理革命的發生,進而延遲從技術革命向產業革命的轉化。于是,探索作為治理革命的“新型生產關系”,便成為在當前彌合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缺口的關鍵之一,而這也構成本文的主要討論內容:新質生產力發展為何需要生產關系的革新?新型生產關系應該包含哪些內容?未來又應該通過哪些方面的持續改革以塑造新型生產關系?
一、生產率“悖論”:從技術革命到產業革命的缺口
索洛關于生產率“悖論”的觀點形象表達了彼時人們對于技術革命能否開啟產業革命,進而持續提升生產率的疑慮。在當時,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方面,技術革命將帶來新機器、新設備的持續投入,而這理應反映為統計數據中的生產率提升效果;另一方面,經濟形態正在從產品經濟(goods economy)邁向服務經濟(services economy),“信息”作為生產要素的價值開始提升,而能夠釋放信息生產要素價值的信息技術革命理應體現出產業催化作用[3]。但遺憾的是,在經歷1948—1973年生產率的高速增長之后,美國開始進入長時間的低增長階段,信息技術革命的前述兩方面積極作用并未能有效體現出來,由此招致索洛的質疑。
在索洛“悖論”提出之后,一些學者從不同維度對此作出了回應。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分為以下四類:第一,技術革命存在“滯后效應”,即計算機革命對于生產率的促進作用需要持續一段時間才能發生[4];第二,生產率的評估指標不夠完善,適配傳統經濟形態的生產率測度指標不一定能全部涵蓋技術革命下的新經濟形態[5];第三,技術革命帶來的經濟增長可能被高估,其更多體現為較為平緩的對數增長而非較為明顯的指數增長,因而難以在短期內看到技術革命的促進效應[3];第四,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等差異會影響技術革命對于生產率的促進效應,尤其是在中微觀層面,技術存量水平、勞動力結構、管理過程特征等都將影響計算機革命之于生產率提升的促進效應[6]。
概括而言,上述觀點大致可總結為兩種分析視角:前三類觀點關注技術革命向產業革命演化的機制復雜性,認為技術革命必將引發產業革命,但也承認這一過程可能緩慢或難以被現有指標所識別;第四類觀點并不假定技術革命引發產業革命的必然性,且認識到了環境因素對該過程的復雜影響。本文的分析視角更接近第四類觀點,試圖通過揭示環境影響的復雜過程,在理論上回應伴隨生產力演化而出現的生產關系變遷規律。在此意義上,本文將分析對象從技術革命、產業革命這些體現“生產力”內涵的要素,轉向制度、組織、管理等體現“生產關系”內涵的要素,并在這種研究視角轉向中,試圖界定當前數字技術與產業革命背景下的“新型生產關系”的內涵和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第四類觀點認識到了環境影響的重要性,但沒有明確指出究竟哪些環境因素需要被納入考量,而這些因素又可以被概括為哪些維度以構成邏輯自洽的理論框架。針對此問題的探索,引導我們進一步回溯至更遠的技術革命史。事實上,以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的發明為起點并在隨后拉開的信息技術革命并非人類歷史上唯一的技術革命“黃金時代”,19世紀后半葉同樣見證了人類技術革命的集中迸發:1844年發明電報、1876年發明電話、1879年發明內燃機、1882年建立第一座電站,直到1886年發明第一輛汽車,電氣革命在彼時徐徐拉開其序幕,并成為繼工業革命之后的又一個技術革命“高峰”。從生產率統計數據來看,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同樣經歷了緩慢的增長過程,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達到了頂峰[2]。換言之,在電氣革命作為技術革命爆發50年后,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主要表征的產業革命才“姍姍來遲”。那么,在這“遲到”的50年里,究竟發生了什么變革,才最終釋放出技術革命的潛在生產力?
產業史研究對此作了詳細而充分的記錄,以下四方面的重要改革可被視為關鍵因素[2]:第一,福特在1913年引入流水線作業,其在創設福特制時并沒有將其申請專利或“密而不宣”,而是將這一組織革命開放給所有行業,讓其他行業都能模仿乃至復制這一全新的勞動組織形式;第二,20世紀20年代美國開始建立標準系統,統一了規格迥異的同類型產品,同時也使得沒有生產經驗的公司能夠比較容易地進入已被標準化的產品領域,從而極大地改進了工業生產效率;第三,美國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了“羅斯福新政”,同期通過了《國家勞資關系法案》(即《瓦格納法案》),在確認工人有組建工會權利的同時,也奠定了勞資協商的制度基礎;第四,20世紀40年代受戰時生產壓力“倒逼”影響,“干中學”等一系列管理經驗被總結和提出,管理者和勞動者相互學習、利益捆綁,極大提升了勞動效率。
由此梳理不難發現,1900—1950年,正是在福特制作為勞動組織變革、標準系統建立作為產業協同變革、《瓦格納法案》作為勞資關系變革、“干中學”作為管理變革這一系列變革基礎上,電氣革命之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和促進作用才完全體現出來,而這一系列變革事實上都可被涵蓋在“治理革命”的范疇之下。
在此意義上,“治理革命”的內涵可被定義為各個層面利益相關方形成特定合作關系的總和。例如,福特制是個體層面勞動者之間形成分工合作關系的一種模式,標準系統是跨組織層面不同企業之間就產品規格達成的合作,《瓦格納法案》和“干中學”均是組織層面資方與勞動者就收益分配或勞動過程管理達成合作共識的制度安排。在不同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背景下,治理革命的具體表現形式可能不同,但其促進技術革命向產業革命轉換的重要作用是相似的。
由此,技術革命經由治理革命實現產業革命的基本邏輯得以呈現,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塔瑪拉·洛西安2017年出版的《法律與國家財富》一書中對三者之間的關系也有過類似表達。洛西安指出,每個歷史時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以實現生產革命的關鍵在于“改造自然”與“改造人類合作方式”這兩類活動的結合[7]。在本文語境下,“改造自然”活動可被理解為“技術革命”,而“改造人類合作方式”即“治理革命”,二者如果能夠很好結合,就能創造出所在時代的“產業革命”。在亞當·斯密時代,具體表現為建立在技術分工基礎上的流程式生產(如“別針工廠”)[8];在電氣革命時代,進一步表現為建立在福特制、標準制、勞資合作、“干中學”等系列變革基礎上的制造業輝煌;在數字時代,“治理革命”究竟意味著什么,是需要進一步探索和挖掘的重要議題。接下來,本文從技術、組織、制度三個方面的內在復雜性入手,揭示思考當代治理革命的視角和方向。
二、治理革命的三重復雜性:技術、組織與制度的多重可能性
技術變遷背景下的治理革命,是利益相關方合作關系在新技術框架下的重要調整。盡管我們不能預先確定治理革命的具體內涵,但仍然可以從已有理論和實踐的梳理中找到理解治理革命的分析框架,其主要體現在技術、組織、制度三個維度上。
(一)多重技術路線視角下的治理革命
技術路線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利益相關方影響技術路線選擇演化的過程,是理解治理革命復雜性的第一重維度。在技術變遷背景下理解治理革命,技術似乎應是一個外生變量而不能被視為治理革命的內涵,但這一觀點恰恰忽視了技術本身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多重技術路線之間的競爭演化關系。“技術路線”概念是相對于將技術方案視為“最優、唯一、必然”的決定論觀點而言的,其更強調針對相同的功能性問題,事實上存在多條解決路徑,而不同路徑的差異不僅體現于技術本身層面,其往往還反映了解決問題的不同價值理念,以及評價技術績效的不同指標。
國際象棋算法的演化歷史便清晰體現了技術路線的多樣性及其選擇過程的復雜邏輯[9]。國際象棋算法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是人工智能領域研究的核心和焦點議題,美國數學家、信息論創始人克勞德·香農認為該領域的相關探索大體可以總結為兩條路線:A路線通過“蠻力”計算方式窮盡所有策略以尋找最優解,而B路線強調以啟發式邏輯識別對弈局勢以聚焦最有可能獲勝的特定策略展開分析。以1997年IBM“深藍”戰勝卡斯帕羅夫為標志性事件,A路線成為彼時業界的共同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A路線就是“最優選擇”,過于迎合比賽規則反而影響了人工智能基礎研究的進展,聚焦于特定比賽目標的研究導向使得A路線算法很難被應用于其他領域,這也導致在戰勝卡斯帕羅夫之后,“深藍”的價值便非常有限,而開發它的部門也逐漸被解散。但為什么A路線彼時會被選擇呢?技術史的研究認為兩方面因素至關重要:為爭取研究資助而將獲得比賽勝利視為最高目標;為更充分利用計算機硬件性能提升所帶來的發展紅利。這兩方面因素與A路線、B路線在技術層面的比較優勢都沒有必然聯系,它們反映了彼時研究者之間以及研究者與研究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10]。
換言之,如果我們意識到多重技術路線的可能性,那么不同技術路線間的選擇、演化便自然進入治理革命的討論范疇。為釋放技術革命的潛在生產力,我們首先需要考慮的可能不是功能層面核心技術瓶頸的突破,而是究竟哪條技術路線能夠真正或充分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如何選擇并推動該條技術路線的發展——而這兩個問題無疑都涉及資助者、研究者、應用者等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合作關系的調整和變革。
多重技術路線視角的復雜性還不限于此,更大的挑戰在于不確定性,即我們事實上并不能提前預知哪條技術路線具有提升生產率的潛力。利益相關方對不同技術路線的預測、比較、選擇,同樣受到主觀經驗的影響。正如斯特雷文斯以科學史上的諸多著名案例為例所指出的,近現代科學并不能完全擺脫“主觀世界”的影響[11]。面對這種復雜性,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羅伯特·昂格爾進一步對“技術”概念作出了重新定義,認為應該將技術理解為“人類改造自然的實驗與改造人類合作方式的實驗的結合點的實體化體現”[12]。換言之,“技術”并不僅僅只是改造自然的工具,也指涉改造人類合作方式的內涵,如何將二者更好地結合才是判定“技術”先進性的重要標準。如果認識到“技術”概念同樣涉及不同利益相關方合作關系的調整和重構,那么就更容易理解為何治理革命需要考慮多重技術路線的分析視角了。
(二)多重組織結構視角下的治理革命
多重組織結構視角下的治理革命試圖回答的問題在于:技術創新是否必然帶來組織結構變遷?如果是,組織結構變遷的結果是否唯一?如果組織結構變遷存在多重可能性,何種因素又會影響不同結構的演化選擇,而哪一種結構才能釋放技術革命的潛在生產率?
正如在電氣革命歷史回顧中提到的,從1886年第一輛汽車發明到20世紀50年代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達到頂峰,技術革命到產業革命的演化遲滯了60多年。在這60多年里,首先出現的關鍵性變革是福特制的形成與擴散。在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杰出社會學教授鮑勃·杰索普看來,福特制是包含勞動過程管理、經濟再生產模式、管理范式在內的整體性治理革命[13]。首先,福特制的勞動過程管理是對泰勒主義的繼承,從簡單技術分工走向流水線以實現標準產品的批量生產和規模經濟。其次,福特制在微觀層面的勞動過程管理反映了宏觀層面的經濟再生產模式,這意味著基于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自動增長過程與自我實現邏輯:基于批量生產的規模經濟提升了勞動生產率,相應增長的收入將擴大標準化的消費需求,由此增加的生產利潤將進一步轉化為針對批量生產技術和設備的新投資,從而維系勞動生產率的新一輪提升。最后,支撐福特制的勞動過程管理和經濟再生產模式,需要形成一系列制度規則和社會關系,這又具體涵蓋工資、企業、金融、國家等各個方面。《瓦格納法案》框架下基于雇傭關系的勞資談判體系,就試圖確保工人收入水平能夠隨著生產率的提升而提升,從而穩定市場需求。
福特制構成我們對電氣革命時代產業組織結構的經典描述,而它也締造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超大規模工廠——福特汽車的胭脂河(River Rouge)工廠,但這是否意味著福特制及其所代表的批量生產模式就是電氣革命下唯一的產業組織結構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如果將技術革命進一步追溯至工業革命,我們往往認為福特制及批量生產是工業革命、電氣革命以來的必然選擇。但隨后的研究指出,過多強調英國珍妮紡紗機對降低工人技能要求的作用,以及在此基礎上認為機器大工業必將取代工場手工業的決定性結論,事實上夸大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農業人口眾多的法國,雅卡爾織布機作為另一條不同于英國工業革命、減少城鄉沖突的技術進步的可能道路[14]。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斯·賽伯等人的研究更是指出,自18世紀后半葉工業革命開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同地區產業在接納并實現機器大工業方面都存在較大異質性:美國普遍實現了批量生產,法國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靈活專業化”特征,英國則介于二者之間[15]。所謂“靈活專業化”,是指高技能工人在使用通用機器過程中生產出小批量且多樣化產品的生產模式,其在生產組織層面體現出自組織、分散化、臨時化等特征,這不同于批量生產模式的一體化整合特征[16]。
對技術與產業演化史的上述回溯說明,任何一次技術革命并非唯一決定組織結構變遷的可選項,批量生產模式并非在任何環境下都是最優選擇,“靈活專業化”仍然有其生存空間。但什么因素會決定二者的選擇與演化呢?
一方面,資源稟賦理論認為,生產組織模式的異質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力、資本、市場等生產要素的差異性,充裕的低技能勞動人口(如農業人口向工業的轉移)、穩定的市場需求(如“二戰”后對標準化且低價格產品的龐大需求)都是促進批量生產模式興起的重要原因,而低技能勞動人口的缺乏以及動態變化的市場需求則被視為維系“靈活專業化”生產模式的關鍵。另一方面,管理主義、制度主義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并非外生,而很可能是與生產組織結構相互影響、相互建構的動態過程。換言之,生產組織模式選擇并非完全取決于市場需求,還可能是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制度性因素影響下,作為生產單位的分散主體所作出的策略性應對。就批量生產模式而言,勞動者被視為習慣于投機或搭便車行為的理性“經濟人”主體,因而勞動過程管理的關鍵是“放棄”或者“抑制”勞動者的主體性,轉而建立標準化的作業流程以減少交易成本。與之相比,“靈活專業化”的生產組織模式更多將勞動者視為嵌入特定制度文化的“社會人”,其對于自身技能的榮譽感、對于勞動規范的遵從在很大程度上都將克制投機并促進信任和合作。由此,究竟何種生產組織模式將成為主流,事實上取決于對待勞動者的態度,以及在此基礎上所作出的管理決策[17]。
如果任何一種生產組織結構成為流行或主導都不是因其在生產效率方面的絕對優勢,而更多體現為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制度環境、特定權力關系下的權變選擇,那么我們在任何一次技術革命面前可能都需要對生產組織結構持開放態度。在承認生產組織結構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前提下去理解、比較、選擇能夠釋放技術革命潛在生產力的產業組織結構形式,而這便構成分析治理革命的第二個維度。
(三)多重制度規則視角下的治理革命
在技術革命引發的系列變遷中,制度規則始終是人們關心的重要議題,也是治理革命的必然范疇。但長期以來,兩個方面的常識性觀點束縛了人們對于制度規則多重性的完整認知。
一方面,制度規則往往被視為對技術革命、組織革命的“事后”回應,作為保護性措施用于抵御工業革命推動下的市場擴張對社會生活帶來的侵蝕和風險。在此邏輯下,技術革命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產業或組織變革,往往被認為興起于制度規則的“空白”處,制度規則是其形成大規模影響后才對此作出回應,將其重新納入治理框架之中[18]。這種解釋盡管具有啟發性,但將“技術產業革命”與“制度規則變化”分隔開的思路并不一定符合現實。美國喬治敦大學法律教授朱莉·科恩在《真相與權力之間:信息資本主義的法律建構》一書中提出,制度規則從來沒有離開過技術產業革命的任何一個環節,二者的相互建構才最終推動了生產力的持續演化過程。具體而言,正是因為1996年的《通信規范法》和1998年的《數字千年版權法》建立起對于數字平臺寬泛的“安全港”保護規則,才促進了數字平臺的繁榮和“硅谷”的崛起[19]。在此意義上,制度規則同樣應作為技術革命過程的必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制度規則的多樣性往往沒有得到充分認可和發現,尤其是當技術革命打開人類生產生活更廣闊空間時,制度創新與改革的多重可能性卻被輕視或忽略。知識產權作為人類社會基礎制度規則的演化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長久以來,我們認為知識產權的制度邏輯在于“知識公開”和“生產激勵”二元目標的權衡取舍:通過保證發明者的排他性所有權,使得知識產品成為能夠進行市場交換的“商品”,并因此激勵知識生產者;同時,知識產權的申請需要以公開為前提,并設置保護期限,從而滿足知識公開的社會需求[20]。但是,此種理解事實上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識生產這一人類活動的全部形態:其假定知識生產是建立在物質動機基礎上,并要求以排他權劃定權利邊界,從而支持所有者在生產過程中獲得物質收益并進一步激勵其要素投入。伴隨著數字技術的創新演化,開源軟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形態的興起就是對傳統知識產權制度邏輯的挑戰。具體而言,開源軟件生產過程的關鍵在于開放,但為了防止開源程序員向社群免費公開的勞動成果被別人占有,其同樣要解決投機風險。“左版權(Copyleft)”作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基本內涵在于,其并不強調排他與控制,而是允許后來者的免費使用和再開發、再發布,但同時要求后來者不能將原開源代碼據為己有。由此可知,“左版權”制度事實上更加包容地承認了人類知識生產的多元動機,并通過分離代碼的所有權、使用權、開發權(發布權)而體現全新的生產激勵邏輯[21]。
上述兩方面的理論分析試圖指出制度規則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多重可能性會伴隨技術、產業革命而不斷發展豐富的演化邏輯。在此意義上,技術革命背景下的治理革命理應將多重制度規則納入考慮范疇,以推動技術革命向全要素生產率普遍提升的產業革命方向發展。
三、“技術—組織—制度”框架下理解“新型生產關系”的三重內涵及改革啟示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挖掘治理革命的具體內涵,以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并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沿襲“技術—組織—制度”三維分析框架,這里進一步結合當前時代進展,具體討論新型生產關系的可能內涵。考慮到數字技術在當前技術革命中的代表性和關鍵性地位,這里的分析將圍繞數字治理革命作為新型生產關系核心組成部分的建構與改革展開,而這又具體包括數字技術多重路線的演化選擇、“數字后福特”作為組織變革的迭代進化、包容性和開放性數字制度的探索變遷三方面分析。
(一)數字技術的多重路線及其演化選擇
探索治理革命內涵的第一個維度是理解所處時代技術革命的多重路線,并在此基礎上明晰其演化過程,使時代所選擇的技術路線能夠真正釋放其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積極價值,從而成功轉化為產業革命。盡管我們很難事前預知哪一條技術路線具備此種潛力,但對已發生現實進行反思有利于啟發對于多重技術路線的演化選擇,而這也正是近年來在全球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出現的新現象。
以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的發明為起點,全球數字化轉型進程迄今已逾60年。數字技術、數字業態創新在極大改變人類生產生活形態的同時,也在近些年招致集中批評。以2018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互聯網治理論壇”上發表的“互聯網已經到了轉折點”的講話為標志,全球利益相關方開始普遍反思過往數字化轉型模式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這既體現為數字技術賦能僅限于特定地區、特定產業領域而未普遍擴散至其他國家或其他產業的“孤島悖論”[22],又體現為因數字技術廣泛應用而帶來信任危機、極化危機、民主危機并招致“技術反沖(Techlash)”[23]的“創新悖論”。導致“孤島悖論”“創新悖論”的關鍵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歸結為壟斷型數字平臺的興起及其在權力擴張過程中出現的分化格局。
由此引發的問題在于,為什么數字技術、數字業態的發展會產生壟斷型數字平臺?互聯網誕生之初被賦予去中心化“烏托邦”愿景的數字未來,究竟如何演化為高度集中的數字分化結構?正是出于對這些問題的反思,近年來才同時涌現對于數字技術多重路線的積極探索,典型案例就是萬維網發明人伯納斯-李對于互聯網基礎架構的新實驗[24]。
在伯納斯-李看來,壟斷型數字平臺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萬維網架構設計的疏忽,以網頁為中心的技術架構沒有將應用程序與數據分離開,這便導致用戶數據被分割在不同網頁(其背后是不同公司)而難以開放共享,由此造成“數據豎井(Silos)”現象。“數據豎井”使得商業公司可以占有大量用戶數據并因此產生網絡效應,同時也造成激勵錯配,使得所有公司都致力于收集并壟斷用戶數據而非提升應用服務的水平。正因為商業公司占有大量用戶數據,基于數據挖掘而推薦廣告的商業模式才成為互聯網公司最為成功、也最為普遍的盈利手段,這又反過來強化了商業平臺公司收集并控制用戶數據的動機。基于對此問題的反思,伯納斯-李發起了“索利得”(Solid)開源項目,其核心理念在于將應用程序與用戶數據分隔開,用戶在互聯網上產生的數據都被存儲在特定位置,商業平臺公司必須首先要獲得用戶同意才能獲得數據以提供服務。
“索利得”開源項目被視為相對于傳統萬維網的另一條技術路線,其實現了互聯互通的網絡功能,針對“數據豎井”及相伴隨的平臺壟斷結構提出了新的方案構想。這一新路線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任何數字平臺公司都不能占有用戶數據,而經由用戶同意,不同商業平臺公司都可以調用同一套用戶數據,由此可以打破“馬太效應”并促進市場競爭;同時,互聯網商業化進程中的激勵錯配可被消除,此時數字平臺公司的核心動機不再是收集并控制用戶數據,而是提升并創新其產品和服務,隱私侵犯、虛假新聞等互聯網亂象可得到有效解決。
盡管我們不能確定“索利得”開源項目的未來是否會像萬維網一樣成功,但這并不影響從技術多重路線視角來理解數字時代治理革命的著力點,相關啟示主要體現為:第一,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的技術多重路線仍然是存在的,即使是作為基礎設施并因路徑依賴效應而往往被認為不能被改變的萬維網,事實上也存在另一條可能的技術路線。以此為基準,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多重技術路線的演化規律同樣一般性地適用于其他類型的數字技術。第二,針對既有發展過程和模式的反思是探索多重技術路線的起點,這尤其體現在數字技術、數字業態的社會影響方面。換言之,數字化轉型的已有模式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結構與關系,使得昂格爾筆下“人類改造自然的實驗”與“改造人類合作方式的實驗”不能很好地結合,新型生產關系自然要求在這兩方面同時作出調整,而其他技術路線的探索與再選擇便是對此的回應。第三,考慮到技術演化的不確定性,以合適機制鼓勵多重技術路線齊頭并進,比選擇特定技術路線重點突破可能更為重要,而這也是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不竭動力。無論是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形式,還是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形式,都可能導致特定技術路線的資源集中乃至壟斷,數字時代的新型生產關系更應該重視扭轉此種“馬太效應”,為不同技術路線的涌現與競爭提供機會窗口。
(二)“數字后福特”作為組織變革的迭代進化
數字時代我們究竟將迎來何種組織變革,同樣是新型生產關系構建需要考慮的重要內容。20世紀后半葉,得益于計算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創新應用,“后福特制”作為回應福特制危機的組織結構已經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一般認為,福特制在促進規模效應的同時也逐漸受困于邊際效應下降,當標準產品的市場需求逐漸飽和、多樣性且定制化的“長尾”市場開始興起之后,流水線式的生產過程在導致勞動異化的同時,也束縛了生產率的持續性提升。這些問題在信息技術勃興的背景下,有了新的破局希望。個人計算機的微型化、互聯網的分布式技術結構在功能上被認為有助于支撐“后福特制”作為靈活生產模式的管理要求,能夠以更為有效的信息傳遞和控制方式為更開放、更靈活的生產組織結構提供現實可能。開源軟件、百科網站等開放生產模式的興起成為證明“后福特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事例。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后福特制”就成為數字技術革命的穩定生產組織結構。開源軟件在證明分散主體合作能夠帶來強大生產力的同時,仍然要面臨如何提供穩定且可持續產品和服務的商業化挑戰。而依托對大量數據或關鍵瓶頸資源(如操作系統或應用商店)的掌控,數字平臺作為交易撮合者、過程管理者、產出控制者的多重身份登上歷史舞臺,其更為徹底地將數字技術革命轉化為穩定的生產與再生產模式,并同樣釋放出新興數字技術的潛在生產力[25]。
但這是否意味著數字平臺就是數字時代新型生產關系的主要內涵呢?答案很可能也是否定的。一方面,數字平臺的出現與擴散究竟是一種必然還是一種偶然,仍然是可爭論的命題。從伯納斯-李的反思不難發現,如果早期萬維網換一種技術架構,我們很可能會迎來截然不同的數字生產組織結構。另一方面,伴隨著平臺規模和范圍的擴大,自2018年以來的集體反思均是針對數字平臺發展過程中引發的一系列治理風險。近年來日益強化的監管壓力不僅改變了20世紀末為數字平臺豁免連帶責任的“安全港原則”基本理念,而且提出了進一步調整生產組織結構的時代命題——而后者才是現階段新型生產關系的實質內涵。
從信息技術發明應用背景下“后福特制”的萌芽,到以開源軟件、百科網站為代表的分布式共同生產模式的興起,再到數字平臺壟斷性結構的形成,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生產組織結構在當下又到了新的變革節點。為更好釋放數字技術革命的生產率提升潛力,組織結構層面的新型生產關系仍然需要再次回到“后福特制”的基本理念,并進一步迭代形成“數字后福特”的新體系[26]。具體而言,包括以下逐級遞進的三點建議:
第一,數字時代的新型生產關系仍然需要堅持后福特主義的基本理念。數字技術革命偏好分布式生產組織結構的發展規律并未改變,動態變化的市場需求環境已成趨勢,后福特主義的基本理念仍然符合當前解放生產力的核心要求。從互聯網到區塊鏈,數字技術不同于其他技術的特殊性正在于其分布式特征,即在不斷消解既有中心節點權力的同時愈發充分地調動分散主體的生產性力量,而后福特主義仍然是與此技術特征相匹配的生產組織結構。
第二,與20世紀下半葉討論的“后福特制”不同,在經歷開源軟件、數字平臺的演化歷程之后,當前的“數字后福特”生產組織體系需要在兼顧二者的基礎上更強調集中與分散的平衡統一。一方面,盡管數字平臺的壟斷性結構招致批評,但其作為權力集中點并不全然是消極的,其承擔的信息認證與連接功能仍然在全社會范疇促進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有序流動[27];另一方面,盡管開源軟件、百科網站作為生產組織結構受到了數字平臺的沖擊,但它們并未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仍然提供了支撐數字技術創新應用的龐大知識基礎。事實上,當前大型語言模型的突破式發展正是建立在以百科網站為代表的海量網絡公共知識累積基礎之上,而開源也仍然是大模型最重要的發展模式之一。在這兩方面基礎上,未來新型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變革,其重點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選一”,而是探索能夠兼顧數字平臺協調能力和開源軟件分散生產特征的新結構。
第三,“數字后福特”作為一種新型生產組織結構能否兼顧集中與分散的關鍵,是“公地”與“私益”能否實現穩定的相互促進關系[28]。開源軟件所代表的生產組織結構,創造的是公地知識,以開放架構促進知識的流動和再生產;數字平臺盡管打破了傳統公司組織的封閉邊界,但管理控制的強化仍然旨在確保私益的實現和累積。在21世紀初的數字化轉型階段,這二者并行不悖,但近年來呈現相互交叉乃至相互侵蝕的沖突局面。這也正是引致利益相關方對治理模式進行反思的關鍵原因:澳大利亞要求社交媒體和搜索引擎等數字平臺與本地新聞內容生產商進行收益分配協商談判,《紐約時報》及作者工會起訴OpenAI和微軟在訓練大模型時侵犯其知識產權等,都是近年來的鮮活案例。在此背景下,新型生產關系要求的“數字后福特”生產組織結構,勢必需要對“公地”與“私益”的再平衡作出回應,既能維系公地資源的不斷增長以支撐數字技術創新和生產力提升,又能確保生產力的提升以服務私益的滿足和福利增長。
(三)包容性和開放性數字制度的探索變遷
治理革命的第三個維度是制度規則的多重可能性探索,數字革命背景下的新型生產關系需要在多種形式的制度規則中找到適配項,使之服務于新質生產力的穩定提升。
包容性數字制度是指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在各個維度扭轉或者限制結構上的分化,以支撐數字時代生產與再生產模式的穩定運行。近年來針對數字化轉型進程的反思,從表面上看是針對當前數字發展模式引致消極影響的回應,實質上則是因為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放大或者塑造結構性分化的關鍵原因。這樣的結構性分化體現在各個層面:數字技術創新被局限于特定領域或特定區域而造成的技術分化,數字資本和數字勞動所占價值分配比例不均衡引起的勞動分化,跨國數字平臺企業與主權國家在稅基繳納與收取方面的稅收分化,等等。這些結構性分化近年來引發了利益相關方重大沖突的典型案例,與之伴隨的制度變遷事實上都體現了縮小乃至扭轉結構分化趨勢的共同特征,而這便是包容性數字制度的基本內涵。以稅收分化為例,2021年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標準的推出,以及經合組織推行的“雙支柱”改革方案普遍共識的實現,都是針對跨國數字平臺企業利用其特殊業態規律展開合理避稅并由此導致各國稅基侵蝕的有效回應,此處的包容性數字制度表現為底線規制標準的實質性要求與經合組織開放談判的程序性要求[29]。對每個領域包容性數字制度的具體內容展開分析已經超出本文范疇,但以打破既有分化結構為主旨以實現更為均衡發展狀態的制度目標,是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實現新型生產關系的關鍵所在。
開放性數字制度主要關注規則的動態演化特征,即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的制度規則需要對不確定性保持開放態度,并伴隨生產過程的變化而相應調整。以數字平臺治理規則為例,從互聯網興起早期圍繞知識產權的爭議,到移動互聯網與“共享經濟”時代圍繞再生產與分配問題的沖突,數字平臺扮演的角色是迥異的,在此基礎上涌現的財產規則或治理規則也是變化的,這也被學者分別稱為“非法興起1.0”與“非法興起2.0”階段[30]。在1.0階段,治理規則的典型特征是確立了以平臺架構為核心保護對象的架構財產權,在促進早期數字平臺快速發展的同時,服務于繁榮網絡言論空間的公共性要求;而在2.0階段,伴隨著數字平臺壟斷性地位的確立,治理規則的核心目標轉而成為打破架構財產權的制度壁壘以重新促進信息、知識等生產要素的跨平臺流動。換言之,在1.0階段服務于要素流動的架構財產權,在2.0階段反而成為要素流動的桎梏,導致這一變遷發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數字平臺推動下數字生產過程和方式的轉化,以及與之伴隨的數字平臺角色和作用的變化。數字平臺治理規則的變遷并非孤例,而是數字技術革命時代制度規則建設要面臨的普遍性挑戰,當前圍繞大模型開源治理規則的爭論便是又一例證。原本針對“搭便車”投機問題而形成的開源軟件許可協議制度,已經不能回應當前的模型責任分配問題,根本原因就在于開源作為一種數字生產方式,已經從分散主體為滿足個體需要的知識生產,轉變成法人主體為滿足市場需要的產品或服務生產。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業態迭代速度的加快,使得數字生產過程和方式的轉變成為常態,而這也自然要求數字制度規則的更迭。“開放性”作為數字制度特征由此成為數字治理革命的必然要求,繼而成為當前新型生產關系的組成部分。
四、結論與討論
技術革命正在密集而迅猛地展開,但其能否轉換為“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的產業革命從而形成新質生產力,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盡管技術瓶頸、技術壁壘、市場規模等技術性或產業性約束條件將影響技術革命向產業革命的演化發展,但體現新型生產關系的治理革命能否順利完成,同樣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考慮到近年來圍繞新質生產力的討論主要聚焦技術或產業層面,本文將關注焦點轉移至表現為治理革命的新型生產關系,由此具有邊際知識貢獻。
以生產率悖論的歷史討論為起點,本文的主要觀點是,在推動技術革命向產業革命轉化以實現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忽略以治理革命為核心的新型生產關系建設,而“技術—組織—制度”三個維度的多重可能性探索,構成治理革命分析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本文結合當前的數字技術革命特征,以數字治理革命為對象提出了數字時代新型生產關系變革與建設的三方面內涵。需要強調的是,當前我們正在進入技術革命的又一個“黃金時代”,能源革命、制造革命、生物革命、農業革命正在各個領域普遍展開,而數字革命僅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領域,因而針對數字技術革命特征而展開的治理革命分析并不能代表新時代新型生產關系的全部內涵;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數字革命作為基礎領域的技術革命,貫穿并影響著其他領域的技術革命,因而以數字治理革命為例來討論新型生產關系的可能變革,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在此意義上,本文的研究定位并非對新型生產關系作出精確定義并解釋其全部內涵,而是提出以“技術—組織—制度”的三維框架作為理解新型生產關系的基本視角,從而豐富我們對于新型生產關系的理解,并進一步激勵未來研究以類似框架和視角探索新型生產關系在其他領域的具體表現和改革方向。 [Reform]
參考文獻
[1]SOLOW R. We'd better watch out[M]. New York: Book Review, 1987.
[2]羅伯特·戈登.美國增長的起落[M].張林山,等,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551.
[3]TRIPLETT J E. The 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 What do computers do to productivity? [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32(2): 309-334.
[4]DAVID P A. 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2): 355-361.
[5]GRILICHES Z. Productivity, R&D, and the data constraint, i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2009.
[6]何小鋼,梁權熙,王善騮. 信息技術、勞動力結構與企業生產率——破解“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之謎[J].管理世界,2019(9):65-80.
[7]LOTHIAN T. Law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Finance,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8]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J].讀書,1996(3):11-21.
[9]ENSMENGER N. Is chess the drosophil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ocial history of an algorithm[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2, 42(1): 5-30.
[10]賈開.算法社會的技術內涵、演化過程與治理創新[J].探索,2022(2):164-178.
[11]邁克爾·斯特雷文斯.知識機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現代科學[M].任燁,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28.
[12]UNGER R M. The knowledge economy[M]. London: Verso Books, 2022.
[13]SCOTT A J, STORPER M. Pathway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 London: Routledge, 1992.
[14]崔之元. 1848年的馬克思、托克維爾和蒲魯東[J]. 二十一世紀,2018(6):25-33.
[15]SABEL C F, ZEITLIN J.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 Politic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J]. Past & Present, 1985, 108(3):133-176.
[16]SABEL C F, ZEITLIN J. World of possibilities: 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賈開,胡凌.合作的互聯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18YdJBFqZUo+0/GcYI6uESuaCrABcJE5ztv6IGGmy165Q=]COHEN J E. Configuring the networked self: Law, code, and the pay of everyday practic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CHANDER A. How law made silicon valley[J]. Emory LJ, 2013, 63(1):639.
[20]賈開,徐婷婷,江鵬.知識產權與創新:制度失衡與“互聯網+”戰略下的再平衡[J].中國行政管理,2016(11):88-93.
[21]王東賓,崔之元.開放協作與自主創新:特斯拉開源與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的戰略機遇[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3):1-10.
[22]蔣余浩.如何避免新技術的“孤島式先鋒主義”陷阱?[J].清華管理評論,2022(6):41-47.
[23]Economist. Reining in the technology giants will take time[EB/OL]. (2020-11-17)[2024-08-01].https://www.economist.com/the-world-ahead/2020/11/17/reining-in-the-technology-giants-will-take-time.
[24]賈開.再造“數字后福特主義”[J].文化縱橫,2023(4):36-44.
[25]賈開.數字平臺經濟的分配影響與治理改革[J].電子政務,2022(5):69-78.
[26]賈開.“數字福特”與“數字后福特”——共同富裕視野下數字生產組織結構的再選擇[J].開放時代,2023(5):31-48.
[27]胡凌.數字經濟中的兩種財產權:從要素到架構[J].中外法學,2021(6):1581-1598.
[28]SLAVO J. ZIZEK. We need a socialist reset, not a corporate 'great reset'[EB/OL].(2020-12-1)[2024-08-01]https://jacobinmag.com/2020/12/ slavoj-zizek-socialism-great-reset.
[29]賈開,俞晗之.“數字稅”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識與沖突——基于實驗主義治理的解釋[J].公共行政評論,2021(2):20-37.
[30]胡凌.互聯網“非法興起”2.0——以數據財產權為例[J].地方立法研究,2021(3):21-36.
The Digital Governance Revolution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s
JIA Kai GAO L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it, but the importance and connotation of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have not been fully discussed. Taking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proposed by Solow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alysi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not automatically be transformed into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rked by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needs to be filled by governance revolution that changes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among stakeholders at all levels. The governance revolution mainly include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alternativ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rules. This is currently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volutionary selection of multiple alternativ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iterative evolution of "digital post-Ford" as a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clusive and open digital institutions.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digital governance revoltion and are also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the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digital revolution.
Key words: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overnance reform; digit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