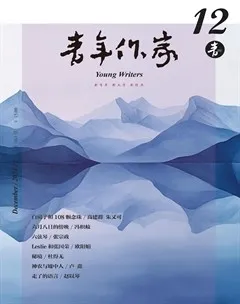六月八日的傍晚
還沒有登機前,達諾不止一次地構想他和李倩相見的情景:
“你……”
達諾先開了口,用目光輕撫站在他面前的李倩。畢竟20年沒有見面了,達諾興奮的目光中含有遲疑。李倩淡然一笑,右邊臉龐上的酒窩隱約可見——那笑臉,那酒窩,不是很新鮮了,陳舊中,熟悉的味道沒有變,依然泛濫著1993年的美麗——三十年前,他們相識在漢江的江畔。他對她的思念,如同篝火一樣,未曾熄滅。
篝火是六月八日傍晚點燃的。
夕陽染紅了溫柔的漢江,江水仿佛灼灼地燃燒。江畔上的篝火逸散的清香,仿佛歌聲一樣飄蕩。篝火晚會是江漢市江漢師范學院中文系的師生和采風的省作家協會的十幾位作家共同舉辦的。達諾盤腿坐在篝火旁,抿著啤酒,他只是偶爾抬頭掃一眼一對對舞伴。他寂寞慣了,獨處慣了,即使生活在喧囂的省城,也從沒有獨自去過舞場。除非作家協會應酬外省市來訪的作家,組織舞會,他非去不可。達諾正準備起身去沙灘上走一走,一個女孩兒走到他跟前,腰身微微一曲,邀請他去跳舞。他抬眼一瞥,女孩兒臉上的紅暈似乎全部聚攏在她右邊臉龐的酒窩里了。達諾知道,他的拒絕,會將女孩兒逼向尷尬。他抓起一瓶還沒有喝的啤酒,剝去了已經撬開的酒瓶蓋子,說:“喝幾口,行嗎?”女孩兒揚起笑臉接過啤酒瓶,脖頸向后稍微一挺,差不多半瓶啤酒灌下去了。達諾覺得自己滿嘴酒味兒,和女孩兒一起跳舞是對女孩的不尊重,也會討她嫌的。他沒有想到,女孩兒會如此瀟灑,連喝啤酒的舉動也是干凈、利落的。他挽起了女孩兒,繞著畢畢剝剝作響的篝火起舞。女孩兒的手臂輕柔地擺動,和達諾交換笑容。女孩兒告訴達諾,她叫李倩,讀大三了。當女孩兒得知,她挽住的就是作家達諾,不由自主地向達諾跟前靠了靠,雙目中流露出毫不掩飾的驚訝和興奮。她在文學期刊上讀過好幾篇達諾寫的小說、散文,她對達諾的尊敬、甚至崇拜,沒有在言語里,而是在神情里,在白皙中浮著紅暈的臉龐上。達諾反而像女孩兒一樣有點別扭了,他兩次踩到了李倩的腳。
是李倩提出去沙灘上走一走的。一離開篝火晚會的現場,李倩就挽住了達諾的一條胳膊,她的頭偏向達諾,腳下有點輕,似乎踩不住舞場上的節奏。“頭暈嗎?你的頭發真濃密呀。頭暈就坐會兒。你這么黑的頭發,給女孩兒,她就更美了。”李倩沒有沿著達諾的話題向前走。達諾說:“坐會兒吧。”李倩點了點頭。兩個人坐在了沙地上。李倩一坐下,就把頭靠在了達諾的肩頭。他們只是這么默默地坐著,默默地看著滿天閃爍的星光,看著被霧嵐糾纏的青山,看著江畔上挑不破的夜色。篝火晚會上的音樂聲像飛鳥一樣,隱隱約約地扇動著翅膀。不是兩個人找不到話題,不是因為他們初次相見無話可說,而是他們覺得,一旦開口,就會給這美好的情境抹上多余的一筆。他們默默地坐著,感受著,讓這一刻,讓這個夜晚,像春雨落在青草地上,悄然滲進他們的心里。微妙的情感,是不可用言語表述的,美的境界是感覺的結果。
達諾和李倩在江畔上分了手,分別向賓館和學校走的時候,篝火晚會剛結束。松柏燃燒殘留的余香依然戀戀不舍,在江畔縈繞。一江星光向東而去。
回到省城,達諾忙于編稿和寫作——那時候,他在省作家協會的《秦風》文學月刊負責小說二審。當他給李倩寫了一封信,發出去以后,他才意識到,大學已經放假了。果然,達諾沒有收到李倩的回信。
九月初,大學開學后,達諾給李倩寫了一封信。盡管達諾思念著李倩,但他極力收斂著自己,用最平淡的言辭陳述,他只是想知道,她在學校里的生活和學習狀況。李倩沒有回信。達諾又給李倩寫了一封信,達諾還是沒有收到回信。達諾的眼前不時地浮現著李倩柔和的笑臉,閃現著李倩臉龐上清純的酒窩,仿佛她對他的情感就盛在那個酒窩中。達諾勸慰自己:你和李倩不過是偶遇,人生的偶然就像黑夜中的一道亮光,隨著亮光的消失,情感世界本該歸于平靜。一個人的自作多情是自戀的另一種方式。即使你喜歡李倩,也是你個人的事情,李倩未必就要呼應。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工作是和文字較量,是探究人物心靈的隱秘之處,是把心貼在筆下的人物身上,而不是把情感、乃至身體粘在生活中的人物身上。一番自我檢討之后,達諾不再想什么李倩、王倩和張倩。
達諾收到了一封來自秦嶺腹地的546廠子弟校的信,他以為是某個業余作者的稿件,就擱在了案頭。他已經離開了雜志社,在省作家協會任專業作家。他要去西水市某個縣寫作,出門時,把案頭擱的那封信拿上,走到作協門口,交給了收發室的劉師,叮嚀他把信轉交給《秦風》月刊的主編許信。
幾月以后,達諾回到了省作協,剛一進門,收發室的劉師就喊他,說有他的幾封信和一些雜志。他把信件和雜志抱回辦公室,一看,其中有一封信就是他轉給許信的稿件;信已經開啟,許信在信封背面寫道:不是稿件,是你的私信。他從信封中抽出信一看,原來是李倩寫給他的。李倩在信中說,她畢業后被分派到546廠任教,在高中部。李倩沒有提說,為什么幾年來沒有和他聯系。她只是說,她結婚剛一年,結婚前,分到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李倩請他到546廠來寫作。她說,這里夏天十分涼爽,空氣清甜,很適合他來寫作。李倩在信中附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李倩,紅裙子,白上衣,臉龐上的笑容好像小說中的句子,有點概念化,那個誘人的酒窩也被相紙忽略了。達諾沒有想到李倩會給他寫信,雖然信中沒有一句暖洋洋的話語,但他總覺得,把私信交給許信,有點不妥,是對李倩的不尊重。達諾想了想,給李倩回了信,并對他的遲復表達了歉意。達諾用漢字排列組合在信紙上的每一句話都是客觀冷靜的。他有意抽干了情感的水分,只陳述他想表述的內容——他會來546廠的。
午飯前,達諾來到了546廠。秦嶺腹地的天似乎比省城里的天高了許多,藍了許多;達諾長長地呼吸著,好像要把積累在胸腔中的燠熱吐出來,把山里的涼爽吸進去,儲存起來。
達諾是先見到了李倩的丈夫,而后見到李倩的。李倩的丈夫高高的個子,膚色微黑,神情深沉,一雙機敏的眼睛好像是從影視劇中那些地下工作者的面部摘下來的。他說,他叫高峰,在546廠子弟校辦公室工作。他說,他提前回來了,李倩還沒有下課,一會兒就到家了。
李倩見到了達諾,淺淺地一笑,問候了一聲,面部的平靜好像化妝師化出來的。達諾打量了幾眼李倩,她面部的紅暈和純情被成熟的美取代了,連那個酒窩也不再有純真的味道。達諾客套了一句:“我來給你們添麻煩了。”李倩丈夫搶先說:“不麻煩,李倩天天盼望你來。”天天盼望?達諾以為李倩的丈夫是實話實說,只感嘆了一聲:“噢!”
吃罷中午飯,李倩和丈夫都去了學校,達諾坐在客廳里的案桌前開始寫作。達諾在稿紙上只寫了一個頁碼,李倩丈夫回來了。達諾的思路被開門聲打斷了,他以為李倩的丈夫是回家來取什么東西,就擱下筆,點上了一支煙,等待李倩的丈夫走后再寫。可是李倩的丈夫并沒有走,他坐在達諾身后的沙發上,也點上了一支煙,翻看一個文件夾。身后坐著一個人,達諾無法進入筆下的情境。用一個粗俗的比喻:寫小說,就好比作者和稿紙親熱;在一雙目光下,能親熱嗎?達諾畢竟在別人家里,他是客人,他只能等待。達諾等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李倩的丈夫沒有走。達諾只好拉開門,走出了房間,在院子里走了走。他再次走進房間,這個年輕人拿起了放在茶幾上的文件夾,又翻動起來了。達諾看看表,再有一個多小時就下班了,他干脆合上了稿紙,拿起了隨身帶的一本書……一個下午,達諾只寫了300多字。
當天晚上,達諾睡在了546廠子弟校李倩的單人宿舍里。
第二天,達諾寫到了十點多,李倩的丈夫回來了,他又坐在沙發上抽煙。過了半個小時,達諾忍不住了,問李倩丈夫:“小高,你不去上班?”李倩丈夫說:“辦公室人多,不安靜,我要寫一個材料,到家里來列一個提綱。”達諾回頭一看,茶幾上無紙無筆,李倩的丈夫沒有說實話。他說:“你坐在這里來寫提綱吧,我出去走走。”達諾離開燠熱的省城,來到山中尋靜,他沒有想到,李倩給他提供的寫作環境是這樣?達諾無奈中又走出了房間。
到了下午,李倩的丈夫沒有回來,達諾安安靜靜地寫了兩個多小時。他拉開房間的門,想去小院子里的廁所方便一下。他抬眼一看,李倩的丈夫坐在不遠處的一塊石板上抽煙。達諾即刻明白了什么,他仿佛被人扒下了內褲,一股羞恥感如火一般在心中燃燒。他進了房間,收拾了簡單的行李,他再也無法寫下去了。
在546廠子弟校,達諾一夜未曾睡好。天還沒有亮透,他走進了李倩住的小院子,李倩和她丈夫還沒有起床。他給李倩的門口留了一張紙條:我回省城了。謝謝!
達諾上了龍口鎮去省城的第一趟班車。
聽見敲門聲,達諾頭也沒有抬。直至有人進了房間,給他打開窗戶,他依然沒有放下筆。他知道,在他寫作的時候,只有雜志社登記稿件的小余偶爾進來,一語不發,打開窗戶,把積攢了幾個小時的煙向窗外釋放一下。他抬眼一看,打開窗戶的不是小余,站在窗戶前的是一個女人的背身。他摁滅了手中的煙,站起來的時候,女人擰過了身,達諾有點吃驚:
“怎么是你?”
“沒有想到吧?”
“沒有。”
“什么時候到的?”
“上午十點。”
“你一個人?”
“一個人。”
李倩微笑著,她的笑容很細,像湖水中泛起的一點漣漪,味兒很淡,色澤缺少亮度,臉龐上的酒窩里似乎填充著一絲苦澀。
“住在哪里?”
“還沒住下。想住在你們作協招待所。”
“我給招待所打個電話。”
“不必了,我自己去登記。”
李倩出去的時候給達諾關上了窗戶,她一邊關一邊說:“不要收留滿屋子里的煙味兒,這樣對身體不好。過一會兒,打開窗戶透透氣。”達諾點了點頭,說了聲“好吧”。
達諾和李倩在街道上的小飯館里吃了晚飯,一同回到了省作協的招待所。坐定后,兩個人都沒有話可說了,還是達諾先開口了:
“最近寫東西沒有?”
“沒有。”
“來省城有什么事嗎?”
“沒有,也可以說有。”
“準備住幾天?”
“不知道。”
“開玩笑吧?”
“不是。”
“你代的課咋辦?”
“我把工作辭了。想去外地找工作。”
“你丈夫……你們有孩子嗎?”
“離婚了。沒有孩子。”
“哦?”
達諾并不驚詫,似乎李倩的離婚在他的意料之中。
李倩給達諾說,她想復習功課,考研。達諾問李倩:“是考古都大學,還是師范大學?”李倩說:“我不想在省內讀,想去外地。”達諾似乎能理解李倩去外地讀研的心思。李倩說:“我來省城,是想叫你給我推薦一所比較好的大學。”達諾說:“我有一個寫小說的作家朋友,在上海的黃埔大學中文系任教,你如果愿意去上海,就叫她指導你復習功課,只要你下功夫,今年就可以考上的。”李倩一聽,笑了,臉上的笑容不再纖瘦,也柔和多了。她說:“我就知道,在我的人生最艱難的時候,貴人就會出現的。”顯然,李倩很激動,她連聲說:“謝謝達諾老師。”達諾也笑了,“什么貴人不貴人?指甲蓋大的事。看你,像小女孩一樣。”李倩臉龐泛上了紅暈。
達諾起身告辭。李倩說:“在這里沖個澡吧。”達諾說:“我回辦公室再寫兩小時。”李倩將達諾送到了門口。達諾抓住了門把,還沒有拉開門,李倩從身后抱住了達諾,她將頭抵在達諾的脊背,幾乎是呢喃:“不要走,陪陪我好嗎?”達諾沒有吭聲。李倩說:“嫌棄我嗎?”李倩這話一出口,達諾被猛刺了一下。他的一部長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對男女純粹的、剔除了相互占有的愛。可是,生活中有這樣的愛嗎?沒有身體參與的愛,能叫愛嗎?他和李倩之間算什么呢?愛情本來就是不必想得明明白白的事,而他卻非要想明白不可。這可能嗎?在渴望中推拒,在推拒中渴望。你這不是虛偽嗎?達諾的內心在撕裂,理智和激情像兩股洪水在沖擊他。達諾回過神的時候,李倩松開了手,她淚流滿面了。達諾用手給她揩了揩淚水,對她說:“倩,我們之間,不是你想的那樣,我明天就給上海的作家朋友打電話。過兩天,就給你訂去上海的機票,你的目標是考研……”達諾把要說的話咽回去了,他深情地抱了抱李倩,拉開門走了。
一個下雨天,達諾收到了李倩的來信,信是從上海寄來的。李倩在上海已經復習了一個多月。李倩信中說,指導她復習的那個年輕教授要她買一本一個法國評論家的《小說敘事學》閱讀。她在上海找了幾個書店,沒有買到,李倩希望達諾能在省城的書店給她找找。達諾做畢痔瘡手術出院沒幾天,傷口疼痛,不但不能多走路,坐一會兒也疼痛。他忍著疼痛上了出租車。那一整天,他跑了四家書店,從東郊跑到西郊,又從城內的解放路書店跑到南郊。在出租車內,他坐不住,屁股一挨上坐墊,傷口疼得如刀割,他只好側身躺在后座上。在去古都大學的路上,他暈車了,頭暈惡心,還沒等他搖下來窗玻璃,就吐在車內了。司機是一個善良的中年人,沒有責備他。下車的時候,他硬是給司機多塞了30元,作為洗車費。在南郊的古都大學旁邊的大學路商店,他買到了這本《小說敘事學》。他一分鐘也沒有耽擱,下午6點以前,趕到了城內的和平路郵局,把書寄出去了。晚上,他回家一看,傷口出血了。第二天,他又去了醫院。
達諾知道,上海的冬天不比他居住的省城,省城的房間里有暖氣,而上海的冷是無可設防的冷,潮濕的冷風仿佛向人的骨頭里滲。剛一入冬,達諾就從省軍區旁邊的軍人服務社給李倩買了一件軍大衣,買了一床加厚的棉花做內墊的被子。李倩收到了大衣和被子后,給達諾打來了電話,電話是打到作協辦公室的。李倩在電話中叫了一聲達諾老師,說收到了大衣和被子。她說了聲:“我……”突然不作聲了,送進達諾耳朵里的是李倩略顯粗重的出氣聲——一個人負重或十分激動時發出的那種聲音。達諾問她怎么了。無形的電波傳給達諾的聲音是李倩的啜泣。她啜泣了幾聲之后,掛斷了電話。達諾似乎看見,李倩走出電話亭子的時候,淚流滿面了。達諾只有一個想法,叫李倩考上碩士研究生,完成學業,重新工作。他幫助李倩,不是為了求得回報。在達諾后來的人生中,只要他有能力幫助,就去幫助。幫助他人,是他的情感,是他的生活。
在李倩讀研的那三年里,她幾次打電話或寫信,請達諾來上海看看。李倩完成了畢業論文答辯之后,達諾恰巧有一個機會來上海——一個上海的作家朋友舉辦作品研討會。達諾提前一天到了上海。
下了飛機,達諾直接去了李倩給他預定的賓館。到了賓館,李倩早已在賓館大廳等著他。
進了房間,達諾才正眼去注視李倩,李倩的臉龐上堆著笑,她的笑豐滿而圓潤,連酒窩也灌進了甜意。三十歲的李倩到了人生最豐腴最有味道的季節。達諾的目光由注視而變輕撫了,他的目光從李倩的臉龐上滑下去,生怕粗了,重了。他站在兩步之外,不錯眼地看著李倩,眼里的內容似乎五味俱全。無形的距離仿佛一根扁擔,把他和李倩挑在兩頭;達諾和李倩的距離感,既來自達諾對李倩突然間產生的陌生和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自卑——也許是對美的畏怯;也來自李倩,達諾能嗅得出,李倩身上已經染上了屬于上海人的那種特有的氣味,包括說話的語氣、語速,包括走路的姿勢,包括一舉手一投足都有點上海味道了。這味道,使在北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達諾感到陌生。這種感觸的產生,和達諾特立獨行、偏執自戀的性格有關。
晚飯是在賓館的餐廳吃的。
從1993年相識,十年了,達諾和李倩第一次同床共枕。達諾什么也不想了,他緊緊地抱住李倩。不知是什么原因,當達諾去吻李倩的時候,李倩豐滿的嘴唇卻抿著,沒有開啟。李倩是達諾擁吻的第二個女人,他曾經在他的初戀那里品嘗過接吻的濕潤和溫度。他和李倩的接吻就像影視劇中看到的鏡頭,只是一種表演,一種形式,沒有內容。盡管李倩的變化像激光一樣迅捷。達諾沒有懷疑李倩對他的情感的真實性。當他再次把李倩擁入懷中的時候,他從李倩的笑臉上、眉眼里讀出了甜蜜和滿足。李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說出了使達諾難以忘卻的三個字:“你真好。”
你真好。
這三個字是從鄰座的一個女孩口中說出來的。上了飛機,系好了安全帶,達諾的鄰座才走過來,落座了。達諾的鄰座是一對小情侶。女孩的頭枕在男孩的腿上。男孩一只手輕撫著女孩濃密而烏黑的長發。女孩仰望著男孩。男孩俯下身去吻女孩。顯然,他們的接吻很纏綿,有點泛濫了。“你真好。”女孩兒說畢,坐直了。她對男孩兒的愛意從雙目中向外漫溢。年輕的愛,才是有活力的愛,有亮度的愛。這對纏綿的小情侶使達諾不由得這樣感慨。他的感慨沖淡了他這次去上海的意義。這半年來,他被思念被渴望纏繞著,催促著:去上海,見一見李倩。這種情緒,這種情感折磨得他夜不能寐,恍恍惚惚。他在猶豫不決中,訂了機票,終于成行了。李倩呢?李倩會如此思念他嗎?
達諾回到省城兩個多月以后,收到了李倩的來信。李倩在信中只告訴了他一件事:她懷孕了。他給李倩寫了回信,想知道她的懷孕究竟是怎么回事;想知道她的工作落實了沒有。李倩沒有回信,等他忙完了正在寫的那部長篇小說,想給李倩打電話的時候,才發覺,他沒有李倩的聯系方式。李倩已經畢業了,走出了學校,即使他撥通學校里的電話,學校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也未必知道李倩在哪兒工作。達諾只好給黃埔大學他的教授朋友打電話,詢問李倩的去處。教授朋友在電話中說,李倩落實到了市三十八中。她在三十八中只上了一個月課就走了。三十八中的老師說,好像去了市政府哪個下屬單位,市政府最少也有三四百個下屬單位吧。她沒有再和我聯系,我不知道她的去處。達諾嘆息了一聲,只說了一句:“知道了,謝謝。”
二十年沒有和李倩聯系,二十年沒有她的音信了。不是你沒有聯系他,你給她寫過信,也盲目地打過電話,卻沒有得到她的信息。你以為,人的情感,錯過了就不會開花,不會結果,也就沒有收獲。既然沒有收獲,達諾也就放棄了。
毫無征兆的思念,毫無理由的想念,而且這思念如同波濤洶涌,沖擊著他理智的堤岸,好像他不來上海見一見李倩,到了天堂也難以安寧,好像在棺材板釘上最后一顆釘子那一刻,他也合不攏雙眼。坐在飛機上,當身體離開地面萬米之后,達諾平靜了許多:你對李倩的思念,是你個人的事情,和李倩沒有關系,你不能把你的思念構架在擾亂她的生活上——假如你見到了她,也許她有了一個稱心如意的丈夫——肯定會吃驚不小;也許,他們會被嚇著的。還有她的孩子——她在信中所說的那個懷孕后生下的孩子……達諾不愿意像構思小說一樣想象了,生活比小說復雜得多,荒誕得多。
當鄰座的男孩兒把手中的飲料遞給那個女孩兒的時候,達諾才聽見空姐問他:“先生,您喝點什么?”達諾擺了擺手,表示不需要。
下了飛機,坐上出租,司機問他去哪里,他竟然脫口而出:“不知道。”他確實不知道該去哪里。“不知道?”司機回過頭來掃了他一眼,迷惑的目光中有責備。他說:“外灘。”二十年前,他和李倩在賓館里的餐廳吃畢飯,在外灘坐了一會兒,才回到了房間。
達諾來到了外灘。他朝不遠處那個中年女人擺了擺手。女人一襲白裙子,一件淡紅色的上衣,挺胸而走的姿勢像極了李倩。達諾沒有喊她,只是擺了擺手——假如喊錯了人,他不只是尷尬,也許會惹出麻煩來。達諾目送著女人走遠了,走進了夕陽之中。
二十年前坐過的地方,已經有了新的面目。外灘和許多城市一樣,披上了時尚的外衣。達諾的記憶里只留下了方位,準確的位置被花呀草呀和精巧時尚的建筑物覆蓋了,被時間淹沒了。達諾坐在一個石凳上,坐在2023年6月8日的傍晚,遠處的建筑物在輕霧般的潮氣中顯得模糊而曖昧。最高的那幢建筑仿佛一個人伸向天空的手臂,似乎在喘息,在掙扎。眼目可及的黃浦江,在夕陽下由暗紅變為淡灰,江水似乎載不動迅速變化的顏色,顯得呆滯而遲鈍。達諾收回了目光,一男一女從他眼前走過去了,他覺得那個女人就是李倩,肯定是李倩。李倩已經中年的面龐大概被化妝品改造了,像硅膠娃娃一樣漂亮而又虛假。達諾目睹著李倩和那個男人走進了渾濁的江水。他閉上了雙眼,等他睜開眼睛的時候,眼前什么也沒有,只有天空和大地。
達諾抬眼看天空。傍晚的絢爛,十分短暫,天空黯淡了。一陣風貼著江水上了岸。達諾感覺到的不是涼爽,不是愜意,而是孤寂,是凄愴。他心里一緊,手腳發涼,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他緩了一會兒,收回了目光,垂下頭,潸然淚下了。
達諾的情緒像開盈了的花,很難控制。他由啜泣改為放聲而哭。這時,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走過來,問他:“大叔,你怎么了?哪兒不舒服嗎?”達諾止住了哭泣,用紙巾揩了揩臉龐,看了年輕人幾眼,說:“我……沒事,謝謝小伙子。”
他注視著年輕人遠去的背影。幸虧,你沒有給小伙子說自己是癌癥晚期,將不久于人世。你直著腰,站立了一生,何必在人生的最后乞憐他人的同情?達諾為他剛才的哭泣而羞愧。他安安靜靜地坐在2023年6月8日的傍晚,上海的傍晚。

【作者簡介】馮積岐,小說家;陜西省岐山縣人,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1983年開始在《當代》《人民文學》《上海文學》等刊發表中短篇小說,小說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選載;著有長篇小說《村子》《逃離》《鳳鳴岐山》等15部;現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