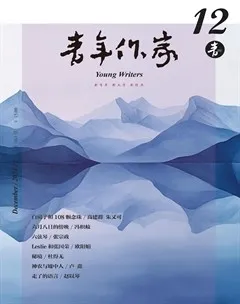Leslie和張國榮
一
“Leslie!”聽到有人在后面這樣叫時,張國榮一下沒反應過來。
近兩年,他時常忘記自己的英文名。雖然是在他的一再強調之下,朋友們才對他以英文名相稱。
剛到北京時,他急于抹去身上的鄉土味,留長發、戴耳釘,像女人一樣斜挎著軟布包兒,頻繁出入酒吧和咖啡廳。老家那個名為野貓窩里的小山村,鬼一樣以并不存在的追趕嚇得他一路狂奔。
在老家,野貓不是貓,是老虎的別稱。
他在那個以老虎扎窩而得名的小山村生活了二十多年,趁著母親做團年飯時逃到了縣城,又從縣城逃到了北京。
他有個叫張國輝的哥哥,還有個叫張國蓮的姐姐。同村還有張國明、張國生、張國慶……張國榮淹沒在一大堆諸如此類的名字中,跟野貓窩里的紅土地一樣土氣。
他要取個英文名。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有個紅遍兩岸三地的港星跟他同名同姓。那位明星的英文名叫Leslie,他就也用了Leslie做英文名。
“叫我Leslie。”他跟每一個在北京認識的人這么說。
如今,在北京認識的每一個人都叫他Leslie,他卻漸漸淡忘了這個英文名。
臨陣變節似的,他帶著負疚感回頭轉身,掃過一排鱗次櫛比的酒吧招牌,看見一個緊裹在曳地長裙里的女人。
“Monica。”對方滿懷激情地指了指自己,“還記得嗎?我是Monica。”
腦袋里網速不足似的轉了個小圈圈,他想起來,她是他剛到北京時的同事。年近五十的人了,身材還是那樣突兀。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趕不趕時間?”Monica將黑浪一樣的長發夾到耳后去。
他抬了抬手腕,假裝瞄了一眼戴在上面的勞力士。
對方以恰到好處的角度欠了欠身:“那改天再約。”
“改天再約。”
他并不在乎時間,也沒看清究竟到了幾點,他只想來去自如地游蕩在五月的后海。
他略顯疲態地點了根七星,軟風棉綢一樣在臉上扯來扯去。與地心引力對抗了將近五十年,他兩腮的肌肉有些松弛,刀劈斧鑿的線條變得圓潤,老之將至從里到外無以掩蓋。每天擼鐵鍛造的體形加上Burberry得體的剪裁和優良的質地給了他宜人的風度,卻給不了他青春。再怎么精心修飾,他也只是個風度宜人的中老年男人。
風度翩翩的中老年張國榮望著夾岸的垂柳,目光順著柳梢伸向遙遠的夜空。北京的垂柳真高啊!夜空被明亮的燈光阻隔在外,不見星光,月色暗淡。暗淡的夜空毛茸茸地擱置在電光的塵埃后面,讓他想起玻璃球體老化的眼睛。野貓窩里的垂柳是清秀的小姑娘,纖纖瘦瘦、眉目疏淡。北京的垂柳如同一個個皮糙肉厚的莽漢,葉肥枝壯、環環相扣,像鐵鏈。Monica在夜風撥動的鐵鏈下越走越遠,陡峭的臀部猶如一張凄厲的臉。
七星煙不好買了,要省著點抽。
二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去山上抓眼鏡王蛇嗎?”張國榮給張國輝發了條微信。
“記得,那時候窮得實在沒辦法了,現在想來蠻危險的。”做大哥的頭一次回復得這樣快。
想起那次抓眼鏡王蛇的經歷,張國榮的思緒才清晰起來。
一個人待久了就是這樣,好像一直在思考,又好像空白一片。
思緒在腦袋里穿梭,逐漸清理出時間、地點。那年他約摸十歲吧,大哥該有十六七歲了。
是六月天。野貓窩里的六月天,是陽歷七八月。熱得很。大家吃著夜飯在村頭的老樟樹下乘涼,二伯爺說:“山里來了條眼鏡王蛇,莫去山里抓石蛙了。”
張國榮看了張國輝一眼,張國輝也正轉過頭來朝著他看。兩兄弟眼里都有竭力按捺的興奮,就跟聽說山里埋了塊寶石樣的。
眼鏡王蛇值錢,一條能賣幾百只石蛙的價格。
放下飯碗,張國輝跑進柴房背了捆油篾出來。
“走,抓蛇去!”他笑吟吟的,眼睛里閃著晶亮的光。
進山前,舍不得點油篾。張國榮跟著張國輝深一腳淺一腳行進在縱橫交錯的田間小道上。月光清明地照著草葉,草葉上落滿了夜露。星子顆顆分明,嵌在黑緞上的寶石樣的。
夜晚的山林異常熱鬧,各類蛇蟲鳥獸鳴叫不止。張國輝抽出根油篾敲了敲張國榮的頭:“不是你,我至少能省下十根油篾。”油篾就是浸了松油的竹篾,易燃、耐燒。說是耐燒,可畢竟也只是根篾片而已,最多燃個十幾分鐘。張國輝獨自進山時,不到萬不得已從來不點,帶了張國榮,一進山口就點亮起來。
油篾一燃,近前的蛇蟲鳥獸即刻噤了聲,無須親眼看見也能想象它們伺機而動的樣子。稍遠些的仍自放肆,嘰嘰咕咕怪叫不止。“吭吭”之聲如鼓如牛的是石蛙,循聲尋去,必有一兩只目瞪口呆伏在那里。
抓了幾個小時的石蛙,眼鏡王蛇出現在一塊平坦的青皮麻石上,一圈一圈密密實實地盤著,斗笠一樣,滴水不漏。
張國輝輕手輕腳脫下外套。張國榮看見斗笠上豎著一個扁平的蛇頭。張國輝悄無聲息走了過去。張國榮憋著滿臉蓄勢待發的狂喜。張國輝縱身一跳,將外套裹在蛇頭上。張國榮歡叫著:“抓住了!抓住了……”
張國輝從麻石上滾進草叢里。草叢有半人來高,伴著翻滾碧波蕩漾。張國榮扒開草叢,聞見石菖蒲濃郁的香氣。半人高的石菖蒲里,眼鏡王蛇玉米稈子粗細的身體緊緊纏在張國輝腰上。張國榮撲上去雙手抓住蛇身,蛇身又滑又緊,怎么用力也抓不牢。他想起大年初一吃長面的情形,掀起蛇尾將雙手變成筷子,一圈一圈把張國輝腰上的長面卷到自己手上去。張國輝雙手壓住蛇頭騰出一只腳來踩蛇尾。張國榮被拖拽著倒在地上。月光如同母親的眼神,看著兄弟二人在石菖蒲里翻滾。石菖蒲濺出新鮮的汁水。
收蛇的老師傅說,幸而二人命大,這蛇毒得很。
沒爹的孩子,怎么能命不大呢?
張國輝將外套連同眼鏡王蛇一起塞進布袋里。布袋里兜著一陣狂風似的。他舉著那陣狂風說:“蓮妹子可以上學了。”
命不大,張國蓮連少女都沒做過就要變成老太婆了。
那條眼鏡王蛇,讓張國蓮享有了一名少女本該有的青春。
石菖蒲好養,張國榮在墻根下種了好幾蓬,襯著青磚灰瓦,頗有幾分致趣。
在北京打拼了幾年,張國輝提醒他:“有錢就買房子吧。”那時良鄉還是郊區,房價低。他就用相當于市中心一間單身公寓的錢貸款在良鄉買了座別墅。沒錢裝修,就抹了層水泥搭了些鋼架子。這幾年流行朋克風,倒讓他趕上了潮流。帶回家的女孩都跟他兒時見到眼鏡王蛇樣的憋著滿臉的狂喜:“太酷了!好舒服呀……”讓她們倍感舒服的,還有停在門口那輛暗藍色保時捷。沒有保時捷的加持,農民自建房般的水泥地和脅骨外露般的鋼架子,難以讓一個正常的城市女孩感覺舒服。
恐怕只有張國榮自己是真正感覺舒服,樓上樓下不用換鞋,除了書房的電腦桌和偶爾開火的廚房,幾乎不用打掃。
他不留女人長住,又不喜歡請鐘點工,不是朋克風,光伺候這個房子就夠他受的了。
鋼架子上擺著一長溜兒咖啡豆,有各種口味,來自各個國度。他抓了一撮綠茶放進玻璃杯。可能是年紀大了,他過了午時就不能再喝咖啡。兩三年前他還是一茶缸一茶缸喝的,喝完立馬入睡。到底是中國人,再怎么崇尚西方的飲食習慣,終究改變不了中國式腸胃。咖啡因帶給他的,不再是國際化的小資情調,而是滿臉的火氣痘和徹夜的失眠。
他看著綠茶在玻璃杯里一片片豎起來,像新生的草地。屋頂的射燈打在這一小片草地上,讓他想起鋪著草坪的足球場。
入住良鄉的頭幾年,他別墅后面不遠有個足球場。每天晚飯前,他都在那兒踢球,帶著一條名叫小九的金毛。
小九被某個跟他戀愛過的女人帶走了。那女人知道他離不開小九,就帶走了小九,并稱領回小九的條件是:結婚。他怎么可能結婚?起頭就說好了的,他是不婚主義者,只戀愛、不結婚。這些女人真是奇怪,說好了不結婚才起頭的戀愛,戀著戀著又要結婚。他怎么可能為了要回一條狗而結婚?盡管他確實離不開小九。
三
張國輝和張國蓮先他一步逃到北京。只不過,二人的出逃都戴著體面的面具。張國輝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張國蓮以優雅的氣質嫁了富商。他二人被母親風風光光送出了門。只有他,是真真正正偷偷摸摸一路逃奔,在月黑風高的夜里,在步步緊逼的鞭炮聲中。
母親說過,無論如何都不會放他走的,吃糠咽菜養大了三個孩子,總要留一個傍身。
他無意承擔傍身的命運,掙扎了五六年,還是甩下了母親一個人吃那頓團年飯。
他到北京時,張國輝已經去了杭州,張國蓮去了美國。二人都把北京當作跳板。他也預備著從這里起跳,跟大哥一樣累積了資本找個中意的城市安身,或是跟二姐在美國會合。
然而上十年來,他停留在預備起跳的姿勢上,一動不動愣在那里,跟卡了帶的錄像片一樣。
他一直在糾結,究竟去向何方。
他從未為錢發過愁。張國輝上清華時,只帶了十幾塊錢生活費。他寫信去問過:“錢花完了怎么辦?”張國輝回信說:“在北京,只要有雙手就能活。”
他對著信紙看了看自己的手,那雙手完好無損。
為了勤工儉學,張國輝在餐館端過盤子洗過碗。他還曾寫信去問過:“會不會被人看不起?”張國輝說:“自食其力就不會被人看不起。”
有雙手就能活,自食其力就不會被人看不起,這些話在張國榮心里生了根。他奔向北京時毫無顧慮,學著大哥的樣子端了幾天盤子洗了幾天碗,果然能活。
挨著餓長大的孩子,有塊大餅吃就夠了。端盤子洗碗換來的不僅是大餅,還有吃不完的大魚大肉。
那時的野貓窩里,同樣的一雙手,換不來頓頓大魚大肉。
他自食其力,果然沒人看不起,北京的大爺大媽們熱情得像隔壁二公公二婆婆。
在野貓窩里,自食其力也照樣有人看不起。沒父親的孩子,常常被人扔泥巴。沒男人的女人,常常被人占田霸地。
為了保護母親和弟妹,張國輝十二三歲就跟著林場里的伐木工習武。
母親說:“為了拜師,你大哥起早貪黑去林場里幫人砍樹。那么粗的樹,也不曉得他怎么砍得動。”
在母親嘴里,大哥孤身一人走向林場深處,赤著腳,挽著衫袖,手里舉著一把磨得精光的斧子。林場里經久不衰的鬼故事和偶然出沒的豺狼都不曾將他嚇退。他頂著星光去,踩著月光歸,懷里揣著用來溫習的書本。
少年張國輝的執著和勇敢打動了一位伐木工。或是說,一位身在異鄉的伐木工看著少年張國輝,想起了他遠在家鄉的孩子。他的孩子也跟張國輝一樣,必須承擔起沒有父親的生活,雖然他還活著。他收了張國輝為徒,寄望著遙遠的故鄉也能有個跟他一樣的壯年男子,給他幼弱的孩子一份保護。
張國輝學的是滾子拳,九滾十八跌,滾得一身破破爛爛。用母親的話說,跟他們早死的父親一樣的。
父親是瘋死的,一身破破爛爛。
發瘋前,父親是十里八鄉唯一的郎中,早出晚歸幫人看病,騎白馬。
白衣白馬的父親喜歡洋東西,帶香味的洋堿、紅頭子的洋火,什么稀罕用什么,收音機都有一大一小兩臺。
在一個擺弄小收音機的夜晚,有人前去告發他偷聽敵臺。
那個夜晚過后,父親就發了瘋。瘋了七八年。
起初,母親以為他裝瘋,直到他對她掏出了刀子。
掏出刀子的父親被母親關進了屋后的牛棚。身為長子的張國輝一日三餐隔著牛欄給父親送飯。
想到給父親送飯的大哥,張國榮腦海中浮現的總是張國輝十三四歲的樣子,那是他記憶的起點。自記事以來,大哥就是個銅皮鐵骨的少年。然而認真算起來,那時張國輝還是個七八歲的孩子。一個缺吃少穿面黃肌瘦的小孩,隔著牛欄給親生父親送飯。
對于山區的孩子來說,失去父親的庇護堪稱災難。張國輝從七八歲起就和母親一起扛起了這個災難,從未向人提及這災難背后的艱難。張國輝不喜言辭,每次跟生產隊開工,總在鋤頭上纏上一條蛇。包產到戶后,村民們仍然記得那條蛇,每回談論起來嘴里都刺溜著冷氣。張國榮明白,那條蛇,是不喜言辭的大哥無聲的宣誓:誰敢欺負他,他就放蛇咬誰。那條蛇——確切地說是那一條條蛇,父親一樣庇護了張國輝,無人膽敢克扣他的工分。
張國榮想象過大哥第一次把蛇纏在鋤頭上的情景。想象中,大哥跟往常一樣,不動聲色、有條不紊。
不動聲色、有條不紊的動作背后,有個無依無靠拼死一搏的孩子。
這孩子到了北京仍然不動聲色有條不紊,端盤子洗碗只是權宜之計,憑借在林場里練就的拳術,他很快找到了一份當武術教練的兼職。憑借那份兼職,他又認識了武館老板的小女兒。武館老板的小女兒得知他是清華的大學生,立刻展開了熱烈的攻勢。一個能文能武勤奮上進的女婿,武館的老板也不好嫌棄。還沒畢業,張國輝就在未婚妻的經濟支持下做起了生意。
張國榮也跟大哥一樣,端了幾天盤子洗了幾天碗就在認識Monica的那家公司入了職。入職不久,又跳槽到一家報社做記者。
他做記者時,頭一次采訪就被拒之門外。他不動聲色地守在那里,有條不紊地一次次跟受訪者的助理溝通,就像往鋤頭上纏著一條蛇。受訪者預備出門時,他立刻堵了上去,頂著嚴厲的斥責和厭惡的冷眼詢問拒絕采訪的原因。那個原因,成為他撰寫的新聞標題。
抓過眼鏡王蛇賣的孩子,再惡毒的機會也能握在手里。
抓過眼鏡王蛇賣的孩子,沒什么格外為難的事。
做記者累積的人脈和故事素材,讓張國榮當上了一家電視臺的編導,拍了幾個不冷不熱的片子,他又開起了文化公司。文化公司給他帶來了勞力士和保時捷,讓他擁有了去美國或者某個心儀城市的選擇。
一切順風順水,他才開始糾結。
四
“老娘還是不肯去杭州么?”張國蓮問過不下幾百回了。
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再耳聰目明也不能一個人留在家里。老人家最怕摔,野貓窩里的路高低不平,鋪上了水泥也仍然是高低不平。
“老娘放不下那兩畝油茶。”
栽著油茶樹的山里,葬著他們的父親。
張國榮已記不清父親的樣子。
父親生活的年代,拍張照片就跟結次婚樣的。野貓窩里的村民往往是過了花甲才去拍一回,留著畫遺像。父親想不到自己那么年輕就會死,沒留下照片,連張遺像都畫不成。
張國榮想當然地認為,父親必然眉目慈善而周正。是個好人。
長到十六七歲時,張國榮聽村里人說:“你跟你爺一樣,桃花眼,招女人。”
原來父親是桃花眼,原來父親招女人。
再長大些,村里人又告訴他:“你爺跟隔壁村里的寡婦相好,大家都叫他浪蕩子。”
原來父親是浪蕩子,不是他心目中正正經經的好人。
張國榮體會到了母親看著父親掏出刀子時的心情。她幻想著他是裝瘋,然而他不是;他幻想著他是個好人,然而他也不是。幻想歸幻想,現實是現實,盡管有關父親的幻想是他和母親賴以生存的動力。動力崩塌了,他們仍要在現實中活下去。
據說那個告密的人,就是為了那個小寡婦跟父親爭風吃醋。
張國榮一度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后來他才明白,浪蕩子未必不是好人。
或是說,他執拗地以他的浪蕩,以他浪蕩后仍然保有的善良,佐證著浪蕩子里也有好人。
他身體力行地反擊著年少時在村里人嘴里聽到父親的事跡時激起的“我父親是個壞人”的感受。雖然從來沒人說過:“你父親是個浪蕩子,所以是個壞人。”
但他感覺父親一直在他的身體里,那個白衣白馬的父親,那個桃花眼招女人的父親,那個偷聽敵臺的父親……既然如此,又怎能獨獨逃脫那個發瘋的父親?
多年來,張國輝和張國蓮極力避開與父親有關的話題,是否也跟他一樣暗自疑心?
野貓窩里那么多讀書的孩子,只有張國輝考上了清華。野貓窩里那么多愛美的姑娘,只有張國蓮美得不同凡響。張國輝和張國蓮的身體里,是否也殘留了父親的某個部分?十里八鄉唯一的郎中有個上清華的兒子,從早到晚白衣白馬的風流男子有個美貌的女兒,在野貓窩里,這一切要以這種方式才能勉強說得通。他們不太相信一對長相平凡的夫妻能生出個貌若天仙的女兒,兩個智力庸常的農民能養出個考上清華的兒子。張國輝和張國蓮在復制父親超常的智商和外貌時,極有可能也復制了發瘋的潛質。
他們遺傳了父親的好,怎能妄想徹底撇開父親的壞?
五月花開如錦,北京和杭州都預備著擺滿草木的房間,只要母親點個頭而已。可再大的房間也擺不進葬著父親的那片油茶林,母親的頭點不下去。
早些年,美國也預備過這樣的房間,直到張國蓮徹底死心。
“能把那兩畝油茶跟杭州連在一起就好了。”張國蓮意興闌珊嘆了口氣。
張國榮想起大哥說起過有個廣東的朋友在研究數字鄉村,到時候,所有的鄉村和城市都將連在一起。
母親能不能等到那個時候?等到那個時候,又能不能被虛擬的鏈接說服?
父親都走了四十多年了,對母親的陪伴不也是虛擬的么?從這個角度,不知能不能讓母親觸類旁通。
張國榮決定回一次野貓窩里。
那個除夕夜拋下的團年飯總在他心里盤桓。
那之后的每年除夕,他和張國輝都陪著母親在野貓窩里團年。然而那之后的每頓團年飯,都不是那一頓。
他是母親選定了傍身的孩子。這孩子一直在逃,一直逃不出去。
也許張國蓮和張國輝也沒能逃脫出去。所以張國蓮會一回回打了電話來問。張國輝會格外留心朋友研究的數字鄉村。
他們的魂一直困在野貓窩里,不管住多大的房子吃多少西餐喝多少咖啡……特地回去一次,能否將那個魂魄釋放出來?能否,將空置經年的那頓團年飯填滿?
五
“榮伢哩!”聽到有人在后面這樣叫時,張國榮一下沒反應過來。
送他回縣城的同學用手肘碰了碰他的手肘:“是叫你吧?”
近兩年,他時常忘記自己的小名。雖然這個同學和野貓窩里的村民都曾對他以小名相稱。
一個鬢角花白的男子滿懷激情地指了指自己:“華股哩。還記得嗎?我是華股哩。”
腦袋里轉了幾個小圈圈,張國榮想起來,這是他兒時的玩伴,玩伴的臉上布滿了老年斑。
“不年不節的,回來做什么?”華股哩有些興奮地在身上摸來摸去。
“我老娘年紀大了……”
“有七十五六了吧?”華股哩從身上摸出一包煙,抽出一支遞給他,又抽一支遞給他縣城的同學,“便宜貨,抽不抽得慣?”
紅白相間的盒子,是十五塊一包的利群。買整條的話,每包只要十三。
張國榮接過利群咬在嘴里,遞了支七星過去。
三人面對面站在村口抽煙。華股哩眼光躲躲閃閃。張國榮知道,他躲閃的是他左耳的耳洞。為了不引起村民注意,他事先取了耳釘,卻取不了耳洞。那耳洞只有針尖大小,原本毫不顯眼,但落在一個男人耳垂上,在華股哩眼里,就跟耳釘一樣明晃晃的。看得出來他極力不以為意,一次次錯開目光,卻又一次次無功而返。
村口的老樟樹散發著好聞的氣味。張國榮很想說“這棵樹還是老樣子”,然而他只是深吸了一口利群。
年幼時,他和華股哩常在樹下撿樟子。于他來說,老樟樹承載著遙遠的記憶。可華股哩天天看著這棵樹,那樣的話在他面前說起來,有種莫名的別扭。
“山里就是這樣,沒班車。”華股哩有些抱歉似的看著張國榮的同學,仿佛沒班車是他的錯。
“這是黎主任。”張國榮介紹說,“我高中同學。”
黎主任接過話說:“上高中那會兒,我跟張總過來玩過,坐的是摩的。路上的泥巴齊著膝蓋,摩托車顛得跳起來,磕我一臉鼻血。現在好歹通了水泥路,有車就能進得來。”
華股哩顯然意識到了自己在稱呼上的唐突,撓著頭皮說:“是,是。我這土老帽,還‘榮伢哩榮伢哩’地叫。是張總,要叫張總了。”
張國榮去了北京后,這位黎主任就不再叫他“榮伢哩”了,公眾場合改稱“張總”,私下里叫“國榮”。
為了讓華股哩放輕松,張國榮笑了笑:“還是叫我榮伢哩吧,聽著親切。”
這一笑,華股哩更緊張了。張國榮的笑,不像華股哩那樣“呵呵呵”的透著憨厚,也不像有些村民那樣“哈哈哈”的透著爽朗。他輕輕抿著嘴,有種溫文爾雅的味道。這溫文爾雅讓華股哩無從應對,更加用力地撓起了頭皮。
雪白的皮屑飄灑在深藍色Polo衫上,中間夾雜著一兩片痂殼。
張國榮很想幫他拂去肩頭上的皮屑,然而他只是更深地吸了一口利群。
“過年回來怎么沒見著你?”
“前些年在佛山打工,沒舍得回來。現如今年紀大了,這不……被老板辭退了嘛……”華股哩有些訕訕的,噴出兩股粗重的煙。
以煙蓋臉。
三個人都有些訕訕的,以煙蓋臉。
華股哩吸起煙來,嘴角層層疊疊的,像塊千層餅。
張國榮看著他微微發顫的手指夾起香煙,有種觸目驚心的恐懼。那個跟他一般年紀的男子,有了遲暮的氣息。
倏忽數十年,不回野貓窩里,無以丈量時光的深淺。
一支煙的工夫,仿似從頭到尾活了一回。
張國榮舉著抽剩的煙頭左右張望。
“就扔地上,扔地上。”華股哩率先垂范,把自己手里的煙頭扔在地上,用腳跟蹍了蹍。
黎主任和張國榮也依次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蹍了蹍。
有條黃狗搖頭擺尾跑了過來,像小九。張國榮伸手逗了逗:“這狗不錯。”
“這是我家的狗。”華股哩驕傲地說,“整起來夜里吃吧?”
張國榮胃部一陣痙攣,險些嘔吐起來。他悲哀地發現,在北京他是野貓窩里人,在野貓窩里他又是北京人。
黃狗樂顛顛去了,渾然不知一來一去間已歷經過生死之變。
不年不節的,村里沒什么人。年青人外出打工沒回來,老人和小孩縮在房間里看電視。穿過一戶戶屋門半掩的人家,偶見熒屏變換畫面的亮光一閃。
只有幾個跟華股哩差不多年紀的中老年男女在村上走動,扛著鋤頭,或是挑著簸箕。
這些人都認識張國榮,一聲聲喊著“榮伢哩”,跟在他身后,護送瓷器樣地往他家里去。也有一兩個自認為精通世故的,喊他“張總”。
這個年紀在北京,正是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在野貓窩里,只能做些不值錢的雜事。外出打工已經沒人要了。
六
明明是張國榮家,卻由華股哩先推開門,嘴里喊著“后里嬸娘,榮伢哩回來了”,邊喊邊把張國榮往屋里讓,招呼客人樣的。
母親不在家,屋里還是老樣子。
由于張國蓮一生孩子就預備將母親接去美國,張國輝事業穩定后又預備將母親接去杭州,房子一直沒翻新,土夯的地面生起了青苔,房梁上結著蜘蛛網。
張國榮知道黎主任住不慣,主動說:“我也不虛留你了,早晚要回去,不如早些回去。”
黎主任到省城接了機,又從縣城送他回村,也是急著回去,揮揮手說“需要用車的時候隨時找我”就走了,連口茶都沒喝。
張國榮也沒打算泡茶。獨居老人的茶杯,不是誰都用得慣的。
華股哩取下掛在桌子腳上的抹布,擦了擦藤椅上的灰,對著張國榮手里的行李揚了揚下巴:“先把東西放這里吧。”
在北京時,這屋子里的一桌一椅他無不爛熟于心。真到了眼前,卻隔山望海般陌生。好比初學開車那會兒,點火、掛擋、松離合、踩油門在腦海中一氣呵成,真往教練身邊一坐,火也點不著擋也掛不準,折騰了半天車子還在原地。
“曉得你回來了,你娘又不曉得要多歡喜。”隨行眾人各就各位或坐或蹲,倒比張國榮更為隨意。
“還是你們兄弟姊妹幾個有出息,都飛出去了。不像我們,一輩子困在這鳥不拉屎雞不生蛋的地方。”
張國榮唯恐眾人跟華股哩一樣在他面前露出自卑的神情,急忙加以安撫:“現在生活條件好了,野貓窩里的日子也不錯。”
“好什么好?只講吃穿是不錯。吃不飽穿不暖的人家是沒了。可除了一身一體,不是還有子孫后代么?就說我家二妹子,從小歡喜讀書,親戚朋友都提醒我好好培養。我是有心培養,可我買不起學區房啊!在鄉下讀完了六年小學三年初中,連城里老師講課都聽不懂了。等到高考,又沒哪個給鄉下學生加分數。以后還不是進廠打工的命?就不說打工妹多少被人瞧不起吧,光是工廠里這個輻射那個污染,就對身體不好。再說賢茍仔,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兒子啊!這在鄉下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想當初,賢茍仔可是笑歪了下巴的。如今可好,三個兒子都三十多了,一個個身強體壯打著光棍。光娶一個新婦就要二十萬彩禮,三個新婦,賢茍仔的老骨頭恐怕要被啃得渣都不剩了……”
張國榮自幼深信只要長大了就能過上好日子。然而幾百個張國明、張國慶、張國生、張國華……才走出張國輝、張國蓮、張國榮三個。其余的,都跟這些擁在門口的村民一樣,窮極無聊又忙忙碌碌地種幾畝地、栽幾棵菜、撿幾天茶子。他的好日子,并非他心目中自以為是的應許之地。極大的可能,他是跟他們一樣過不上好日子的。
可年少時總是那樣,聽到飛機失事,只要有幸存者,必然認為自己理當是幸存者中的一員。聽到洪災地震,只要有不曾損毀的房舍,必然認為自家的房舍理當是不曾損毀中的一例。任何一個少年,都不會認為自己不配擁有那份幸運。就像張國榮跟著張國輝去抓眼鏡王蛇時,從沒想過有被咬死的可能。
他們兄弟姊妹三人,享受的是幸存者的人生。這讓張國榮惶惑起來,生出一絲莫名的愧疚感。
“張總。”有位村民站起來說,“現在時興精準扶貧,你也扶扶我唄。”
“扶我扶我。”
“野貓窩里,最窮的就是我家了。”
眾人紛紛說笑。
“精準扶貧”四個字在報紙、電視、手機上隨處可見,可落入日常生活的閑談,張國榮還是有些陌生。不在政府部門工作,這類詞匯跟他還是隔了一層。他干笑著,搜腸刮肚想不出一句得體的話來回復。
“你人脈廣,幫我們推銷推銷村里的蕎頭。”
“是啊是啊,前些年鎮里發動我們種蕎頭,起先賣得還好,后來種得越來越多,快要賣不出去了……”
一個開文化公司的,怎么賣蕎頭呢?張國榮有些后悔。過年回來,人人都忙著辦年貨、走親戚、搓麻將……沒人跟他提這些。不年不節的,村里人有的是工夫,只怕要時常纏著他了。他幾次拿起電話想把黎主任叫回來,即刻逃出野貓窩里、逃出縣城、逃回北京。
不尷不尬地瞎扯了一陣,母親回來了,簸箕里挑著兩捧蕎頭。張國榮喉頭一哽,突然就覺得開文化公司也未必賣不得蕎頭。
“先去看看你爺吧。”這是母親跟他說的第一句話。
六月將近,澗流里有了清涼的水汽。冬月的水是暖的,渾濁、遲緩。開了春才活躍起來,洗盡沉垢,越流越清。
水澗環繞著一大灣稻田。田里密密實實的,抽著淡綠的穗子。穗子上掛著芝麻大小的花粒。
穿過這灣水田,就是種滿油茶的山地。
山里的路,一年一個樣。張國榮年年春節去給父親壓歲,年年都要母親領路。
草木瘋長的五月,更要母親領路。
母親在繁雜的草木間疾步如飛。張國榮趕上去說:“我教您老人家上網吧。學會了上網,想跟哪個見面就跟哪個見面。野貓窩里的人,都能拉到一起閑聊。對著手機,就跟在野貓窩里一樣。”
母親問:“看得到你爺么?”
張國榮又說:“等到數字鄉村全面推廣,野貓窩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跟城市連在一起。”
母親又問:“你爺也能跟城市連在一起么?”
張國榮不知道怎么把一座墳跟城市連在一起。那墳里,住著被母親稱為“你爺”的男人。
有位老人扛著毛竹走下山地,竹梢子一顛一顛,歡蹦亂跳似的。老人跟母親一樣,見了張國榮就只有關于他父親的話題:“回來看你爺啊?”
張國榮點了點頭,說不出話。
母親代替張國榮作答:“是啊。砍竹子做竹篙啊?”
“砍竹子做竹篙。”老人隨口應著。
山地里長滿了毛竹、梔子、樹莓、金銀花……每一種植物,張國榮幾乎都能叫出名字。
碎石子硌著鞋底,腳下顛顛簸簸的,草葉在手背上拉出一道道細小的口子。
從什么時候開始,草葉都能割破他的皮肉了?
他與野貓窩里貼得有多近,隔得又有多遠?
草木中有塊表面平滑的青皮麻石,張國榮疑心正是盤過眼鏡王蛇的那一塊。
然而并不是。母親指著麻石后的另一塊巨石問:“還記得這塊銅鼓石么?敲起來嗡嗡響的?”
張國榮記得,銅鼓石跟他們抓過眼鏡王蛇的那塊青皮麻石相距甚遠。
他撿了根樹枝,“嗡嗡嗡”敲了三下。聲似悶雷、色若青銅、形如巨鼓……是他敲過千萬次的銅鼓石。
他不懂精準扶貧,可他懂得野貓窩里的一山一水一磚一石。
七
“別再做來美國的打算了。”張國蓮說,“只怕你這輩子來不了,我也回不去了。”
“想看野貓窩里的照片么?我上次回去拍了好多。”
“看看吧。微信還是郵箱?”
“微信吧。”
張國榮端著綠茶撩開紗窗往外望了望。公司樓下有塊小場地,以往來得早時,偶爾會碰上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大爺大媽興沖沖拍了視頻發抖音。
也許該教野貓窩里的村民用抖音賣蕎頭。張國榮看著一張張照片在他和張國蓮的對話框里依次顯示。
【作者簡介】歐陽娟,生于1980年12月;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中國作家》《長篇小說選刊》等刊,著有長篇小說《深紅粉紅》 《路過花開路過你》《交易》《手腕》《最后的煙視媚行》《婉轉的鋒利——林徽因傳》等;現居江西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