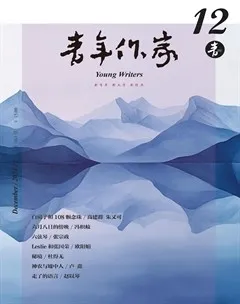我們無從掙脫的遺跡
我們泡酒吧,我們蹦野迪,我們開豪車,住在種滿花草的大房子里……我們不是我,是那樣的一群人。他們看上去與父輩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在風華正茂的年輕時代也曾有過與原生家庭徹底割裂了的錯覺。然而,某個宿醉醒來的清晨,某個秋涼乍起的黃昏,甚或某個利潤豐厚的項目談成時,很久很久以前的很多東西突然一下子全部回來了。回來了,覆蓋那個自以為全新的自己,剝露出銹跡斑斑的靈魂。
我曾經看到他哭。在后海的酒吧里,喝著芝華士十二年,聊著埃米爾·庫斯圖里卡,優雅中帶著舍我其誰的表情。電話響起,舉到耳邊接聽,嘴唇不期然抽動起來,蒙蒙的眼淚在眼眶里轉啊轉、轉啊轉,轉到電話掛斷。抱歉中又帶著兩分尷尬向我解釋:“我媽啊,是我媽……”接著轉開臉去,面對一個我無法觀察表情的位置。
我也曾經看到過他暴怒。在臨江的旋轉餐廳,吃著法式料理,展望著未來兩年的風光前景。接了幾個微信,意氣風發的表情芝士焗飯一樣逐漸變冷、變硬。“我爸啊,真特么……真牛叉。”欲言又止的怒火,漫無目的旋轉著手機,然后“啪”一聲掀翻椅子,頭也不回地離席。
我還看到過他、她、他……他們在我面前呈現出與平日截然相反的一面。因為寫作者的身份,我有幸傾聽了他們的故事。
《Leslie和張國榮》寫的就是他們的故事。故事純屬虛構。即便故事是真,我也絕不承認。他們的故事,注定無人認領。那是傷痛,而非榮耀。在文字虛構的情節里,他們才敢于袒露真心,褪去光怪陸離的掩飾。
他們新造了一個自己,耗費十年、二十年,甚至半輩子的生命。然而他們一直在那里,在那個舊的靈魂里,在那個弱小的身體里。他們走遍天南地北,走不出呱呱墜地的那幢老宅。
他們無從掙脫祖輩留下的遺跡。不是無法,而是無從。母親站在門口目送的眼神,鋪天蓋地,自何處掙脫起?父親賜予的姓氏,冠在名前,待何時拋得開?母親也有母親掙不脫的眼神,父親亦有父親拋不開的姓氏。父母將層層疊疊的眼神與姓氏交付到他們手里。于是他們兒時養過的那條狗、游過泳的那口塘、打過的那一板梭子……都疊加了祖祖輩輩的眼神與姓氏。
平地里蓋高樓,地基有多深,高樓才能有多穩。他造不出一個全新的自己,他是深不見底的地基托舉出的生命。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誤以為自己只由自身所擁有的一切構成,待到某種特質在肉體上復蘇、某種聲音在心靈深處響起,越來越疾、越來越密,才發現地基始終跟自己緊緊聯結在一起,地基亦是自身的一部分。
他一個人跑不了,于是折轉身,跟他們一起。
他們一起。一步一步。向前走。或者折轉身,再去帶上那些走得更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