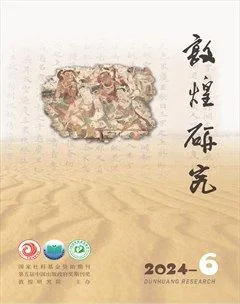漢簡所見官記文書考論






內容摘要:官記屬于漢代官文書的一類,在郵書傳遞記錄中除單獨稱記外,還根據發文單位、傳遞方向、材質、功用等的不同,又稱為府記、候官記、置記、東記、楊記、還記等。官記文書大致有三種格式,其文書形式隨著時代的演變逐漸變得正式,威信和法律效力亦得到加強。官記文書格式用語簡化,使用簡捷,可快速傳達上級教令,提高行政效率,是漢代行政機構中日常使用較多的一種文體,在文書行政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漢簡;官記;文書行政
中圖分類號:K87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6-0138-10
A Study on the Official Ji Documents i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CHENG Fanjuan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Ji記documents were an official type of document in the Han dynasty, which included fu ji府記, houguan ji候官記, zhi ji置記, dong ji東記, yang ji楊記and huanji還記, the contents of which varied based on the issuing organization, direction of transmission, physical material and intended function. There were roughly three forms of official ji documents, which gradually became increasingly formalized over time and gained greater authority and legal efficacy. Both the format and the wording of ji documents were greatly simplifie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official documents, and therefore the orders made by various government employees could be issued quickly, which improved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ese documents were used quite frequently in the daily functioning of the Han dynast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ocumenta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time.
Keywords: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official ji documents; documentary administration
文書行政是漢代國家治理和日常行政管理的基本形式,東漢人王充“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的表述[1],就是對官文書所發揮作用的高度概括。簡牘所見諸文書名稱有書、檄、記、教、傳、致、律、令、品、式、條、案、錄、刺、課、劾狀、辭、符、券、莂、簿、籍、計、算、名、檢、卷等,尤以書、檄、記、律、簿、籍最為常見[2]。相對于其他官文書種類,目前學界對漢代官記文書關注不夠。東漢有俚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3]官記文書在漢代文書行政中所起的作用值得十分重視。
學者們圍繞漢代的“記”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對“記”含義的討論與分類。記所記述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表記錄、記載,類似于志記的作用;二是傳達私人之間的事務,是私人間的書信,可稱為私記;三是作為官文書的記,是官府間的行政往來文書,可稱為官記{1}。簡牘材料所見的官記文書基本為官府間的下行文書,本文即以此類文書為研究對象。簡牘郵書記錄中有較多關于記的記載,對于其所反映的官記稱謂學者們并未論及。
其二,對官記文書程式和特點的討論。學者們在具體辨別何為官記文書時有一些爭議。汪桂海認為記文書在起首表示行文關系的文字皆作“府(或官)告某官”,由此將“告”字作為推斷記文書的依據[4]。■飼昌男則認為無“如律令”而有“毋以它為解”句子的下達文書可以視為記[5]。劉寒青將記的一般格式總結為:某月XX(干支),XX(官/府)告/謂/召XX,某事[6],但這一格式未收錄五一簡等材料,且未關注到記的體式變化。隨著簡牘材料的增多,對于官記格式的總結可進一步細化,并探討官記體式的變遷。
其三,對于官記性質功能的討論。李均明認為官記是較書、檄隨意的通行文書形式,功能與書、檄相同[7]。鷹取祐司認為記基本用于私事,是具有靈活性的文書,但是在傳達內容的重要性和約束力上與書、檄沒有區別[8]。■飼昌男認為相比書、檄,記是法律約束力較弱的文書[5]。高村武幸將“記”“教”“奏事”“白事”等簡牘統稱為“公文書性質的書信”,認為其適用于尚待決議的事項[9]。各位學者對官記的性質功能意見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簡牘材料對諸家意見進行辨析,從而對官記文書的存在與稱謂,官記文書的體式和變遷,官記與其他文書之間的關系以及官記在文書行政中的作用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 官記文書的存在與稱謂
由于記涵蓋內容較廣,官記是否是官文書曾引起質疑。陳槃認為記是漢人書牘的統稱,記之體式為公為私都無一定[10]。高村武幸從書信這一視角出發,將簡牘中的“記”“教”“奏事”“白事”等稱之為“公文書性質的書信”{2}。筆者認為官記應屬于漢代官文書的一種。
“記”作為官文書,在傳世文獻里屢見。如《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11],此為郡太守直接向亭長下記。《漢書·何武傳》記載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谷美惡”[12]。《后漢書·鐘離意傳》載鐘離意“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人受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13]。《后漢書·宋均傳》載宋均“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14]。
除了傳世文獻的記載,簡牘材料的郵書記錄中亦屢見記的傳送記錄:
1. 四月廿一日記一左掾私印詣肩水候官四月己未日
北記一昏時遣" 506.19[15]
2. 第十七候史張宗持府記尉檄詣官三月戊午晡時入" EPT43:5[16]
3. 出東書四封敦煌大守章
一詣勸農掾一詣冥安一詣廣至一詣淵泉
一詣勸農史一詣淵泉
府記四鮑彭印一詣冥安一詣宜禾都尉
一詣廣至合檄一鮑彭印詣東道平水史杜卿
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時縣泉置佐忠受廣至廄
佐車成輔·即時遣車成輔持東
Ⅱ90DXT0114{2}:294[17]
4. □楊檄一還記一
府一封冥安
□長史二封酒泉■
□長印一封詣西域
Ⅰ90DXT0111S:34[18]
5. ■詣府
檄一冥安長印詣令史張猛在敦煌界中
置記一詣府
十月壬辰莫食世付樂望卒卬
Ⅱ90DXT0112{2}:23[19]
6. 出西書三封置記二
二封詣府一封冥安長印
一封酒泉大守章一封毋印章詣敦煌十二月癸酉大農付樂□卒印卩" 1291[20]
7. 出東記三其二左掾印一詣冥安其一毋章詣戶曹史吳憲十月丁巳夜過半時■
Ⅱ90DXT0114{3}:57A
丁巳夜過半時付
Ⅱ90DXT0114{3}:57B[17]399
8. 東記一印曰林舒國印詣冥安守令合歡在所五月戊申夜過人定時縣■
Ⅱ90DXT0114④:388[17]529
9. 出合檄一楊記一皆詣原掾治所
建平三年五月辛酉日下夕時縣泉御張宮付魚離置佐郭鳳Ⅱ90DXT0113{2}:34A
下夕(左齒半字)
Ⅱ90DXT0113{2}:34B[19]592
10. 出東楊記十二皆司馬■
Ⅱ90DXT0114{1}:73A[17]343
11. 出西書三封還記一詣府二□一封■楊□
Ⅱ90DXT0111{1}:229[19]460
以上官文書的郵書記錄中,“記”“書”(簡3、簡6、簡11)或“記”“檄”(簡2、簡4、簡5、簡9)出現在同一份文書傳送記錄中。由此可見,記應是和“書”“檄”不同的文書類別,并也屬于官記文書的一種。記類文書在郵書傳遞記錄中除單獨稱記外,還根據發文單位、傳遞方向、材質、功用的不同,被稱為府記、置記、北記、東記、楊記、還記等。
府記為太守府或都尉府發出的文書,官記為候官發出的文書,置記可能是懸泉置這樣的機構發出的文書[21],“府記”“官記”“置記”是以發文單位來命名的“記”文書。“東記”是以“記”文書的傳遞方向來命名的,即東行方向的記。“楊記”有學者提出可能是以楊木為質材而書寫的記[22]。
“還記”具體是何種記,《說文解字》載:“還,復也。”段玉裁引《爾雅·釋言》注曰:“還,復返也。”[23]還有返還之意。《后漢書·鐘離意傳》載鐘離意:“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人受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后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13]1406郡督郵鐘離意對府記命令提出異議,將記返還給府。《漢書·薛宣傳》也有“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的記載[24]。官吏如果對記所下達的命令有所異議或不服,可以將其返還,此種記或稱為還記。
除了郵書記錄,文書楬中也可見官記文書的存在。文書楬又稱文書簽牌,其頂端大多呈黑色網格狀,用作已歸卷入檔文書的標簽。
12. 建昭二年十月
■盡三年九月吏
受府記" EPT51:151A
建昭二年
■十月盡三年
九月吏受府記" EPT51:151B[25]
13. 建武五年十一月以來
告部檄記算卷" EPF22:408[26]
上述兩枚文書楬,一枚是西漢建昭二年(前37)十月至建昭三年(前36)九月一年來甲渠候官接受其上級機構居延都尉府下發的記文書,一枚是東漢建武五年(29)十一月以來甲渠候官下發給其所屬候部的檄、記、算、卷等文書,言十一月以來,且檄、記、算、卷等文書放在一處,似乎到目前為止這份案卷尚未建立完畢,新的同類文書仍在不斷加入此標簽中[4]212。簡牘材料中有“……臧記令可課483”的表述[27],記文書也像其他官文書一樣需要立卷存檔以備考課查驗。由以上傳世文獻、郵書記錄、文書楬的記載表明,官記文書也是官文書的一種。
二 官記的文書程式與變遷
使文書行政發揮有效功能方面,最重要的是文書必須要有固定的形式和格式。沒有固定格式的文書,即便內容相同,也不能有效發揮功能,甚至不具備文書的可信性[28]。簡牘通行文書程式,通常包含標題、日期、發件人、收件人、正文、起草人、附件等要素[2]143。在這些要素的提示下,官記文書的程式用語體現出與其他通行文書不同的特征。筆者經過整理辨析,現將體式比較完整的官記文書分成三類移錄如下:
14.元延二年十月壬子甲渠候隆謂第十候長忠等記到各遣將廩" 214.30[29]
15.九月辛巳官告士吏許卿記到持千秋閣單席詣
府毋以它為解" 988A
士吏許卿亭走行" 988B[27]328
16.四月戊子官告倉亭隧長通成記到馳詣府會夕毋以它為解急□□
教" 1065A
□署□□令□
倉亭隧長周通成在所候長候史馬馳行
記□日一□" 1065B[27]340
17. 十二月甲辰官告千秋隧長記到轉車過車
令載十束葦為期有教" 1236A
千秋隧長故行" 1236B[20]266
18. 五月戊午官告士吏索下當谷隧長記到□吏持
方□□□日不驗調官食入毋以□□□□□" 1831A
卻適士吏當谷隧長亭次走行
1831B[20]290
19.六月甲戌玉門候丞予之謂西塞候長以可得將候候長福將□候長□等記到課
望府檄驚備多虜黨來重正甚數毋令吏卒離署持七月府記將卒稟毋忽臧記令可課
483A
西塞以記遣" 483B[27]259
20.五月丙子士吏猛對府還受……●有所驗□□□
府五官張掾召第十候史程并記到便道馳詣府會丁丑旦毋得以它為解
99ES16ST1:11A
第十候史程并行者走
99ES16ST1:11B[30]
21. 九月癸亥官告第十七候史為官買羊至今不來解何記到輒持羊詣官會今毋后都吏
……" 2000ES7SF1:16[30]149
22. 三月壬申官告第四候長孤等府記省卒卌二人遣士吏就將領之廣地
59.32+59.33[31]
23. □□癸卯官告第四候長記到馳詣官會
毋以它為解急□[董]云叩頭唯卿幸為持具簿奉賦急" 113.12A
第四候長行者致走□□□哀憐罰鐵者頃蒙恩叩頭叩頭" 113.12B[32]
24. 六月辛未府告金關嗇夫久前移檄逐辟橐他令史
解事所行蒲封一至今不到解何記到久逐辟詣" 183.15A
會壬申旦府對狀毋得以它為解各署記到起時令可課
告肩水侯=官=所移卒責不與都吏趙卿所舉籍不相應解何記到遣吏相抵校及將軍未知不將白之" 183.15B[32]210
25. 三月辛未府告骍北亭長廣
與俱車十六兩馬三匹·人廿八□■
73EJT23∶349A
府記予骍北亭長■73EJT23:349B[33]
26.官告第四候長徐卿鄣卒周利自言當責第七隧長季由
百記到持由三月奉錢詣官會月三日有
285.12A
長徐卿" 285.12B[29]227
27.官告吞遠候長黨不侵部卒宋萬等自言治壞亭當得
處食記到稟萬等毋令自言有
教EPT51:213A
記吞遠候長黨" EPT51:213B[25]246
28. 官告候長輔上記到輔上馳詣官
會晡時輔上行與廿一卒滿之
EPT56·88A
詣官欲有所驗毋以它為解。
第十七候長輔上故行" EPT56·88B[34]
29.官告誅虜守候史褒次當候虜井上記到莊詣" 263A
官候重事毋以它病為解有
教●隧長西貸食" 263B[27]225
30.告第廿三候長記到召箕山隧長明詣官以急疾為故急急" 160.4[32]150
簡14—30為官記文書的第一種格式:(某年某月某時)某告/謂/召某下屬……記到……(毋以它為解/有教)。此種形式的官記文書具文時間較為省略,多為某月某日,有時則省略日期。簡14“元延二年十月壬子”寫明了年月日,但僅見一例。簡15—25的開頭僅署月序及日干支,簡26—30則省略具文時間。
表明發文時間之后,會寫明發文者與收文者。關于發文一方,未寫明具體的責任機構或責任人,大多僅署“府告”“官告”之類[2]267,有時還會省略發文單位,起首僅署“告”字,如簡30。關于收文一方,多為府或官的下屬,一般會具體到收文者職官個人,如簡15“官告士吏許卿”、簡24“府告金關嗇夫久”等。
官記文書在表示行文關系的動詞選用上,“告”字出現頻率最高,還有用“謂”(簡19)和“召”(簡20)的,但僅見此各一例。《釋名·釋書契》載:“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35]“告”一般用于下行文書。汪桂海將“告”字作為推斷“記”文書的依據[4]51,但有學者指出,單純以簡文中是否出現“XX告XX”的格式來判斷是否是“記”文書是不嚴密的,在其他形式的文書中“XX告XX”這樣的格式也是常見的[6]。例如:“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丙午,居延令、丞審告尉謂鄉移甲渠候官聽書從事,如律令。”(EPF22.56A)這份文書并不是“記”文書。
在表明發文者與收文者之后,一般會出現“記到”二字,表明此文書為記文書。在“記到”之后,則是上級機構下達的具體指令。下達的指令多為“詣府”(簡15、16、20)、“詣官”(簡21、23、26、28、30)等召會通知。召會即召喚相關吏員來官府會面,行政實踐中召會主要用于限定辦事的時間與空間,是實現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36]。除召會通知外,還有一些具體的指令:如“遣將稟”(簡14)、“毋令吏卒離署,持七月府記將卒稟,毋忽,臧記令可課”(簡19)、“轉車過車令載十束葦”(簡17)、“數循行,教敕吏卒明■火、謹候望,有所聞見亟言”(簡32)等,多為領取糧食、載葦草、加強戒備等日常行政事務。
下達指令以后,則以“毋以它為解”(簡15、16、23、28)、“毋得以它為解”(簡20、24)、“毋以它病為解,有教”(簡29)、“有教”(簡17、27)等文書用語結尾,承接前面講述具體命令的語句。■飼昌男認為無“如律令”而有“毋以它為解”句子的下達文書可以視為記[5]。但由上述所列記文書可見,其結束語不止“毋以它為解”,還有其他多種形式,因此不能將“毋以它為解”作為判斷記文書唯一的依據。
上述官記文書均是下行文書,但存在越級下達的情況。如簡16“四月戊子,官告倉亭隧長通成,記到,馳詣府,會夕,毋以它為解,急==□教1065A”“倉亭隧長周通成在所,候長候史馬馳行記□日一□1065B”,簡17“十二月甲辰,官告千秋隧長,記到,轉車過車令載十束葦,為期,有教1036A”“千秋隧長故行1236B”,這兩件記文書是候官直接給隧長下達命令,而越過了候部這一級,一般官文書均是逐級下達,越級下達命令體現了官記文書的緊急變通性。
以下官記文書與第一種官記文書格式稍異,列舉如下:
31.廷告西部候史臨前兼南部今罷守左后候長有" 73EJT3:118A
教" 記綏和二年三月己卯起廷
73EJT3:118B[37]
32.府告居延甲渠卅井殄北鄣候方有警備記到數循行教敕吏卒明■火謹候
望有所聞見亟言有教 建武三年六月戊辰起府" EPF22:459[26]295
33. 甲渠鄣候以郵行
府告居延甲渠鄣候卅井關守丞匡十一月壬辰檄言居延都田嗇夫丁宮祿福男子王歆等入關檄甲午日入到府匡乙未復檄言
EPF22:151A
男子郭長入關檄丁酉食時到府皆后宮等到留遲記到各推辟界中定吏主當坐者名會月晦有" EPF22:151B
教建武四年十一月戊戌起府
EPF22:151C
十一月辛丑甲渠守候告尉謂不侵候長憲等寫移檄到各推辟界中相付受日時具狀會月廿六日如府記律令" EPF22:151D[26]242-244
簡31、32、33為官“記”文書的第二種格式:某告某下屬,記到……毋以它為解/有教,某年某月某時起某。第二種格式的官記文書與第一種格式的官記文書相比,文書用語基本相同,但發文日期更加精確且寫在了文末。如:“記綏和二年三月己卯起廷”“建武三年六月戊辰起府”“建武四年十一月戊戌起府”,紀年依次為公元前7年、公元27年、公元28年。
34.府告臨湘前卻詭課守左尉傿梵趣逐捕殺鄉佐周原男子吳主主子男
□賊王傅烝于烝尊不得遣梵詣府對案傅于尊共犯桀黠尤無狀梵典負被書受詭逐捕
訖不悉捕得咎在不以盜賊責負為憂當對如會以傅已得恐力未盡冀能自效且復假期記
到趣詭課梵逐捕于尊復不得遣梵詣府對會七月廿日勉思方謀有以自效有
府君教
長沙大守丞印延平元年五月十九日起府
一一四二+一二四一
2010CWJ1{3}:264-296+264-395[38]
35.府告臨湘前卻趣詭課左尉邽充守右尉夏侯弘逐捕殺小史周諷男子馮五
無什及射傷鄉掾區晃佐區期殺弟賊李湊劫女子王綏牛者師寇蔣隆等及吏殺民賊朱祉董賀
范賀亭長袁初殷弘男子王昌丁怒李高張恭及不知何四男子等不得令充弘詣府
案祉賀
初昌怒寇高四男子等所犯皆無狀當必禽得縣充弘被書受詭逐捕連月訖不捕得
咎在不以盜賊責負為憂當皆對如會恐力未盡且皆復假期記到縣趣課充弘逐捕祉
賀高隆四男子等復不發得充弘詣府對會十六年正月廿五日令卅日勉思謀略有以自效有
府君教長沙太守丞印永元十五年十二月廿日晝漏盡起" 二一CWJ1{3}:291[39]
36.府告兼賊曹史湯臨湘臨湘言攸右尉謝栩與賊捕掾黃忠等別問僦趙明宅
者完城旦徒孫詩住立詩畏痛自誣南陽新野男子陳育李昌董孟陵趙□□等劫殺明及王得
等推辟謁舍亭例船刺無次公等名縣不與栩等集問詩詩自誣無檢驗又詩辭于其門聞
不處姓名三男子言渚下有流死二人逐捕名李光陳常等自期有書案□移湯書詩辭
者不欲實事記到湯縣各實核不相應狀明正處言皆會月十五日毋佝擊無罪
毆擊人有
府君教
永元十五年五月七日晝漏盡起府
五月九日開" 一一七CWJ1{3}:285[39]39
簡34、35、36為官記文書的第三種格式:某告某下屬……記到……有府君教,某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起。這三件官記文書均以“府告”開頭,長沙太守府首先引述了臨湘縣此前關于案件內容的匯報,中間“記到”之后是太守府針對案件向臨湘縣下達的具體指令:如簡34“趣詭課梵逐捕于、尊,復不得,遣梵詣府對,會七月廿日,勉思方謀,有以自效”、簡35“縣趣課充、弘,逐捕祉、賀、高、隆四男子等,復不發得,充弘詣府對,會十六年正月廿五日令卅日,勉思謀略有以自效”、簡36“湯、縣各實核不相應狀,明,正處言,皆會月十五日。毋佝擊無罪,毆擊人”,最后以“有府君教”結尾。且在文末詳細注明記文書的發送時間“延平元年五月十九日起府”“永元十五年十二月廿日晝漏盡起”“永元十五年五月七日晝漏盡起府”,前者為公元106年,后二者為公元103年。
第三種格式的官記文書與前兩種格式相比,行文更加正式繁密。為了顯示郡府的威嚴,開頭“府告”的“府”字最后一筆拉長,占筆較多,字形較大。結尾“府君教”提行頂格書寫,不僅表示對郡太守的尊崇,還可以通過郡太守突出文書的重要性,以此引起責任官吏的重視,同時表明此記雖然是以郡府名義發出的文書,但實際上體現了郡太守的行政意志[40]。精確記錄文書發送時間,無省略日期的情況。記錄發文機構的印文信息,以發文機構的佐官之印封印文書。完整的簡34、35正文顯示有“長沙太守丞印”,簡36上部殘缺,雖無印文信息,但有另筆書寫的“五月九日開”潦草大字,說明該文書確實經過封緘后傳遞,所封之印也應為太守丞印。長沙太守丞依太守命令成文后,以太守府名義直接發送給收文者,發文程序快捷。
上引前兩種格式的西北簡的官記文書正文中均未寫明發文機構的署名或長官用印,僅以“府”或“官”的機構名自稱。郵書記錄顯示西北簡中的記文書多以屬吏之印或私印封印;也有不封印的情況,如簡1“記一,左掾私印詣肩水候官”,簡3“府記四,鮑彭印”,簡7“出東記三,其二左掾印,一詣冥安,其一毋章詣戶曹史吳憲”,簡8“東記一,印曰林舒國印,詣冥安守令合驩在所”。
隨著時代的演變,官記文書的形式逐漸變得正式,但還有使用簡便的特性。首先,未見文書起草人署名。起草人信息通常位于正文之后或簡背[7]134,這三類格式的記文書,均未見起草人署名。其次,從文書形態上來說,官記文書常使用單獨簡,牘較多,也使用檄[41]。觀察官記的文書形態,似乎沒有標準的對應形制,文書內容書寫在單一載體上,不與其他簡編聯,常由單獨一枚簡構成一份文書。簡34、35均為木牘;簡36應為合檄{1},但簡身不完整,上部凸起的部分殘缺。這三枚簡于簡身兩側刻槽,以利直接綁封檢加封泥蓋印后發送出去。這種單一簡牘具有使用簡便,信息集中的特征。
三 官記與漢代的文書行政
秦漢時期國家行政事務均要憑借文書進行處理,出土的云夢秦簡秦律中有明確規定:“有事請殹(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42]由于文書行政的發展,到東漢時代統治者倡導“文書調役,務從簡寡”[43]。漢帝國長久支撐著集權國家的架構,而維持和強固國家政治軀體的血液和血流正是文書行政[44]。具體的文書行政過程中,針對不同的行政需求,會選用不同種類的官文書。李均明將秦漢簡牘文書分為書檄、律令、簿籍、錄課、符券、檢楬六大類,根據是否具有通行性,將書、檄、記、教、傳、致等劃歸到書檄一類[7]8。官記文書具體在漢代的文書行政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需要關注它的性質功能及其與其他書檄類文書之間的關系。
部分官記文書以“有教”或“有府君教”結尾,因此大多數學者將“記”與“教”聯系起來,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目前有三種看法:漢代作為下行文書的“記”又可稱為“教”,“記”與“教”實際上是一種文書的兩個名稱[4]51;“有教”意為在“記”文書之外另有“教”作為附件[45];“有教”“有府君教”是記文書結尾的慣用語,可以將其理解為“此為教令”,其性質與其他文書中的“如詔書”“如律令”等相同,屬于一種在視覺上凸顯命令的絕對性和文書的權威性的結束語[44]157。
《說文解字》載:“教,上所施,下所效也。”[23]128《文心雕龍·詔策》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46]“教”乃官府或長上對臣下的規范或告諭。有學者指出,漢代日常行政中的“教”,有口頭傳達和文書傳遞兩種方式:在距離較近的官府內部機構,長官很多時候以口頭指示的方式傳達教令;當信息傳遞距離較遠,或相關事務比較重要,為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就需要將“言教”制作成文書進行傳達[40]466-468。這種形成文書的“教”或是官記文書,即長官的教令以官記文書的形式下達。
從官記文書所下達的教令內容來看,其多為“詣府”“詣官”等召會通知,除召會通知外,還有一些具體的指令,如領取糧食、載十束葦、加強巡行戒備、抓捕罪犯等日常行政事務。官記文書在“記到”之后已清楚表明上級的教令內容,似無須再另加附件“教”傳送。
筆者認為,長官的教令是以官記文書的形式下達,但官記文書和“教”不能完全等同。在簡牘材料中,與“教”相關的文書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上文所述官府所下之“記”文書,文末有“有教”或“有府君教”,意為長官教令;另一類是屬吏呈請長官批示的文書,一般頂格書寫“君教”或“君教諾”,“君教”意為請君給予教令批復,“諾”字則表示了上級同意認可的簽署[47]。像這類呈請長官批復的“君教”文書則不能與下行的官記文書等同。且“教”應該不像記文書是一種特定的文體,在相關文書傳遞記錄和文書表述中并不見“教”的傳送記錄和“教到”這種表述,因此不能完全將“記”和“教”等同。
簡牘通行文書程式,通常包含標題、日期、發件人、收件人、正文、起草人等要素。官記文書的程式用語體現出與其他通行文書不同的特征,其文書體式相較正式的書檄簡略,具體可歸納如下:官記文書中的時間記載較為簡省,只記月日或無日期記載,后期在文書末記有“某年某月某日起”,書、檄的日期會寫年月日,一般不會省略;官記文書未署具體的責任機構名稱或責任人,僅以“府”或“官”的機構名自稱,書、檄發文以長官或長官與副官聯名發文;官記文末多以“有教”“毋以它為解”“毋以它為解有教”“有府君教”等結尾,書、檄大多以“如律令”“如某書律令”結尾;官記文書末尾未見起草人署名,書、檄文末有文書起草人署名{1}。
官記文書是上級下達教令的一種便捷方式,其簡便性不僅體現在文書程式上,還表現在文書形態和處理流程上。官記文書程式一般只保留發件機構、收件人、正文等主要因素,發文日期適當減省,標題、起草人等相關要素則省略不見。官記的文書形態,似乎沒有標準的對應形制,文書內容常寫在單一載體上,不與其他簡編聯,由單獨一枚簡構成一份文書,信息集中且使用簡便。官記文書未見長官署名或用印,屬吏或依長官教令成文后,以官府名義直接發送給收文者,發文程序快捷。一般官府文書為逐級下達,而官記文書則存在越級下達政令的情況,更體現其快捷變通性。
結 語
秦漢時期有著系統規范化的公文制度,公文種類繁多,強大的文書行政體系維系著國家治理和日常行政管理。在具體龐雜的文書行政過程中,既要合乎規范,又要講求效率。以漢代簡牘所見諸通行文書名稱,除了正式的書、檄外,還有官記這類的簡便文書。官記文書格式用語簡化、體裁短小、使用簡便,可快速傳達上級教令,提高行政效率,是漢代行政機構中日常使用較多的一種文體,雖處于輔助行政溝通的地位,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官記文書的形式隨著時代的演變逐漸變得正式,其威信和法律效力亦得到加強。東漢有俚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3]地方官府對州郡長官的命令文書的執行效率竟可比擬皇帝的詔令文書。特別是東漢時期,隨著地方勢力的增強,官記文書作為地方長官傳達教令的一種便捷方式,其權威性和高效性更加提升,在日常行政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王充. 論衡校釋[M]. 黃暉,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516.
[2]李均明,劉軍. 簡牘文書學[M].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85-209.
[3]崔寔,仲長統. 政論校注 昌言校注[M]. 孫啓治,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186.
[4]汪桂海. 漢代官文書制度[M].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47-51.
[5]■飼昌男,著. 徐世虹,譯. 關于漢代文書的一點考察——“記”這一文書的存在[G]∥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2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23.
[6]劉寒青. 釋漢簡中的“記”[J]. 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120.
[7]李均明.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09-111.
[8]鷹取祐司. 簡牘所見文書考:書·檄·記·符[M]//冨谷至. 邊境出土木簡的の研究. 京都:朋友書店,2003:119-160.
[9]高村武幸. 秦漢簡牘史料研究[M]. 東京:汲古書院,2015:45-48.
[10]陳槃. 漢晉遺簡識小七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
[11]班固. 漢書:第76卷:趙廣漢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62:3203.
[12]班固. 漢書:第86卷:何武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62:3483.
[13]范曄. 后漢書:第41卷:鐘離意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65:1406.
[14]范曄. 后漢書:第41卷:宋均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65:1412.
[15]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肆)[M].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157.
[16]楊眉. 居延新簡集釋(二)[M].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163.
[17]甘肅簡牘博物館,等. 懸泉漢簡(叁)[M]. 上海:中西書局,2023:389.
[18]甘肅簡牘博物館,等. 懸泉漢簡(壹)[M]. 上海:中西書局,2019:414.
[19]甘肅簡牘博物館,等. 懸泉漢簡(貳)[M]. 上海:中西書局,2020:535.
[2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漢簡[M]. 北京:中華書局,1991:268.
[21]胡平生,張德芳. 敦煌懸泉漢簡釋粹[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4.
[22]王錦城:西北漢簡所見郵書的類別及相關問題考略[J]. 古代文明,2017(3):89.
[23]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13:72.
[24]班固. 漢書:第83卷:薛宣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62:3387.
[25]李迎春. 居延新簡集釋(三)[M].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228.
[26]張德芳. 居延新簡集釋(七)[M].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286.
[27]張德芳.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M].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259.
[28]冨谷至. 漢簡語匯考證[M]. 張西艷,譯. 上海:中西書局,2018:28.
[29]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叁)[M].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14.
[30]魏堅. 額濟納漢簡[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78-79.
[31]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壹)[M].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191.
[32]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貳)[M].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23.
[33]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 肩水金關漢簡(貳)[M].上海:中西書局,2012:163.
[34]馬智全. 居延新簡集釋(四)[M]. 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207.
[35]劉熙. 釋名[M]. 任繼昉,劉江濤,譯注. 北京:中華書局,2021:446.
[36]李均明. 居延漢簡召會考[G]//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牘學研究:第4輯.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86.
[37]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 肩水金關漢簡(壹)[M].上海:中西書局,2011:78.
[38]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叁)[M]. 上海:中西書局,2019:137.
[3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M]. 上海:中西書局,2015:8.
[40]凌文超. 黃蓋治縣:從吳簡看《吳書》中的縣政[G]//“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3分. 臺北:2020:471.
[41]角谷常子. 中國古代下達文書的書式[G]//簡帛研究二〇〇七.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78-179.
[42]陳偉. 秦簡牘合集(壹)[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146.
[43]范曄. 后漢書:第1卷:光武帝紀[M]. 北京:中華書局,1965:62.
[44]冨谷至. 文書行政的漢帝國[M]. 劉恒武,孔李波,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349.
[45]佐藤達郎. 關于漢魏時代的教[M]//法律文化研究:第六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62.
[46]劉勰. 文心雕龍校注[M]. 黃叔琳,注. 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 北京:中華書局,2021:289.
[47]陳松長,周海鋒. “君教諾”考論[M]//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上海:中西書局,2015:325-330.
{1} 黃金貴認為“記”的本義是記載、記錄,也即疏記,參見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59頁;李均明提出“記”分為官記和私記,官記的功能與書、檄同,私記是私人信件,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09—113頁;楊芬將“記”分為官記、官場私記、私記三類,參見楊芬《西北漢簡中所見的“記”》,《學習月刊》2008年第20期,第29—30頁;劉寒青將漢簡中的“記”分為官記、私記、物品記錄三類,參見劉寒青《釋漢簡中的“記”》,《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第116—124頁;何祿凱提出在先秦文獻中,“記”通常指的是歷史事件、先例或有權威性知識的記錄,西漢時期,這些記不僅是下行命令,也包含筆記和信件,參見Luke Habberstad,“Notes on the ‘Note’(JI記) in Early Administrative Texts,”Early China,Vol. 45,
2022,pp.135-165。
{2} 高村武幸所謂“公文書性質的書信”,可以分為“一般書信形式”的“公文書性質的書信”與“定型化”的“公文書性質的書信”兩大類別,后者是否屬于“書信”較具爭議。“府記”“官記”及“叩頭死罪敢言之”等文書視為公文書似無不妥。參見劉寧欣《高村武幸〈秦漢簡牘史料研究〉評介》,《簡帛研究·二〇一九秋冬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327—328頁。
{1} 參見鄔文玲《“合檄”試探》,《簡帛研究·二〇〇八》,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2—173頁;何佳、黃樸華《東漢簡“合檄”封緘方式試探》,《齊魯學刊》2013年第4期,第45頁。
{1} 相關研究參見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第267頁;角谷常子《中國古代下達文書的書式》第165—180頁;鷹取祐司:“記”條,冨谷至編、張西艷譯《漢簡語匯考證》,第106頁;劉寧欣《漢代政務溝通中的文書與口頭傳達:以居延甲渠候官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2018年,第488頁。
收稿日期:2024-03-01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家治理視域中西北漢代官文書簡牘形制研究”(22AZS001)
作者簡介:程帆娟(1995—" ),女,甘肅省莊浪縣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秦漢史和簡牘學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