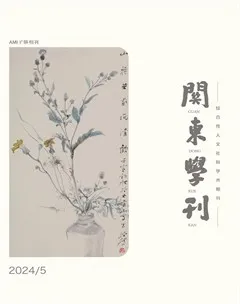姚莘農英譯京劇建構的文化中國形象
[摘要]《天下》刊發英譯京劇《販馬記》《風波亭》和《打漁殺家》劇本,組成一個三部曲,分別代表京劇中的神權、君權和人權思想,向英語受眾跨文化傳播中國京劇,建構了文化中國形象。其中《販馬記》和《打漁殺家》由姚莘農翻譯。《販馬記》的譯文特別關照戲詞字里行間的非言語因素,注重演員演了什么,如何體現戲劇情節及情節背后的文化,傳達戲中人物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建構人物表演傳遞的文化中國形象。《打漁殺家》刻意向英語受眾建構官逼民反的抗暴英雄形象,在抗日戰爭的時代背景之下,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抗精神,并表現出這種反抗精神已沉浸血液里,展示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勇于抗爭、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建構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國文化形象。
[關鍵詞]《天下》月刊;姚莘農;京劇;跨文化傳播;中國文化;中國形象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青年》的‘新青年’元敘事研究”(13BXW007)。
[作者簡介]嚴慧(1978—),女,文學博士,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廣州510665)。
20世紀30年代,受中西方戲劇互動交流的影響,《天下》以京劇為主要譯介對象,向英語世界傳播京劇及京劇理論。京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表現形態,藝術元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符號。《天下》英譯跨文化傳播了京劇《販馬記》《風波亭》和《打漁殺家》劇本,“在學術研究層面上,既向西方展示了中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西戲劇比較研究的成果,也充分顧及戲劇兼具文學性與表演性的特點,學術研究與戲劇翻譯相結合”
嚴慧:《超越與建構——〈天下〉與中西文學交流(1935—1941)》,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106頁。,組成一個三部曲,分別代表京劇中的神權、君權和人權思想,建構了文化中國形象。
京劇是一種面向大眾的表演藝術,也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戲曲劇種,在文學、表演、音樂、舞臺美術等各個方面都有一套獨具中國文化色彩的藝術表現形式,是“全方位的綜合表演藝術,是以演員的表演為中心的。京劇從起始就不是單項的說唱藝術,也不是草臺、廣場、地間、廳堂曲調或單一簡單的表演形式,更不是單純的武術和雜技。京劇從始就有文學劇本、故事情節、人物個性、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的‘四功五法’、化服道盔以及音樂、美術等的綜合藝術表演形式;還是在中國歷史上,綜合性強、藝術性強、思想性強、民間性強的戲曲表演藝術”
葉少蘭:《京劇·國粹》,《人民政協報》2017年12月25日,第11版。,多種藝術元素被用作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符號,能生動、具體建構文化中國形象。姚莘農是《天下》編輯中唯一的戲劇專家,追求理論研究與劇作翻譯緊密結合,系統英譯京劇腳本,跨文化傳播中國傳統戲劇,消除英語受眾對京劇的誤解與隔閡,為此翻譯了《販馬記》(
MadameCassia)與《慶頂珠》(TheRighttoKill),“京劇對于姚克原是駕輕就熟。他經過一番構思,決定先翻譯《販馬記》《風波亭》和《打漁殺家》三個劇本,組成一個三部曲,分別代表京劇中的神權、君權和人權思想。這三篇譯文是姚克的精心之作”,既體現跨文化傳播中國傳統戲劇時學術性與普及性兼顧的傾向,也反映譯者在文學研究領域鮮明的社會性。“另外,他還把三個劇本的主題思想,貫串起來,寫了一篇《譯后記》,說明劇本反映了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封建統治下,為了昭雪冤屈,從祈求神靈君恩,發展到奮起反抗的演變過程。”任傳爵:《回憶姚克》,《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3期。
一、英譯《販馬記》建構的中國文化形象
《販馬記》是京劇傳統劇目,又名《奇雙會》,自徽班傳入京班。道光年間進入宮廷,又由宮廷傳入民間,清末民初盛行于京城,是生、旦與老生聯手的傳統劇目。《販馬記》的表演不是按照生活原貌布飾舞臺,角色不按照生活面貌裝扮,而是根據所扮演角色的性別、性格、年齡、職業以及社會地位等,在化妝、服裝各方面進行藝術夸張,“本質是角色扮演。有時候,演員的表演并不依賴于劇本,甚至,沒有劇本也可以成為戲劇。在這個意義上,演員的表演才是戲劇藝術的根本要素”
康保成:《譚霈生先生論中國戲曲的戲劇性》,《四川戲劇》2013年第9期。,突出獨具中國文化色彩的唱、舞、對白、武打及各種象征性的動作,融合成一種高度綜合性的藝術,建構文化中國形象。
(一)姚莘農翻譯的《販馬記》
姚莘農作為一名戲劇家,深知文學上的戲劇僅指為戲劇表演所創作的腳本,而一部完整的戲劇包含兩個基本部分:戲劇腳本與舞臺表演。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之前翻譯中國傳統戲劇只能是“戲劇腳本”。20世紀以后,西方才真正在舞臺上實質性接觸中國傳統戲劇。為讓英語世界受眾能夠同時在理論層面與現實層面把握中國傳統戲劇,姚莘農沒有選擇已經在舞臺失傳、僅成為學者案頭研究對象的元雜劇,而是選擇英語受眾能在舞臺上看到的京劇劇目作為翻譯對象。
1935年12月,《天下》第1卷第5期刊發姚莘農翻譯的《販馬記》譯本。戲由《哭監》《寫狀》《三拉團圓》三折組成。《販馬記》中占篇幅最長的是第二折《寫狀》,也是全劇的精華。姚莘農認為:“《販馬記》不僅是當代中國京劇界最受歡迎的杰出劇目之一,同時也是我那篇關于元雜劇結構形式一文的最佳佐證。《販馬記》典型地反映了在京劇中保留下來的元雜劇的基本結構特點:一本四折,聯套的使用(可參看中文原本,譯文已將唱曲改譯為念白),該劇還體現了中國戲劇的其他一些普遍特征,如念白的介紹功能。”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37.
姚莘農英譯的《販馬記》講述了新任褒城縣令趙寵的妻子李桂枝,夜聞縣衙牢房有人哭泣,私自打開獄門,提出犯人李奇,詢問緣由。一問之下,發現李奇竟是蒙冤入獄的親生父親。當年桂枝生母早亡,李奇續娶楊氏。楊氏趁李奇外出販馬,將桂枝和弟弟逐出家門。李奇歸家,不見兒女,拷問婢女春華,春華懸梁自盡。楊氏又與姘夫合謀,誣陷李奇逼奸殺婢,買通胡縣令,將李奇問成死罪,收監待訣。趙寵是位初出茅廬的縣令,不諳官場黑暗,認為私開牢門是件大事情,因而斥責夫人,但因為是新婚夫妻,感情又十分融洽,便馬上互相諒解,并為桂枝代寫辯狀,待翌日按院大人巡查時,由桂枝女扮男裝代父鳴冤。原來按院大人就是李奇之子、桂枝之弟保童,李奇冤案終得昭雪,一家團圓。全劇通過閨房之中,夫婦之間的風波及與出任八府巡案的弟弟李保童一家團圓,構成喜劇的特點。
姚莘農具體考證了京劇《販馬記》中的“聯套”:“由于《販馬記》中構成音樂的曲牌名字大多已經失傳,所以現代人已經無法知道這些曲牌對應的音樂。所幸的是在第一折與第三折保留了兩首曲牌名字”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37.,可以肯定《販馬記》是“吹腔”,“很可能吹腔的前身是一支使用比較多的曲牌,在長時間遠距離的演出過程中吸收了許多有利因素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擴大腰逗的特點,而成為一支獨立的聲腔。無論事實情況是否如此,從《販馬記》的音樂形態中,可以肯定的是,吹腔既不等于‘梆子腔’,也與西北梆子系統的各種梆子迥然不同,它的旋律線是比較典型的南方音調,演唱起來婉轉柔和,肯定是來源于唱曲牌連綴體的昆弋腔。”
汪文娟:《從徽池雅調到吹腔——兼析〈販馬記〉的唱腔》,《咸寧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姚莘農認為《販馬記》中所用的曲牌《點絳唇》(第一折)與《哭相思》(第三折)表明了這出京戲與元雜劇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點絳唇》與《哭相思》分屬北曲與南曲的曲牌,《販馬記》應該是“南北合套”時期的劇目,并給出了另外三個論據:“一本四折是北劇的特征,多人演唱是南曲的特征。每一幕由男女主角一人獨唱某一曲牌是承襲自北劇。所使用的音樂是北曲中的七音音階。”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38.這種是“有人聲幫腔,鑼鼓伴奏,可以判斷來自于第一母體弋陽腔。曲調的音響效果昆曲味很濃,能看出是弋陽腔融合了昆曲因素的產物。”
汪文娟:《從徽池雅調到吹腔——兼析〈販馬記〉的唱腔》,《咸寧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姚莘農從《販馬記》所使用的語言及“吹腔”推出該劇形成于明代,并指出該劇是“在京劇形成過程中起到推動作用的諸多地方戲中的一出,在現存的二十二出吹腔戲目中,《販馬記》在主題與結構上都堪稱是最佳最受歡迎的。”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39.現代著名京劇演員也肯定“《奇雙會》雖然是笛子伴奏,但它屬于吹腔不屬昆曲,昆曲曲律嚴格,曲牌固定,吹腔有過門兒,詞句自由。《奇雙會》一劇始于徽班首創,程長庚演李奇,小生鼻祖徐小香演趙寵,胡喜祿演李桂枝,《奇雙會》也是在京劇孕育時期就有了,是京劇第一批保留劇目”
葉少蘭:《京劇·國粹》,《人民政協報》2017年12月25日,第11版。。
姚莘農對翻譯所選用的京劇腳本也做了說明:“并非目前京劇界所使用的劇本,而是來自古代的刻本,與現在的通行本有一定區別。”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39.姚莘農翻譯的《販馬記》不僅選取了比較古老的版本,與當時的流行版本略有出入,而且翻譯時相當重視尊重原文,保留了幾乎所有中國傳統戲曲中特有的重復與戲謔場景,還花了相當多的筆墨大量提示人物的動作、場景、角色等。姚莘農認為,翻譯戲曲不能缺乏這些細節,甚至應當放大以凸顯戲曲表演的獨特性。戲文文本外加上注釋,讀者就能根據詳細文字的引導進行形象創造,在腦海里展開盡可能與劇場環境相一致的舞臺想象,使翻譯文本具有很強的現場感,增強戲劇效果。
參見江棘的《近代中外戲曲翻譯者的對話——阿靈敦、艾克敦和姚莘農筆下的〈打漁殺家〉與〈奇雙會〉》,《戲曲研究》2013年第1期。
姚莘農最后說明翻譯《販馬記》的意義在于:“元雜劇由于年代的久遠已經在舞臺上失傳很久了,除了金代的《董解元西廂記》一劇,人們只能從文字劇本中一窺其容。《販馬記》是當前在京劇舞臺上演出的最接近元雜劇特征的戲劇劇目,理應受到研究中國戲劇的學生的重視。”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39.
(二)《販馬記》建構的文化中國形象
京劇腳本翻譯具有特殊性,表現為高度重視非語言因素,如人物的細膩動作,戲詞中的停頓、沉默或補充說明等等非語言因素,因為戲曲表達與非言語表達之間有著深刻的勾連,只有準確翻譯非言語因素才能更加生動地反映戲詞背后的文化心理并烘托主旨,將唱、念、做、打的藝術內在規律融合形成一出鮮活而富有表現力的劇目作品。京劇的跨文化傳播是一種立體表達,須有機整合詩詞、音樂、舞蹈、服裝等因素,構成有機的統一整體,否則就會很大程度地削減傳播效果。不同讀者閱讀同一劇本,閱讀感受肯定大相徑庭。“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戲劇審美領域的共識。傳播學理論不能有效解決戲曲審美的傳播效果,而非言語傳播理論能更有效地實現跨文化傳播京劇審美;京劇審美所要傳遞的意義可以通過人物動作、表情、語氣等非言語因素表達呈現,因此,京劇審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運用非言語傳播理論進行解讀。翻譯京劇必須最大限度地還原非言語因素搭載的文化意義,表現背后的傳統文化心理。所以,翻譯《販馬記》既要重視非言語因素,更須確定表達什么樣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
姚莘農翻譯《販馬記》對非言語因素的高度關照,表現為每一幕前的人物簡介,細膩的動作刻畫,戲詞中語氣的拿捏都翻譯得恰到好處,傳達出微妙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達到文化層面交流的目的。文化心理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而又頗具特色的交叉學科,是在社會組織、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社會習俗、社會教育等多個層面上探討個體文化人格形成和發展的多學科交叉研究。文化本身是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結果,“文化反應的最顯著特征是人們的群體可以共有它。在與特殊對象的接觸中,個體必然獲得文化反應的能動性,而許多個體也以特殊的方式反映著同一對象。由于反應行為的一致性,我們把所有這些個人當作是一個特殊團體的成員,后天的文化行為就在這些人身上烙下了某種心理團體的參與者的印記。這樣,相對于共同的刺激環境所包含的對象,個人行為也缺少獨特性和隱私性。典型的例子是對共同語言的反應,信仰、習慣、思想、風俗以及將個人塑造為民族的、職業的或其他團體的某一心理分支成員的方式。”
[美]J·R·坎托:《文化心理學》,王亞南、劉薇琳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頁。因此,研究人類的行為、神態、語氣、服飾等非言語因素,就能發現其經歷的文化,理解其建構的文化形象。
姚莘農的《販馬記》翻譯,特別關照戲詞字里行間的非言語因素,注重演員演了什么,如何體現戲劇情節及情節背后的文化,傳達戲中人物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而且人物的表演注重傳遞文化中國形象。《販馬記》有三個主要角色:李桂枝、趙寵、李奇。《販馬記》翻譯文本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人物心理狀態與行為,不僅突出人物的角色性格,而且展現人物背后的文化心理,建構文化中國形象。
李桂枝是貫穿全劇始終的主要線索人物,文本這樣展示其心理狀態與行為:
家院(白)啟夫人,監中有一老犯人,被前任老爺打的棒傷疼痛,故而啼哭。
李桂枝(白)啊呀且住!〔小鑼一擊〕(桂枝站起上步)想那老犯人,哭的如此凄慘,這內中定有緣故。
嚇家院,你去到監中,將那老犯人提出監來,夫人要親自問話。
家院(白)老爺回衙,降下罪來,何人擔待?
李桂枝(白)老爺回來,由夫人做主。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p.546—547.
李桂枝偶然聽到監獄里有人哭泣,立即想到的是有冤屈的犯人在哭訴。這位身份尊貴的縣令夫人,原不該被犯人的哭聲擾亂內心、產生漣漪,但她確實心有感觸,產生憐憫,命“家院”去探一究竟,李桂枝這種心理狀態與行為,展現出平易近人、善良博愛的良好品質——關心殘弱個體,能急弱者之所難。這個人物“那么大膽地私開獄門,可稱有勇;獲知父親蒙冤,便與恩愛夫君相商營救,然而又不是氣概萬端、辭嚴義正,可稱有情;最后又女扮男裝地公堂告狀,可稱有義,雖是奇女子,但又嬌柔可愛得無以復加的李桂枝形象。”
崔偉:《〈奇雙會〉引出的話語》,《中國京劇》2005年7期。這是中國傳統的大家閨秀的文化形象。
李桂枝不僅是心里關切有冤屈的犯人,而且迅速落實為行動,私自打開牢門,“將那老犯人提出監來”,“親自問話”。“家院”擔心“降下罪來,何人擔待?”李桂枝非常果斷,自己“做主”承擔后果,充分表現出可嘉的勇氣,這種敢作敢為的氣勢,完全不是中國儒家主流文化中逆來順受的弱女子形象,因而更加突出李桂枝這個角色的果斷勇敢,建構敢作敢為、心地純潔、樸實溫厚的大家閨秀的中國文化形象。
李桂枝(白)呀!
(唱)聽父言,心暗驚,
啊呀爹……
〔雅笛〕。李桂枝雙手內折袖欲扶李奇急掩口住聲,出門,向西側望門。〔雅笛〕收。李桂枝推門進。)
李桂枝(唱)啊呀爹爹嚇!
(李桂枝外翻袖高舉,右內折袖拭淚。)
李桂枝(唱)兒享榮華父受刑,
父女只隔重門地,
不能當面說分明。
(丫鬟手托茶盤上)
丫鬟(白)夫人請用茶。
(李桂枝掩面不飲。)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51.
李桂枝唱詞的內心獨白,深情抒唱出濃濃的父母恩情。雖然李奇只有生育之恩,并無養育之情,但得知李奇蒙冤,李桂枝依然悲極而泣,這個細節充分展現出這個角色性格中體貼孝順的特質,建構起了中國女性優良的文化形象。
李桂枝長大成人的過程雖然喪失了父親的陪伴及關愛,但血濃于水的父女親情并沒有被削弱。中國家庭傳統教育讀本《弟子規》,就是教育幼童建立社會與家庭的倫理觀念。開篇就強調“首孝悌,次謹信”
李逸安譯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79頁。,突出孝悌謹信是做人的根本。孝悌是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包括人孝父母、悌對兄弟、盡忠國家;謹信探究人與自己的關系,包括言行舉止要謹慎有禮,為人處世要誠實守信。李桂枝善待李奇的行為即展現了愛父情深、子女愛父母的“孝悌”中國文化形象。
(李桂枝戴素羅帽,穿海青、手持狀紙上,與趙寵相撞。)
趙寵(白)嚇夫人,上面坐的,就是按臺大人,你去告嚇。
李桂枝(白)我心中有些害怕,我……不去了。
趙寵(白)這有什么害怕?
李桂枝(白)我要回去了。
趙寵(白)噯!你去告呀!
(趙寵推李桂枝進門,趙寵驚慌地左串袖掩頭自上場門下。)
李桂枝(白)爺爺冤枉嚇!
(李桂枝手頂狀紙跪。)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68.
這個細節真實而又細膩,展現了李桂枝雖有決心替父叫冤,但真要面對地位威嚴的官員面陳父親冤情時卻又膽怯怕言的矛盾心理狀態及行為。李桂枝身上雖有一腔正義與勇氣,但畢竟是養在深閨的家庭婦女,站在嚴肅的官府殿堂之上,面對官威之人難免心虛。李桂枝與趙寵的博弈過程,細膩地表現出李桂枝的心理博弈及心理矛盾,豐富了人物的形象——愛父深情最終戰勝內心的恐懼,女扮男裝,呈上訴狀,突出地展現了李桂枝的勇敢與對父親的厚愛深情,用無聲的臺詞使思想感情形象化;“用人物的一舉一動、一個姿勢、一個神態、一個眼神,說出比有聲的言語更響亮、更準確、更復雜的語言”
焦菊隱:《焦菊隱戲劇論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第148—149頁。,刻畫出身上聚合忠勇孝悌禮信愛的小女子可愛可敬的形象,并傳遞給了觀眾,感染觀眾,建構起中國女性敢愛敢恨敢作敢為的文化形象。
《販馬記》的第二位主要角色是趙寵——李桂枝的丈夫。《販馬記》演繹的是一樁冤情引發的悲歡離合,趙寵不是主要角色,所以戲份不重。趙寵雖膽小怕事,但不是昏官。因是考取功名初入仕的新官,明辨是非,也想有所作為。他初到任所,第一時間就到鄉查旱。趙寵熟悉刑名,任事守職,聽到妻子擅開監門十分生氣,但他深愛妻子,舍不得妻子傷心,舍不得聽她嘆氣,舍不得聽她道苦,于是自找梯子下臺階,一再向桂枝賠罪,并表示妻子有委屈,只管說出,要為她做主。面對更強大的命官,無力撬動的權勢,他選擇矮下去,縣令雖是小官,但畢竟是辛辛苦苦、寒窗十年才賺來的烏紗帽,自然十分愛惜,不敢得罪上司:
趙寵(白)哎唷!哎唷!哎唷!啊呀寅翁嚇!
(趙寵雙手向胡老爺打拱)
趙寵(白)你可曉得大人出京的時節,可曾帶得家眷哪?
胡老爺(白)按院按院,不帶家眷。
趙寵(白)喔!
(趙寵雙手向外大攤手)
趙寵(白)完了,完了!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70.
這個細節展現出趙寵內心焦慮不安又迫于身份無計可施的形象。趙寵新官上任,烏紗帽得之不易,極為珍惜。妻子告狀,被“不帶家眷”的按院拉進后堂,深怕妻子被辱,焦急萬狀,急得團團轉。這個細節具體生動地表現了趙寵這個角色的性格特征:做事戰戰兢兢的本分書生,“主角趙寵為什么不帶官氣而要書生氣呢?等等,這都是京劇很講究的地方。因為《奇雙會》要表現趙寵的是新生(受難受苦的百姓重獲新生)、新官(讀書、奮斗得官,尚不懂官場黑暗,更未染官場陋習)、新婚(少年夫妻、純樸思愛),一出悲劇以溫情愛意、喜氣團圓的表演手法去處理,”
葉少蘭:《京劇·國粹》,《人民政協報》2017年12月25日,第11版。展現出中國封建社會官吏膽小、懦弱的文化形象。
《寫狀》一折,趙寵寫訴狀人姓名時,因為不清楚妻子的姓名,寫不下去。“有觀眾心存疑問:‘都結婚了,還不知妻子叫什么名字?’但只要想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婚姻制度,便會明白。出嫁后女子的身份變成了‘X門X氏’,丈夫只知妻子之姓而不知其名,是再正常不過的。對于古代婦女,名字是秘密,不好隨便問,更羞于向別人啟齒,包括自己的丈夫。傳統戲中,女性被問及名姓,總是說‘我是無有名字的’。問者反駁:‘人生天地之間,哪有無有名姓之理!’《寫狀》中有這樣的對話,《游龍戲鳳》中正德皇帝‘調戲’李鳳姐時也有相同的對白。寫戲的在名字上有文章可做,戲里的少年夫妻三番兩次在女方名字上開玩笑,既讓今天的觀眾很難理解,同時又使觀眾覺得饒有趣味。”
穆欣欣:《傳統戲看什么?——從昆曲〈奇雙會〉說起》,《中國戲劇》2008年第5期。
李桂枝(白)我姓李呀!
趙寵(白)嗐!我曉得姓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要與我講!
李桂枝(白)我叫……
趙寵(白)什么?
李桂枝(白)桂……
(趙寵故作聽不清。)
趙寵(白)嚇?
李桂枝(白)枝……
趙寵(白)嚇?
李桂枝(白)哎!桂枝嗄!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MadameCassia”,T’ienHsiaMonthly,vol.Ⅰ,no.5(Dec.1935),p.561.
這個細節蘊藏深厚的文化密碼,向觀眾透露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很獨特的信息:中國舊社會時男女地位極不平等,女性社會地位低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戀枷鎖在當時十分常見
張少涵:《傳統孝道對野性愛情的讓步與妥協》,《名作欣賞》2014年第8期。。“盡管兩人談論的是父親的冤苦案情,但表現出來的卻是少年夫妻,閨房之樂。以樂景寫哀事,是中國文學慣用的筆法,內里則映照出國人樂天知命的性格”
穆欣欣:《傳統戲看什么?——從昆曲〈奇雙會〉說起》,《中國戲劇》2008年第5期。,發掘出人物性格背后的文化動機,建構了文化中國形象。
二、英譯《打漁殺家》建構的反抗英雄形象
1936年5月,《天下》第2卷第5期刊登《慶頂珠》英譯本,姚莘農在譯者話中指出:《慶頂珠》表達了京劇較少涉及的“反抗主題”:“在京戲的諸多劇目中,它既無關才子佳人的老套主題,表演上也沒有用京戲里慣有的插科打諢去娛樂觀眾。這出短短一個小時的戲,緊湊、真實、扣人心弦、讓人熱血沸騰”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TheRighttoKill”,T’ienHsiaMonthly,vol.Ⅱ,no.5(May.1936),p.469.,并介紹了《慶頂珠》取材于《水滸后傳》,因為原來的劇名《慶頂珠》《討漁稅》《打漁殺家》都不能夠反映出“反抗主題”的精神,英譯本取名TheRighttoKill,是著名的京劇優秀劇目之一。
姚莘農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文學活動,得到魯迅的支持與幫助,與左翼文化圈聯系緊密,無論是在文學研究還是戲劇創作領域,始終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性與社會性,明顯影響他向英語受眾跨文化傳播中國文學的視角與立場。《慶頂珠》的故事講述了“梁山好漢花榮年老,隱居山莊,偶得一寶,名曰‘頂珠’,如將此珠系在頭頂,入江河后,可以分水,故名頂珠。后來演戲者不明來歷,將珠名誤稱‘慶頂’(如在臺詞中誤念:‘得來慶頂珠一粒。’),其實是慶賀得到頂珠,不是珠名慶頂。花榮得寶大喜,邀集故友知交,慶賀歡宴。蕭恩父女賣藝,路遇花榮,亦應邀而至。席間,花榮之子花逢春與蕭恩之女桂英,比武獻藝,桂英失神絆倒,惱羞成怒,要與花逢春相拼,被眾人勸阻,并受蕭恩斥責。眾人見逢春與桂英少年英俊般配,從中撮合,花榮得寶得媳,雙喜臨門,乃贈‘頂珠’作為聘禮。下面才接《打漁殺家》。在蕭氏父女‘打魚’與‘殺家’之間,還有‘惡討’、‘屈責’、‘獻珠’三折。‘惡討’即是現在的‘討漁稅’。在這幾折戲中,教師爺的‘惡討’是‘戲核’,所以從前演時,或貼《慶頂珠》(以全本名稱代折子),或貼《打漁殺家》,間亦有貼《討漁稅》者”
吳同賓:《京劇劇名正誤》,《文史知識》2000年第2期。。姚莘農選擇跨文化傳播《慶頂珠》,是刻意向英語受眾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抗精神,目的是配合抗日戰爭爆發后積極宣傳抗日的系列活動,展示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勇于抗爭,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而且向全世界形象地演繹了中國人民的這種反抗精神已融入血液里,具有英雄崇拜的文化傳承。
(一)姚莘農翻譯的《打漁殺家》
姚莘農翻譯的《打漁殺家》,不僅高度重視翻譯臺詞,還從衣著、性格兩方面言簡意賅地介紹角色,既蘊含了京劇角色分類的知識,又便于讀者閱讀理解。為讓英語受眾對劇中人物留下明晰的印象,還特別描述了人物扮相、角色類型和性格,將虛擬的舞臺環境和人物扮相、性格等細節描述給受眾,不僅豐富了人物形象,而且更加突出主題,引起受眾共鳴。如描繪情境不僅出現李俊、倪榮的扮相、性格說明,還特別描述蕭恩和桂英的形象:
桂英和她的父親蕭恩一起登場,劃著一條想象中的漁船,桂英芳齡十六,健壯美麗,頭戴廣沿帽,身穿打魚衣,襯裙前開。她的父親戴著又白又長的胡須,同樣的漁夫打扮。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TheRighttoKill”,T’ienHsiaMonthly,vol.Ⅱ,no.5(May.1936),p.472.
西方戲劇重視情境,因為情境是人物展開矛盾沖突的具體環境。京劇也高度重視情境,因為京劇的情境是提供展開唱、念、做、打的契機和平臺,通過演員的唱、念、做、打,把形體動作都化為舞蹈,成為“以動作為形式的詩歌”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劉大基、傅志強、周發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373頁。,成為表現人物內在心理節奏的外在形態,形象地展現出氣韻生動的虛靈空間,建構起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給受眾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京劇融合豐富生動的語言和演員形體構成的運動畫面,既創造了無限的時空,也深入剖析了人物的內心世界,觀眾不但能從戲文中想象到情和景,更能從演員的身段動作中真實地見到情和景,建構同時訴諸觀眾的聽覺和視覺的舞臺形象,演繹成為文化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
姚莘農英譯的《打漁殺家》文本,不僅簡單介紹了人物造型和性格,還為主人公添加了細致的心理獨白:
蕭恩:(被女兒的勸阻激怒)你知道什么!(他的目光堅定而有神,似乎看往很遠處。)他們剝奪了我抗拒非法漁稅的權利,他們剝奪了我擁有正義的權利,(大喊)他們剝奪了我作為一個人活著的權利,(痛苦地)但我還有一項權利,(聲音里滿是憤怒)殺人的權利!(他轉眼看向他的女兒)去拿我的衣帽和刀來。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TheRighttoKill”,T’ienHsiaMonthly,vol.Ⅱ,no.5(May.1936),p.501.
這段心理獨白是蕭恩的殺人權利宣言,京劇的舞臺演出不可能有這樣的臺詞,純屬姚莘農為蕭恩量身設計的。這種臺詞不是京劇臺詞的風格,而是話劇的風格,但蕭恩的這段內心獨白,一方面能推動故事情節發展,使人物情感達到一個最高點進而爆發;另一方面,符合英語受眾的戲劇審美,更容易觸動受眾的思想情感,從而理解并接受蕭恩從忍讓到奮起反抗的變化,能幫助英語受眾理解劇中的中西文化差異,姚莘農還因此特別解釋:“最后一幕蕭恩父女殺死惡人全家的劇情,西方觀眾可能會覺得太過血腥暴力。看起來似乎也不符合中國傳統道德中的涵養與中庸之道。但蕭恩的行為完全符合中國人的社會心理。因為在以血親家族關系為本位的中國社會里,個人并不被認為是社會的一分子,個人首先是屬于家庭的,社會是由眾多家庭構成的。……在舊中國一人犯罪全家獲罪。因此蕭恩殺惡人全家是合情合理的。”
YaoHsin-nung(姚莘農),“AnIntroductionofTheRighttoKill”,T’ienHsiaMonthly,vol.Ⅱ,no.5(May.1936),p.469.
英語受眾閱讀英譯京劇文本時,不僅不熟悉京劇藝術審美,也不甚了解中國京劇文化,更不熟悉京劇藝術形態,姚莘農為幫助英語受眾理解《打漁殺家》,譯文夾雜了大量的背景知識補充,不僅有京劇知識,還有中國社會文化的知識。如丁員外出場時的介紹:
同一天的下午,丁員外家的大廳。丁員外上場,葛先生緊隨其后。丁員外是三江口地區有名的士紳,與縣官呂志球有著密切的關系,丁自燮生性奸邪,貪戀錢財,嚴重腐蝕著當地的司法、執法機構,對當地老百姓而言是個可怕的壓迫者。在現實生活中,他一定是舉止優雅,衣著講究的士紳,但是在京劇舞臺上,丁員外由凈角應工,勾水白臉,夾著黑色斑紋,以此來顯示他邪惡奸佞的性格。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TheRighttoKill”,T’ienHsiaMonthly,vol.Ⅱ,no.5(May.1936),p.482.
丁員外是劇中的反面人物形象。這一段文字介紹丁員外的身份是“三江口地區有名的士紳”,是地方上的惡霸,“與縣官呂志球有著密切的關系”,“生性奸邪,貪戀錢財”,是老百姓心中“可怕的壓迫者”。同時還補充了京劇勾臉的常識:“勾水白臉,夾著黑色斑紋,以此來顯示他邪惡奸佞的性格”。文本描述丁員外“在現實生活中”,是“舉止優雅,衣著講究的士紳”,京劇為表達百姓的憤恨,特別丑化這種反面形象。這樣補充社會背景知識,既反映社會現實,又闡述了京劇表演在底層百姓生活中的社會功能,較為成功地建構了中國文化形象。
姚莘農英譯《打漁殺家》不以舞臺演出為服務對象,而是力求服務英語受眾的閱讀,所以翻譯不考慮劇本的“可表演性”,而追求“既重點強調了反抗行為背后那種‘人’之為‘人’的個體意識或者說主體性;而另一方面,又并沒有把這種反抗行為視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特例’,而是解釋為中國傳統固有的、合情合理的行為”
江棘:《近代中外戲曲翻譯者的對話——阿靈敦、艾克敦和姚莘農筆下的〈打漁殺家〉與〈奇雙會〉》,《戲曲研究》2013年第1期。,跨文化傳播這部戲背后反抗的精神,展現中華民族不怕犧牲、勇于抗爭的民族性格,成為跨文化建構文化中國形象的載體,展示出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敢于反抗的文化形象。
(二)蕭恩官逼民反的抗暴英雄形象
蕭恩是劇中主角,以打魚為生,與女兒桂英相依為命,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丁員外是皇權代理人,勾結縣官呂志球,管理社會最底層的人,織成控制社會的鐵網,形成壓迫底層平民的社會大環境。《打漁殺家》的故事就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演繹,“這出戲第一場丁郎兒到河下催漁稅,是表明豪紳地主勾結縣官壓榨漁民的暴行,這在戲里對于蕭恩是一次催逼;教師爺到蕭恩家里去是二次的催逼”
歐陽予倩:《京劇一知談》,《戲劇報》1955年第10期。,這些還都是劇情鋪墊,推動戲劇情節發展的關鍵“戲眼”是打漁殺家。“最后一場寫蕭恩父女連夜過江來到丁員外家,當丁員外命令家丁將蕭恩拿下時,蕭恩從容不迫地向他表示要獻寶。丁員外問他獻的是什么寶貝,他回答說是要獻‘慶頂珠’。當丁員外準備接受慶頂珠時,蕭恩父女出其不意地突然拔出刀來,殺死了丁員外及其走狗葛先生。蕭恩父女向丁員外獻慶頂珠這個行動,標志著這個戲的戲劇情節由‘打漁’而發展到了‘殺家’,并以此為基點將全劇迅速推向高潮。因此,劇中蕭恩父女獻慶頂珠這個舞臺動作即成為該劇的‘戲眼’”
任玉福:《淺談“戲眼”》,《陜西戲劇》1983年第3期。,完成了建構中國文化形象。
蕭恩受壓迫后感到絕望,被迫奮起反抗,殺死丁員外全家。這種劇情的“好處,當然是描寫了當時惡紳橫行、與官府勾結、欺壓良民的事實。在京戲中,惡霸和贓官是很多的,并不足奇,這個戲著重描寫蕭恩的心理,一步步地高揚,終于如火山般爆發出來。就藝術性而說,它遠比許多類似的劇目要高得多。比之其他‘水滸戲’,也更加深沉和悲壯”
金庸:《談〈慶頂珠〉》,《金庸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6頁。,演繹被壓迫者絕望地反抗社會——官逼民反,建構中國文化的抗暴英雄形象。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學為核心,主張以和為貴,倡導中庸之道,不提倡暴力反抗。這出戲能夠在封建社會“上演因為可以解釋為劣紳惡霸倚勢欺人,于朝廷正稅之外勒索漁民致遭仇殺。丁郎兒催討漁稅的時候,蕭恩問:‘可有圣上的旨意?’答:‘沒有。’問:‘可有戶部公文?’答:‘也沒有。’問:‘憑著何來?’答:‘本縣太爺當堂所斷。’這樣便把皇帝和戶部(中央政府)撇開了,表示罪過只在贓官惡霸,但是看戲的人誰都同情蕭恩父女,戲的宣傳效果并不因以上的幾句問答而減弱”。京劇的“無名作者最恨為富不仁的家伙。凡屬有勢力的鄉紳,告老回鄉的大吏,武斷鄉曲的財主都是攻擊的對象。這些家伙會勾結官府欺壓勞動人民,如《討漁稅》中的丁員外”
歐陽予倩:《京劇一知談》,《戲劇報》1955年第10期。。清末戲曲家余治就說:“打漁殺家。以小忿而殺及全家。血濺鴛鴦樓等劇皆足使觀者稱快。然其主人固有可殺之罪。而其合家中數十徐門何罪。諸如此類。皆作者欲圖快人意。信筆寫去。未及究其流弊耳。藐法紀而熾殺心。更適足開武夫濫殺之風。破壞王法。端在于此。”[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光緒乙酉寶善堂重刻本,第57頁。由此可知,封建社會不認可蕭恩“殺及全家”的行為,一度禁演《打漁殺家》,但京劇是大眾化的平民娛樂形式,反映平民百姓反抗社會壓迫,除暴安良,歌頌抗暴英雄是京劇中位居前列的重要內容。平民百姓生活在社會底層,面對社會的壓迫,要么忍氣吞聲,要么奮起反抗。《打漁殺家》表現的就是奮起反抗的精神,通過蕭恩反抗丁員外的壓迫,呈現社會底層平民百姓面臨社會壓迫時,只能做出以死抗爭的悲愴的選擇。這種不滿壓迫向往公正的抗爭,也是一種符號化的精神內涵,是中華民族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而且不會因為社會形態的更替而改變,體現了《打漁殺家》的價值追求。英語受眾接觸的不僅是一個憤怒的漁夫殺人報仇的故事,而且是面對強權壓迫,被迫抗暴的不懼犧牲的抗暴英雄形象。
京劇比西方戲劇多許多符號,如唱腔、舞蹈動作、臉譜和服飾等。這些文化符號絕大多數時候沒有表達什么內容,而單純是京劇審美,但英語受眾完全陌生。欣賞京劇,一是聽唱腔,二是看身段,三是念做打的“玩意兒”,其中最推重唱功,所以“老北京人去戲園都說‘聽戲’,誰要說去‘看戲’,就算鄉下人。”
尹丕杰:《京劇之本——玩意兒》,《中國京劇》2006年第11期。唱腔與動作形影相隨,且唱且舞。王國維就提出,中國“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
王國維:《戲曲考原》,《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第201頁。,所以“后代之戲劇,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戲劇之意義始全。故真戲劇必與戲曲相表里”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39頁。。有學者認為,“王國維說的不錯,宋元戲曲確實以演故事為目的,以歌舞為手段。而傳統京劇則相反,它以展示歌舞(即賣玩意兒)為目的,故事僅作為載體而存在,只是平臺,因而也只是手段。”
尹丕杰:《京劇之本——玩意兒》,《中國京劇》2006年第11期。運用“玩意兒”審視《打漁殺家》,蕭恩、桂英是漁民,舞臺上的劃船、打魚的動作,需要演員用唱、念、做、打細膩表演,描畫人物內心,蓋叫天“曾說‘景都在我的身上’,這就是以演員高水平技術為編研中心的最經典的理論。景是演出來的,不是畫出來的,京劇是不受時空限制的,這就是傳統國粹京劇。西洋歌劇是單面藝術形式,而京劇是三面立體的藝術表演形式,它需要演舞臺人物,有胡琴鼓伴奏,面向觀眾運用心譜程式來完成。一套舞劍、一個起霸就要求四面好看,要求四面立體美、心境美、氣質美”。
葉少蘭:《京劇·國粹》,《人民政協報》2017年12月25日,第11版。但《打漁殺家》的英譯文本喪失了唱腔和動作等審美功能,受眾只是閱讀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和辭藻文采,沒有了吸引讀者審美的唱、念、做、打的符號,只有突出和放大情節、臺詞與唱段。如蕭恩與大教師的對手戲。
大教師是丁府家奴,沒有什么真本領,唯擅長拍馬吹牛,但在丁員外面前自吹本領高強,混得一碗飯吃。丁員外派給“任務”,就帶一批幫兇同去,擺出“氣吞山河”的架勢,如遇緊急情況,幫兇就一擁而上,如同瘋狗一般亂打,是典型的“地頭蛇”惡霸。大教師碰上蕭恩,兩人演出精彩的對手戲:
蕭恩""(白)也罷。將老漢衣帽留在家中,待老夫打個樣兒與你們見識見識。
(西皮導板)聽一言不由我七孔冒火,
大教師"(白)聽一言不由你七竅冒火?教師爺,打個你八處生煙!
蕭恩(西皮搖板)不由得年邁人咬住牙唇。
(蕭恩打家丁。)
蕭恩""(白)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
(蕭恩打家丁。)
大教師"(白)江湖上叫蕭恩不才就是你?教師爺好有一比。
蕭恩""(白)比作何來?
大教師"(白)我好比左銅錘。
(蕭恩打家丁。)
蕭恩(西皮搖板)大戰場小戰場也見過許多。
爺本是出山虎獨自一個,
(蕭恩打家丁。)
大教師"(白)什么,你是出山虎獨自一個?教師爺好有一比:好比那打獵的,單打你這個死老虎!
蕭恩(西皮搖板)何懼你看家犬一群一窩。
你本事奴下奴敢來欺我!
大教師"(白)打啊!打啊!
家丁"(同白)不要打了,人家罵下來了!
大教師"(白)罵怎么?
家丁"(同白)罵咱們是奴下奴。
大教師"(白)我去問問他。
蕭恩,你罵我們是奴下奴,我們是丁府上奴,不是你蕭家的奴。這么辦,經得住,教師爺三“羊頭”,漁稅銀子不要了。
蕭恩"(白)慢說三“羊頭”,就是三“狗頭”,二太爺何懼!
大教師(白)"人頭變的狗頭了?你站好了,待我運運氣。
蕭恩"(白)"咳,小心二太爺的零碎。
大教師(白)"哦,你倒夸口。你站好了。
(大教師撞三羊頭。蕭恩領起,打四家丁同下,截住大教師。)
TranslatedbyYaoHsin-nung(姚莘農),“TheRighttoKill”,T’ienHsiaMonthly,vol.Ⅱ,no.5(May.1936),p.95.
大教師被蕭恩打趴跪下,蕭恩的手轉一圈,大教師爺就瞪眼吐氣隨著轉一圈,幫兇們早已逃掉,只剩下大教師出丑。蕭恩這段“西皮搖板”唱得“酣暢淋漓,辭句意境之佳,真是京戲中罕有的杰構。我們想象得到,當年蕭恩快馬鋼刀,在大小戰陣中會過多少英雄好漢,這時候雖然落魄,但哪里把你這種狗腿子放在眼里。‘奴下奴’三字,可與‘大名府’中石秀罵梁中書‘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那句名罵交相輝映”
金庸:《談〈慶頂珠〉》,金庸:《金庸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8頁。,不把勢利之徒放在眼里,無所畏懼地教訓大教師,盡顯不畏強權勇于抗暴的英雄形象。正如周信芳所說:“《打漁殺家》是一出好戲。它就是通過這么一個集中而又生動的故事,通過父女倆的遭遇,刻劃出了‘官逼民反’的富有革命性的主題。戲里的人物性格十分鮮明,劇情是逐步發展的,同時,也是有曲折、有起伏的。先是丁郎來催討漁稅,這時挑起了一個小高潮,蕭恩隱忍下去了;接著來了大教師,帶了一群打手來催討漁稅,壓力更重了,蕭恩還是想忍耐,卻又被迫和他們交了手。事態越來越嚴重,發展到上公堂當原告反遭毒打,還要過江賠罪,蕭恩的忍耐到了盡頭,起了殺機。照理,戲應該立刻向高潮發展,然而并不,反而向下落了一落,這就是蕭恩和桂英離家上船的那一段。牽扯越是多,障礙越是多,蕭恩的決心也就越是堅定而不可動搖。這一段充滿了悲劇性的戲,實際上更為高潮積蓄了力量,好比猛進之前的一個退步。正因為有這個退步,就能在前進時得到更大的沖力。這樣,到了《殺家》的時候,就像火山爆發一樣,一發而不可收拾了。”周信芳:《五十年來的藝術經驗——〈打漁殺家〉》,《戲劇報》1959年第19期。
蕭恩本就是江湖好漢,到了老年隱居江湖,為保護好女兒忍氣吞聲,避露鋒芒。他與丁員外不僅是私仇,還是一種社會壓迫與對立。蕭恩雖一次再次地忍氣吞聲逃避沖突,但社會壓迫及矛盾并沒絲毫化解,更加無法避免社會壓迫與對立,蕭恩被迫絕望地反抗社會——官逼民反,以死抗爭,抗擊強暴,演繹了一部悲愴的英雄覺醒戲,“殺死丁府一家之后,觀眾看到的是蕭恩的勝利。現在這樣結束,觀眾會想到,這樣一個老人一個幼女,蕭恩縱然英雄,只怕也很危險。父女兩人抱頭而哭,悲劇因素就深伏在內。這時江上月少星多,兩人決死一拼。至此一唱三嘆,令人千載之下,猶有馀思。雖然這不如殺盡壞蛋那么大快人心,但恐怕是更加現實主義的處理,梁山泊震動天下的大舉起義都煙消灰滅了,蕭恩這樣孤零零的反抗注定是要失敗的。雖然知道失敗,但仍舊要反抗,那就是英雄傲骨,那就是一個正直的人在那樣的環境中不得不走的道路。”
金庸:《談〈慶頂珠〉》,金庸:《金庸散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9頁。因此,欣賞京劇《打漁殺家》,不能將蕭恩的“殺家”行為具體化,而應該從文化的角度認識——蕭恩和丁員外的行為都是一種文化行為,蕭恩和丁員外的恩怨是社會的壓迫造成的不可調和之矛盾,蕭恩殺死丁員外全家,針對的實際是丁員外代表的社會階層,是壓迫與反壓迫的抗爭。這也是這部戲一直保存著鮮活的生命力,至今仍活躍在舞臺上的重要原因。這部戲不僅有漂亮的動作和唱腔,平民百姓更支持認可反抗精神,認可蕭恩是官逼民反的抗暴英雄,建構的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文化中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