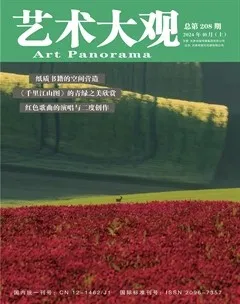原始的純粹

摘 要:本研究以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爾布雷希特·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現象學為視角,剖析保羅·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繪畫的藝術魅力與價值。通過其核心概念“懸擱”“意向性”“本質直觀”“回歸到生活世界”等理論,探討高更繪畫中對世界的認知與藝術表現方式。研究發現,高更的繪畫主題傾向展現原始純粹的世界,與胡塞爾追求的“先驗本質”和“純粹意識”契合。高更在繪畫風格上,運用鮮明的色彩、簡潔的形式與打破寫實的束縛等方式,與“本質直觀”一致,即營造有象征意義和精神內涵的視覺空間。同時,對主觀情感和內在精神的強調與“回歸到生活世界”的理論相一致,借繪畫表達對世界的意向性建構。此研究不僅有助于理解高更繪畫的哲學內涵與藝術價值,還為跨學科研究藝術與哲學關系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關鍵詞:高更;胡塞爾現象學;原始;純粹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8-000-03
胡塞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現象學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一種在純粹直觀的范圍內,在絕對被給予性的范圍內的本質分析和本質研究”。理論中最為重要的口號就是“回歸到事情本身”。
傳統哲學的思維態度是感性獲取之后理性進行分析,是一種自然的思維態度,是主體承認主客二元模式為前提的思維方式,因此,就導致了現象和本質的割裂。但胡塞爾所認為的則是,我們在觀看一個事物的時候就已經可以把握本質了,不需要再通過感性到理性這個階段。
他提出了一種辦法,就是“懸擱”。“懸擱”后回到事情的本身。在我們認識的世界中,總是或多或少的帶有主觀判斷的色彩,自己好似處在一個被主觀偏見所支配的狀態中,是被遮蔽的,這就阻礙了我們去觀看世界,去探尋本質。所以就必須撥開這個云霧,而撥開的辦法就是“懸擱”,懸擱存在,懸擱歷史,獲得“純粹意識”和“純粹現象”。這些最后的指向就是“回歸到生活世界”。
與胡塞爾相同的是,高更區別了自然與繪畫之間的關系,對于藝術作品不進行事先的預設,在不斷探討的進程中表現出了回歸于原始的狀態,這是一種更為純粹的方式。他將目光投向了原始,投向了布列塔尼、塔西提、馬提尼克島,投向了至純至美的藝術當中,以當地的居民作為創作主題。技法上也能夠看出來他運用了大量的鮮艷色彩、裝飾性、輪廓線、舍去陰影等方式來表現,雖然線條簡潔但每一個形象都極具表現力,用最簡潔的手法將所描繪的事情本身及生活態度都表現出了回歸原始的狀態。這不僅表現為創作主題的原始性,也表現出了創作方式的原始性。
現象學關注視覺關系的內在層次和結構,這些關系由事物如何對我們顯現的種種面向構成。繪畫可以強化這些視覺關系的內在層次,使通常不被關注的面向變得顯著。無論是視覺形式還是繪畫方式,胡塞爾與高更都表現出了一種通過“懸擱”后的自我構造。
一、“打破自然思維”的觀看
現象學作為20世紀西方流行的哲學思潮對自然態度進行了批判,傳統的自然態度即主體認識客體,就是先預設了客體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礎上去探究客體究竟是什么。采用傳統的自然態度就會導致現象和本質進行割裂。現象學的態度就是在事物顯現的那一刻,所有一切事物的感性材料都一并展現了出來。這就要求我們對于所存在的事物不進行預設,并且采用現象學的態度去認識世界[1]。
高更在致埃米爾·舒芬尼克爾(émile Schuffenecker,1851—1934)的信中提道:“哲學家們均窮其心力探討自然界中許多對我們而言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現象,殊不知,那種現象即我們的感受。”這種感受在思考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完美的系統,獲得了最為純粹的知覺,也完成了大腦最為精微的轉化。因此在高更看來,藝術家感覺的形成往往是先于思維而產生的。這恰恰與胡塞爾提到的現象學的態度所一致,即在事物顯現的那一刻,所有一切事物的感性材料都一并展現了出來。這種直覺是不輕易顯現的,是在最深處的,是人們最初內在的自我顯現,因此在繪畫的過程中無法理解的線條與點綴的形式都變得更加純粹。
僅僅通過現象即感受還不足以達到真正的認識,要想真正完成轉變則需要“自由想象的變更”。自由想象是在人的意識領域發生的一種意識行為,是意識本身具有的特點,對于一個對象,對其任意維度的“想象”,并且不斷變更想象的維度及其內容,就會產生關于意識對象的各種例子。意識也就有了主動性,通過想象力去自由變換。同時,人類的意識活動是人們心理活動的最高形式。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我們總會有藝術構思這個層面,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或多或少地也會被意識和無意識所影響[2]。
高更是象征主義的先鋒人物,象征主義在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的過程中往往不是直接的表達,而是通過符號或者是將藝術形象通過想象的方式表達出來。高更對于繪畫的本質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將寫生與想象的幻覺聯系在一起組成畫面,其中《布道后的幻象》是最為典型的象征主義作品。因為畫面上實際所呈現出的狀態往往超越了現實,只是人們的幻覺。另外,在高更的很多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宗教和神話主題,這些都需要想象力進行變更才能描繪。
胡塞爾打破了傳統的觀看方式,運用邏輯研究、概念論證的方法使得在觀看事物本身的時候就能夠做到現象與本質的完美統一,并且直觀地把握本質。高更也與傳統的觀看方式有著巨大的差別,他將目光伸向了更加原始的純粹,并且運用打破傳統的體系和規范、忽略細節和不再追求逼真準確的透視等方式來表現。他將自身的感覺與思維做出了合理的解釋,認為現象就是我們的感受[3]。
二、“本質直觀”的表達
胡塞爾致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的信中提道:“現象學的直觀與純粹藝術的美學直觀是相近的。”“本質直觀”就是認識,如何達到本質,其中則需要“懸擱”以及“本質還原”。懸擱就意味著懸置一切,從而達到回歸到精神世界的狀態。這種精神世界的狀態下就能夠發現最為本質的東西,達到本質的顯現。將我們已經擁有的成見、概念、理論、看法等懸置起來,先去獲取未經反思的生活體驗,然后再來反思。最終的結果就是還原到絕對純粹的“先驗自我”及“先驗意識”領域。
意識的本身是如何構造意識對象的就是胡塞爾所提出的“意向性”,即意識總是指向某個對象的特性。在藝術創作中藝術家可以通過現象學的方法來分析自己的創作意圖,明確他們的藝術表達指向何種主題、情感或觀念。并且在感覺(感知)和思維之間善于聯想及想象,為這種感情尋求最單純的形式[4]。
高更在繪畫的過程中也進行了一種歸納、演繹以及直觀的行為狀態,擺脫理論的束縛,從客觀的現象出發,探索創造思維的方式,形成創作的能力。直接表達創作內容,并不像經驗主義那樣對本質進行歸納。在他看來,“偉大的藝術家是懂得如何傳達智慧的人,智慧能令其表達各種最精致、最微妙又無法捕捉的感受和直覺”。因此,在表現方式上高更采用鮮艷的色彩、裝飾性、舍去陰影,以及加強輪廓線的方式進行創作,將本質直觀下的現象表達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創作出了真正屬于自己的作品。
1.注重色彩。早期高更的色彩并不鮮艷明朗,而是灰暗,沒有強烈對比。在受到了卡米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的影響以及印象派的影響后高更的很多繪畫作品中也逐步運用了鮮艷的顏色,他認為色彩能夠震撼眼睛,并且也能夠做到很多的延伸。在高更的作品中絢麗的玫瑰色、綠色、淡紫色構成了他表現塔西提風情的重要技巧。
2.裝飾性。在高更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現出了裝飾性的特點,他認為裝飾的效果是美麗的,是一種音樂。這種裝飾性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歐巖畫,他們把對于動物的極簡最后抽象演變成了幾何圖案,也是具有一定裝飾性效果的。同時,由于大量的木版畫來到法國,高更也受到了日本版畫和裝飾性特征的影響。在創作中,其藝術風格也逐步變得具有裝飾性和原始性。他更是將三角形稱為最完美的形狀,認為長三角形是最為典雅的存在[5]。
3.舍去陰影。陰影在一幅畫中其實與透視法相通,能夠賦予物體強烈的空間感,自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之后,陰影的地位逐漸下降。到了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他在繪畫中極少用灰色調來表達陰影,或者就是用對比色來表現陰影的存在,到了高更更是將陰影舍棄,他認為陰影只不過是太陽的幻覺,在繪畫的過程中不應該只是將陰影作為繪畫的必需品,應當讓陰影受到我們的支配。
4.強烈的輪廓線。高更認為,線有崇高以及虛偽之分,直線象征著無限,而曲線限制創造,向右的線意味著向前,向左的線意味著后退。因此,在線的運用上高更也十分重視,在繪畫中他大膽地用黑色勾邊,用線條來分割色彩,放棄了傳統的光影,運用線條來處理顏色的對比以及畫面的邊緣,這種流暢的線條也為他的裝飾性平添了更加強烈的沖擊感。
三、“回歸生活世界”的目標
生活世界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胡塞爾對這個世界的理解為最初的、事先被給予的、永遠事先存在的世界,是人能切身感受到的實實在在本真的世界,它包括一切個人的、社會的、感性的、實際的經驗。生活世界才是最為根本的,是人們通過直觀的方式能夠感知到的。科學的發展也要以立足于生活世界為基礎。因此,高更毅然決然地走出文明社會后就徹底回歸到了“生活世界”中,獲得了原始的純粹[6]。
在高更充滿詩意的文章《諾阿·諾阿》著作中記錄了他在塔希提十二年的種種回憶以及藝術的創作思想。他將自己看作一個脫離文明社會的“野蠻人”。在這里他原本被文明與理性所掙扎的內心得到了釋放,獲得了純粹與原始。在這個充滿異域風情的原始之地,高更獲得了靈感,畫面也展現出了不同于傳統的創作風格。在他的作品中,大多以塔希提地區的民俗、原始宗教、神話故事為主題。在他看來,這種充滿原始性的地區并不是文明地區所說的野蠻,他認為這里是美好的、原始的、樸素的。正是在這里他的內心得到了短暫的安寧。就像他說的那樣:“我離開是為了尋找平靜,擺脫文明的影響。我只想創造簡單的,非常簡單的藝術。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回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只看野蠻的事物,像他們一樣過日子,像小孩一般傳達我心靈的感受,使用唯一正確而真實的原始表達方式。”
1898年夏,在塔希提,高更創作了著名的作品《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往何處去?》。高更認為,這幅畫是他藝術生涯的巔峰之作。畫面的構圖以及形式已經遠遠與傳統繪畫中的形式形成了反差。他采用了散點透視以及平涂的方法,畫面的形式更具裝飾性特色,色彩的運用也更加大膽、明艷,表現出了神秘以及奇特的狀態。畫面中的元素也都來自塔西提特有的山脈、人物,再加上作品的命名也體現了畫家多年來在塔西提的感受,以及對于原始和質樸純粹的生活態度和人生哲學的反思。這種觀念與形式的統一,讓人們在欣賞作品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想起我們生活的世界,使我們去探尋生活世界的美。無論是他從文明之地去往原始的、充滿異域風情的原始之地,還是對于繪畫創作方式以及對人生的思考來看,在這個過程中高更就完成了一種“懸擱”過后回到本真,最后達到自我構造的呈現。
藝術源于生活,對藝術的研究必須根植于“生活世界”。胡塞爾的理論核心正是“回歸到生活世界”,他提出了更為科學的辦法,運用邏輯研究、想象與本質、懸擱的辦法回歸到了這種“生活世界”的狀態。而高更的藝術生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如何在現代世界中尋找和保持個人真實性的范例,他的作品和思想至今仍然激勵著我們去探索和發現生活世界的無限可能。高更仿佛是這個時代的激進者,又像是一個純粹的“野蠻人”。對于藝術他永遠保持虔誠及對原始的敬畏,這也許更是我們當下所要追求的——對人生的追求,對生活的向往,這樣才能夠真正地感知到人的本身。
參考文獻:
[1][法]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爾布雷希特·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M].倪梁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倪梁康.叔本華與胡塞爾——藝術直觀與理念直觀[A].孫周興,商士明.視覺的思想:“現象學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
[3][法]保羅·高更.高更藝術書簡[M].張恒,林瑜,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4]蔡惠萌.莫蘭迪繪畫作品的現象學分析[J].創作與評論,2016(06):111-114.
[5][法]羅·高更.高更藝術書簡[M].張恒,林瑜,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6][法]弗朗索瓦絲·加香.高更—我心中的野性[M].廖素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