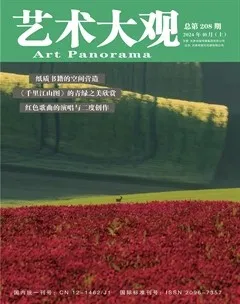品析“有筆無墨”與“有墨無筆”

摘 要:筆墨是老話題,也是常談常新的話題,中國畫的現代性,亦是筆墨問題探討中的焦點話題。諸多藝術家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賦予這一課題清新的鮮活。肇源于山野與農業文明的中國畫藝術,形成了它的怡情寄興、物我合一和崇尚內省、化物為我的基本功效。作為體現和反映社會狀態的包括中國畫在內的傳統文化,自然具有內斂溫純、品操有度的生命秩序。就中國畫而言,它是傳統文化意識形態的思想凝聚和形式提煉,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意識和審美情趣,其美學形式、語言形式、藝術風格在歷史的演變和沉淀中日臻高度完美[1]。然而,隨著封建王國的經濟消退、工業文明的荒蕪、帝國主義的資本崛起,中國進入了融合中西的現代化進程。社會形態的轉型造就了新的生存環境,進而使人生價值重新確認。作為具有傳統文化標志的中國畫也開始了由內而外自我思考,那就是變革——已經成為傳統中國畫自身的需要。傳統中國畫在當下文化中的精神價值如何確定,逐漸獲得了新的定義和釋讀。本文以傳統文化為背景,從筆墨作為中國畫的形式語言角度,去談及當代“有筆無墨”和“有墨無筆”的諸多問題,以及這一問題所涉及筆墨的形態、風格和格調等。
關鍵詞:筆墨;形式語言;有筆無墨;有墨無筆;使命意識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8-00-04
一、近現代中國文化改革的時代背景
20世紀以降,近現代中國文化的一切變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后發生的。包括中國畫在內的傳統文化,大都以西方文化為主要參照體系,一方面進行著傳統文化的維護和贊賞,一方面追求著傳統的現代性轉換和變革。學界對中國畫命運的關注,是要不要中國畫改革和如何改革的問題論爭。中國畫改革方式中,以西畫來改造中國畫成為那個時期的主要途徑和手段,但終究是在藝術社會學范疇,并未涉及中國畫的形式語言。20世紀50—60年代,筆墨已降為中國畫的附庸,一切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重內容、重形式,而將筆墨視為一種趣味,“筆墨”是作為保守派的批判對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場轟轟烈烈的現代美術運動——“85美術新潮”到來了。“85美術新潮”源于第六屆全國美展落選的一些勇敢而激進的青年畫家。他們以西方現代藝術為參照,進行中國式的改革和實驗,以期獲得中國美術的標新立異。這一潮流的特色是多反對寫實主義,追求和強調暗喻意義及現代哲學,把感性和偶發性的沖動作為創作的契機,偏于怪異、荒誕和模糊的表現。這一美術運動解放了思想,它宣布了長期的封閉將不可逆轉地退出歷史舞臺。西方古典寫實觀念對中國藝術的影響開始走向衰落,中國藝術迎來了多元開放的新時代,但由于青年新潮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缺乏對西方現代文化、西方傳統文化的深入體驗,他們似乎要在幾年內走完西方人一個世紀才能走完的歷程,結果如同曇花一現[2]。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才突然間感受到筆墨的意義,尤其是“筆墨等于零”和“中國畫窮途末路”論點的提出,引起了學界、畫界的廣泛關注。一些美術評論家和畫家,紛紛著文立說進行反駁并在思想上進行辯論——筆墨內涵、價值意義得到了空前的高度審視。21世紀左右,各種關于筆墨問題的著述和展事,也如雨后春筍。
二、“有筆無墨”與“有墨無筆”的筆墨關聯
關于筆墨的釋讀,就中國畫而言,亦作中國畫技法的總稱,包括筆和墨的相互作用、融合,如用什么樣的筆鋒、筆勢、筆觸,墨的濃淡干濕、渾厚華滋等都是筆墨技法的體現。筆墨和紙硯合稱為文房四寶,是中國畫獨有的文書工具,其名稱起源于南北朝。這里的筆墨特指是用中國傳統的書畫材料去表現藝術家的內心世界,由此引發出多種技法和運用方式,并在運用過程中,產生的諸種審美感受和感官情趣,從而決定了藝術品質有著高低與優劣。因此筆墨技法,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用筆用墨技巧,而是藝術家體道、悟道和映道的筆墨的載體。筆墨承載了藝術家的情感與哲思,它具有獨立的精神元素和審美經驗。由此可見,技法背后的支撐乃是藝術家在人生經歷和筆墨體驗中形成的人生價值觀和世界觀。此外,筆墨的重要性,還與它自身的屬性和特殊功能有關,因為它是中國畫所獨有語言和審美對象。任何繪畫都有造型、色彩、構圖、形態、風格、格調,唯獨中國畫要求筆墨,失去了筆墨,中國畫就失去了與其他畫種區別的基本標準。
水墨畫是近百年來中國美術關注的重心,而筆墨又是水墨畫討論與實踐的焦點之一。筆墨是傳統水墨畫的主要語言與技巧方式。作為藝術等專業話語,筆墨是有模糊性,但又具有解說性、釋讀性。它原生于對特殊材料的技術把握又升華了材料與技術的客觀現實。作為視覺語言藝術,它具有結構性、程式性,有獨立而悠久的傳統精神背景。“有筆無墨”和“有墨無筆”其實是將筆墨隔離開來。筆墨依附于造型,但又超越它。傳統繪畫中的形神兼備,很突出“骨法”。就對象而言,“骨法”與造型是有嚴謹關系的整體結構。就主體而言,“骨法”乃指用筆。骨法有時可以理解為力法,書畫界以有力的筆法,寫出有力的線條,有剛健、遒勁、挺拔等之感,反之便是柔弱、輕浮、圓滑等,便是無力或乏力之現。骨法用筆,力為先決條件,靈動飄逸,力是根本基礎。在“六法”中,“骨法用筆”排在“氣韻生動”之后,地位比“應物象形”重要,這在六朝時期,筆法已經不是造型的從屬物了。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總結說:“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元以后,宣紙取代絹,筆墨韻致的效果在文人畫中得到空前認可。明清畫家將“不似之似”“離形得似”作為造型的最高級別,尤其在董其昌繪畫中,將筆墨看作繪畫的最高表現。
唐·吳道子,開元間以善畫被召入宮廷,開創“蘭葉描”,人物畫稱作“吳帶當風”,極力推崇線條對造型的表現力和把控力,以簡約奔放的線條表現出物體形象的動態感和飄逸感。而荊浩則評價為“有筆無墨”,意味著他在繪畫中注重筆觸的運用,但在墨色的運用上稍顯不足。項容是畫史上第一個見于記載的大膽用墨的畫家。荊浩《筆記法》有云:“項容山人,樹石頑澀,用墨獨到玄門。用筆全無其骨。”“全無其骨”意指物體表現無線,無勾勒之手法,勁勢均在墨,于放逸中不失真元。吳道子畫山水,“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兩者應成一家之體,方諧筆墨之能之趣。
傳統水墨畫,在唐代后期就已經成為中國畫的主流,就有了“遠墨而無色具”[3]之說。而后又有了“畫道之中,水墨之論”,工筆重彩畫,也多有勾勒、皴擦的因素存在。可以說,筆墨無處不在,無處不與造型、結構、色彩發生關系。除重彩花鳥,大青綠山水外,筆墨總是處于主導支配地位。荊浩在《筆法記》中不僅提出了“圖真”“搜妙創真”的藝術觀點,還提出了“六要”即“氣、韻、思、景、筆、墨”。“六要”之外,“筆有四勢”亦足珍視。刑浩說:“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黃賓虹總結的“筆法五種”(平、圓、留、重、變)和“墨法七種”(濃墨、淡墨、破墨、潑墨、積墨、焦墨、宿墨),并將墨法歸為“清、潤、沉、和、活”五類。這在當下仍然有著積極的意義。
三、中國畫現狀
(一)缺乏表現性
現代作者所畫多形式化、圖示化、標準化,作品線條繁密、場面恢宏、尺幅巨制。如此效果確能增強作品的寫實性,如描繪祖國河山、江海奔騰、生活繁榮的圖景,能逼真再現大千世界物造的偉岸和雄奇,令人嘆為觀止。然終是脫離了傳統寫意畫的筆墨精神,丟卻了物我皆忘意境和創作旨歸。即使是寫實,恐怕也非是真正的寫實,沒有直面自然物態的人為力量而使其生態失之平衡,沒有直面生活,揭示生活的矛盾。具體而言,在這里已不單純指“有筆無墨”了,不再是技術技巧方面了,而在于作者的理念、思想力、情感指向。換言之,即缺乏表現性。
這一問題的出現,主要不在藝術形式本身,而是作者有沒有表現的氣質、才能,以及這種表現有沒有觸及更為積極的生活觀照和人性問題。比如,因人性的貪婪和欲望,過度地開墾和砍伐或因一時的政績,大量地進行人工工程等,這樣生態物象能引起作者的反思嗎?當然,高度贊揚性的描繪與表現性是可以統一的,這里的關鍵是如何挖掘自己的內心生活,去表現豐富多彩的現實人生的問題。真正的藝術家,必須有能夠觀察社會、深入理解人生的能力和情懷。有獨到的洞悉、感受和批判力,方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變目前的作品形式,去完善自身的藝術語言和風格[4],達到筆與墨合而為一的最終要求,那就是表現心靈與追求心靈中的筆墨之美。
(二)無表情和同一化
現代畫展,人物畫居多。但縱觀畫作,可以發現大多淡化表情,甚至無表情——人物無怒無怨、不喜不悲,失去情感表達。“傳神在阿堵中”在這里已是遙望不及的象牙塔了。當然,在特定環境里,由于需要,沒有表情的傳達是完全可以的,就怕它成了一個模式,成為人人可用的公式,從而形成了集群式的風格化。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物畫形式因社會需要和要求,完全可以是一個表情公式,那是充滿階級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當下的無表情竟然是一種時尚,甚至為參展流行的一種“共象”,具有同一化傾向。
四、“有筆無墨”與“有墨無筆”是當下主要問題
1.“有筆無墨”與“有墨無筆”這一問題的產生歸根結底是對筆墨和筆墨傳統缺乏基本的認識和切身體驗。現代中國畫受徐悲鴻教學理念影響,強化結構、效果、視覺張力,但這絕不意味著放棄筆墨自身的精微表現。筆墨乃中國畫的寫意精神。寫意精神是中國畫藝術精神的核心命題,是區別中國畫與其他繪畫形式的本質特征,對中國畫寫意精神的認知,不是一個簡單從技法層面對其寫意性的理解問題,而是一個民族文化深層次結構認知與實踐體驗的關系問題,也就是中國畫藝術創作與中國文化精神的互動問題。
筆墨是中國畫的語言,“點、線”又是語言中的核心要素。筆墨含性,性必修筆墨之道,貴在用水。情緒、環境的影響,會產生不同品味、不同味素的筆墨形態。它所營造出的無形的、抽象的、朦朧的味素,就是個性化筆墨意境。反觀當下展覽作品,均“高大全”式的拼貼,重細筆描畫,重色彩堆積,密、繁、亮、厚是其形式特色,又傾向一律化、程式化。中國畫藝術形象漸漸成為攝影藝術的翻版,已是當前創作中頗受爭議的一個問題,尤其在青年畫家群體中普遍存在。手機拍照的普及和網絡圖片資源的日漸豐富,為畫家創作素材提供了便利,但丟棄了傳統的“目識心記”和“對景寫生”。其結果是,圖片的廣泛使用弱化了畫家的想象力和取舍能力,也就是現實物象和“經營位置”的取舍能力和創造性弱化或者失去了。筆與墨皆為構成而服務,以筆墨傳達個性和情感趨于“貧血”狀態,藝術創作缺失了獨立性和創造性,極大地影響了藝術的思想性和文化內涵。
2.“有筆無墨”和“有墨無筆”創作品類中,前者居多,當下創作均將造型與色彩放于首位,造型從屬于色彩服務。線條本是物體的造型手段,在這里卻成了服務于造型的從屬物。形式多傾向于工筆畫的方向,繁雜處甚而密不透風,與傳統的“有筆無墨”的內涵差距甚遠,將傳統的寫意精神轉化為裝飾性。后者重于墨色的設置和映照,追求鮮艷、亮麗和時髦,不僅在寫意畫,工筆畫亦如此。一些作者在繪畫過程中,用素描技法代替傳統的書寫筆意,用西畫的形式語言改造中國畫,這導致了中國畫傳統韻味的喪失。甚至有些作者直接將國外的藝術形式和理念生搬硬套,沒有進行本土化的轉化和吸收,使得作品失去原創性和獨立性。
重線條而脫離墨的運用,更忽略“墨分五色”的內涵和運用,色彩也脫離了線條的吻合和統一關系。古人“以墨作色,以色作墨”的創作理念在當下的創作中進行了脫離和機械似的組合。現代作者則是將“有墨無筆”轉化為讓墨色唱主角,將骨法用筆降為次要地位,甚至放棄或基本放棄筆法,主要表現為強化色彩,強調色彩渲染。這樣的結果是大面積多層次渲染會弱化筆墨表現,傾向裝飾性。因此,既要強化色彩又要保留筆墨的自身特性,使其完美統一,解決辦法是應理解作品的精神性,山水畫的裝飾性、人物畫的無表情都應該由內而外進行刻畫,增強人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去關注人的命運尤其是普通人的命運,那是作者自身的思考和情感的邏輯,若放棄了對人物內在精神與個性的刻畫,筆墨尤其是墨色成為營造時尚藝術的附庸,將會丟失中國畫所應體現的精神性和創造性。
而這一切源于部分藝術家對藝術基本功的訓練,過于依賴現代技術和工具,導致作品在技法和表現力上存在不足。如在繪畫領域,一些作者對造型、色彩、構圖等基本要素的掌握不夠熟練,作品顯得粗糙和稚嫩。歸根結底,缺少的是筆墨基礎的訓練和把握,缺乏的是對中國畫筆墨結構的理解與把握。
3.“中國畫的演變大致包括兩種方式:一是水墨或以水墨為主的方式;二是色彩或以色彩為主的方式。在傳統繪畫中,兩種都重視筆墨。[5]”就后者而言,現實中也有些以筆墨畫色成功的個案。作品以大面積色塊布局,力圖保持筆墨的表現,“有的用筆墨的方法畫色,有皴有擦,有潑有積,既見色又見筆,所謂‘以色為墨’,還有的以平面構成的方法安置色塊、墨塊等”[5]。這些在田黎明、陳平、陳向迅等畫家的作品中都能清晰地看到,他們讓色彩唱主角,但充分保持了筆墨性,從而使作品在描繪與表現上都得以充分發揮。他們有一個共同性——強調筆墨與心靈的同構,追求筆法與心法的統一,他們有獨立的思想、獨到的理性醒悟,藝術思想超越歷史、超越現實、超越唯美主義等,時刻賦予作品精神的高度和厚度。
在帶有傳統標志的中國畫中,能取得成功是因為創作者尊崇美、敬畏美、追求美的神圣性,而不是對線條、皴法、顏料等的熟練掌握和復制性運用。說實話,技法固然重要,但心法更重要。技法人人都可以達到,唯獨心法難以練就。美的神圣性,就是中國畫的心法。田黎明、陳平等人通過筆墨傳達個人的道德情操和哲學思想,個人情操和價值就是由筆法轉向了心法的體驗與駕馭。即在扎實的筆墨根底上,色彩修養也與筆法同步。
五、從形態、風格、格調等方面解決筆墨脫離問題
解決“有筆無墨”與“有墨無筆”的根本問題,就是解決筆墨形態、風格、格調問題。不同筆墨形態能喚起不同的視角心理感受,傳統畫論有一套詞語系統來描述人們的感受經驗,如蒼厚、深重、樸拙、荒率、質樸、柔潤、遵媚、甜俗等話語,都是可以意會的。它們所表達的種種感覺,是人們在生活經驗和人生經驗中,將筆墨語言進行提存。這一過程,融入了對萬象世界的豐富感觸,化為精華凝縮其中,人對于生命的意義的感悟通過筆墨進行了升華。所以有筆,有墨,筆墨合為一體,方是一個有有血有肉的生命本體。
筆墨有形態之別,也有筆墨風格,不僅源自自身的生活經驗、筆墨經驗,更源自時代的氣息。五代宋元繪畫,筆墨風格與造型風格有著緊密的聯系,明清繪畫,造型風格弱化而筆墨風格凸顯,近現代繪畫造型與色彩風格突出而筆墨風格淡化等,……但近百年來,探索筆墨風格與論著,關注并能夠進行筆墨風格分析的美術史家,如鳳毛麟角[4]。關于筆墨風格的弱化,還與作者的盲目跟風國外的藝術潮流有關,與以西畫的理念、標準改造中國畫的理念、標準有關。對外改革開放,借鑒吸收西方文化以充實和改進中國畫,是十分有必要的。然中國畫的基本原則如物我兩忘、造化心源、傳神寫意等,其基本語言方法及其規范如以書入畫、筆墨合一,是不變或少變的。筆墨風格有傳統性,傳承相近的畫家多風格相似的筆墨風格,如董源和巨然,李成和郭熙,馬遠和夏圭等均如此。時至當下,畫家的風格面貌區別不大,這里不是強調要拉開距離,而是要注重筆墨風格的特殊品格[5]。
現代諸多畫家強化視覺張力,竟以西畫標準要求作品效果,無視筆墨風格講究細微品味的特點,“出奇出怪”是基本問題的顯現,作品因此大而空,虛而假,“有筆”“有墨”的合一最終走向風格格調的評判。郎紹君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釋讀“格調”的內涵。“如果說藝術風格是藝術家把握世界觀的一種態度和方式,藝術格調便是對這種態度和方式價值的判斷。人們可以勉強說風格無優劣(假設都是有個性的風格),卻必須承認格調有高下。具體言之,格調是透過形式風格、語言和技巧運用折射出來的人格價值——寓于美中的真與善的程度,業已形式化、物質化的精神品位。在中國藝術史里,格調是判定雅俗優劣和最終價值的主要尺度”[6]。
當然,藝術的格調高低還涉及作品內容——既包括與時代相契合的現代風貌,也包括從具體現狀抽象出來的心靈體現。筆墨應當隨時代發展,藝術也應當反映時代的精神面貌和審美追求。這要求在繼承傳統技法的基礎上,不斷探索新的表現手法和主題,賦予傳統筆墨以新的生命力。傳統技法的煥發源于對自然的規律性和時代性的契合,充滿豐富的文化內涵、自信和使命感,將中國畫的傳統要素和寫意精神發揚下去,這便是對“有筆無墨”與“有墨無筆”合而為一的終極期望。
參考文獻:
[1]張修佳.孤獨與自由[M].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7.
[2]張修佳.中國藝術家個案研究——田黎明[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
[3]張彥遠.歷代名畫記[M].秦仲文,黃苗子,點校.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
[4]郎紹君.探問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5]郎紹君.筆墨經驗[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6]郎紹君.現代中國畫論集[M].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