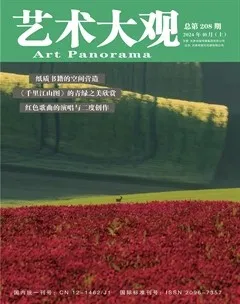真實與模擬



摘 要:在工業革命后,現代印刷技術現世,當下時代中數字藝術蓬勃發展,數字化對人民生活具有多方位的影響,版畫的創作手段及途徑隨數字技術的發展同樣被推陳更新,出現了多者在傳統創作理念上的再創新。因受工藝程序和制作材料的影響,版畫使其擁有與其他繪畫不同的表現方式,這些特點體現了版畫本身得天獨厚的藝術語言,也決定了其必將與時代共進退的特性。印痕作為版畫的重要屬性之一,在奧克威爾克的《藝術基礎理論與實踐》中談道:“肌理”分有四種基本類型,“真實的、模擬的、抽象的和設計的”,隨著數字技術不斷進化,用數字藝術制作的版畫印痕在文中被定義為數字化印痕,其所展現的內容、情緒也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那么如何在遵循版畫本體印痕屬性的同時,合理地延續數字化印痕的生命力?筆者將以此作為本文主線,對版畫創作中的數字化印痕表現技術進行論述,以此為契機來體現數字技術對現代版畫創作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數字技術;版畫印痕;技術展現
中圖分類號:J2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8-00-03
“肌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質,我們去觸摸任何物體,都會感受到肌理的存在,筆者以為版畫印痕與該“肌理”為同一概念。傳統版畫中,印痕的表現是通過對板材的轉印而呈現在紙或布等物品上的,其中的板材屬于可觸摸的、具有物理特征的實物,往往其印痕也屬于可觸摸的實物,而文中數碼版畫的“印痕”卻有所不同,其表現的形式卻為不可觸摸的、虛擬的、數字化的。
一、印痕中與生俱來的“觸感”
如何在當代文化語境下界定版畫的屬性?筆者認為,“版畫印痕”是最直接的語言形式。版畫不僅具有“復數性”和“間接性”等屬性特點,同時擁有最本質的特征,因其靠“版”的間接轉印從而產生了獨特的、反映板材特性的物理印痕。所以,經過長期的實踐與探索,作為一門以技藝見長的傳統的視覺藝術形式,“間接性”和“多樣性”已經不能完全概括當前文化背景下的版畫屬性特征,“印痕”也是作為表現版畫藝術屬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版畫由“印刷”而實現的“與生俱來”。
談到“與生俱來”,是筆者對傳統版畫屬性特點的再明確。“我們的語言,通過光滑、粗糙和堅硬等詞語,顯示了觸覺可以告訴我們的關于客體的本質”[1]。無論是光滑、粗糙和堅硬的物體都可以通過觸摸來感受它凹凸起伏的特征,所以通過觸覺來感受物體本質屬性美感是一種感受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人在視覺上的觀感同樣也可以實現對物體本質屬性美的感受,即使是物體本身特有的肌理,如水印版畫的木紋肌理,齋藤清的水印木刻作品《妙心寺》,其畫面干凈明麗且構成形式簡潔,為避免畫面過于單調和視覺的分散,作品借助木材本身的肌理來轉印出不規則的紋理效果,從而增強畫面的感染力(見圖1);除此之外,還有銅版畫的金屬質感以及石版畫的石材顆粒感等,如應天齊的代表作品《西遞村系列》組畫,他在利用木板拼貼方式的同時,綜合利用不同板材的肌理來表達自然景象,很好地將版材自帶的紋理與現實自然景物的肌理對應,具有寫實般的視覺效果(見圖2)[2]。這些肌理都是對其物理板材屬性的真實反映,所以美感是以對形象的直接感知方式來進行的,這個過程包含了視覺與觸覺的交互體驗[3]。然而版畫的印痕既是對物質肌理的表現,也是對物質屬性的表現,通常版畫創作中的印痕與“版”是相互交融的,版畫中的“版”不僅承載了板材本身自帶的媒介信息,同時還承載著藝術家的創作情感。
版畫中印痕的表現是多樣的,印痕對于物性的真實反映是基于“真實的實物”,而在筆者看來,該“真實的實物”意指為媒介或介質,媒介的變化也促使了版畫物理印痕具有多樣性,所以印痕屬性也是版畫區別于其他畫種的主要要素之一。
二、數字化印痕的產生
版畫作為一門通過以印刷的方式逐漸發展的藝術門類,無論是古代雕版印刷,還是新興木刻運動的推廣,至今始終離不開技藝的作用與影響。在科技發展與進步的加持下,數字印刷技術通過簡單的數字化生產和便捷的快速出圖,為版畫藝術家提供了更為開闊的創作空間,以至于藝術家能夠選擇更為多元的方式進行藝術創作。因此,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嘗試使用數字技術的手段去探索更多的版畫語言,但是數字技術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版畫的屬性關系,如在版畫本體語言上的缺失,包括間接性和印痕質感等。
作為以數字技術為主要創作手段的數碼版畫,它是否也具備與傳統版畫相似的“印痕”屬性呢?答案是有的,只不過它的印痕在未經過轉印呈現之前是虛擬的、數字化的。數碼版畫創作著重強調的是版畫語言的實驗性、多元性和融合性,有別于傳統版畫的藝術語言,它強調對不同版材印刷效果的疊加、互換和融合,試圖通過數字模擬技術拓展和突破傳統版畫材質的邊界[4]。不同于傳統版畫印痕,數字印痕的產生是靠計算機的基本語言在執行與表現,即不同的代碼會驅使計算機執行不同的命令,從而出現不同的繪制效果。另外,不同的數字軟件在功能設置和繪制效果方面都有區別,但始終是靠藝術家的主觀思維在操控著后臺數據,從而出現不同的畫面效果。
其實早在21世紀數字藝術從最初的計算機藝術,演變為如今以數字技術為媒介的藝術創作,如CG繪畫、交互藝術、AI藝術、數字影像等,其中也包含了數碼版畫。不過在藝術表現過程中,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都離不開對現實的模擬,如用于模擬藝術風格的非真實感繪制技術(non-photorealistic rendering,NPR),該技術可以通過模擬不同藝術作品的肌理、色彩、線條等風格特征,從而生成具有鮮明的藝術風格和美學特點的圖像;還有近幾年推出的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基于大數據的作用下,將現有的藝術創作方式及圖像資源融合在一起,對固有的藝術創作模式進行了創新和突破。在藝術作品中也有部分范例,如首屆中國數字大展中胡特的作品《九歌圖》,該作品模擬古代長卷的形式進行表現,并通過現代CG渲染技術再現楚人的精神境界;又如20世紀60年代末,哈羅德·科恩開發的AARON繪畫程序所繪制的《帶裝飾板的亞倫布面油畫》,畫面的顏色及對象的線條表現,有著類似野獸派的語言穿透力(見圖3)。同理,數碼版畫中的數字化印痕也是依靠數字化模擬及合成而產生的,正是因為數字化的模擬技術,使其具有無限的創作可能和相互融合的空間。
三、數字化印痕的表現
關于數碼版畫中虛擬形式的數字化印痕,它的實現如同奧克威爾克眼里的“模擬肌理”。筆者以為《藝術基礎理論與實踐》中的“模擬的肌理”是對現實肌理的夸張化,或者是一種觀感上的錯覺,從而對現實事物“可識別性”的增強。在傳統版畫中,模擬印痕也許很早之前就已經存在,這是藝術手段上的主觀性體現。相對于物理的印痕,筆下數碼版畫中的模擬印痕來源于數字技術對現實的模擬與仿造,甚至是“聞所未聞”的虛擬化。
數字技術為藝術創作提供多重技術條件的同時也影響了版畫藝術形式的發展,導致版畫與其他藝術形式之間的概念界限越來越模糊。相對于傳統版畫屬性特點的部分缺失,我們如何繼續維持數碼版畫的發展活力?在傳統藝術視角的構架內,要探索版畫的內在價值,必須超越傳統版畫的“技巧”與“技藝”觀念,我們是否可以對數字化印痕進行物理呈現?也就是把虛擬的印痕轉化為物理的可觸摸的印痕。例如,國內就有美術專業院校曾以攝影、圖像為創作元素,通過數字平臺實現圖像轉換,最后以現代印刷技術的方式輸出圖像,以此進入版畫創作的當代語境的做法;例如,第十四屆全國美術作品展版畫展區中的于瑋萍、諶汐雨曉的銅版畫作品《天問·探月》,以及周慶的《越山跨海——中國特大橋》版畫作品,他們前期通過運用數字技術的輔助處理,最后利用傳統版畫的轉印及再加工,呈現的畫面層次豐富,具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及畫面氛圍感。猶如該兩幅作品,運用數字技術來輔助制版的藝術家數不勝數,但最終還是以傳統版畫的形態來呈現,這一類作品與直接噴繪輸出的數碼版畫作品不一樣的是,他們因為有了自己獨有的“版”的屬性,便有了版畫物理印痕的屬性,筆者認為這是對數字化印痕的一種合理表現方式之一。所以數字技術與傳統版畫創作的有機融合是未來數字藝術發展趨勢的表現之一,不僅影響當下的版畫創作形式,也將為未來數字藝術的無限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數字技術對現代版畫帶來的深遠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同時對傳統版畫本體語言的沖擊也不小。數字技術極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但如果手頭功夫不足,就會影響到人與作品之間的直接對話,以至于削弱人與作品之間的情感關系,好的藝術作品是需要藝術家源于內心極其虔誠的創作,說到底是人的創作,精神上的創作。數碼版畫之所以爭議不斷,部分原因在于數碼版畫作品的表現缺少制作過程中“量”的體現,以至于觀眾看不到作品所能夠呈現的手工痕跡,當這些特質被弱化后,作品的精神性也會隨之被減弱。“從傳統的模仿到機械的復制再到數字的虛擬,變化著的是作為符號的圖像與作為實在的現實世界間的那個關系。……當一切都呈現為持存物的無蔽狀態時,藝術是否仍然具有某種拯救的最高可能?[5]”但圖像的發展終究還是離不開技術指引的,就像機械復制會影響傳統藝術的“本真性”一樣,也會影響到版畫本身所具有的本質屬性,以至于破壞藝術家對版畫所建立起的最初的情感。那么基于版畫在面對數字技術沖擊的背景下,如何將數碼版畫回歸到版畫本體“印痕”屬性中去?從而激發版畫藝術創作新的生命力。綜上所述,在版畫創作中對于數字化印痕的表現就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對現代版畫創作實現創新與突破的重要體現之一。
參考文獻:
[1]奧克威爾克,著.藝術基礎理論與實踐[M].牛宏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陳鳴鳴.對水印木刻創作寫實性語言的分析與思考[J].美術,2021,(03):152-153.
[3]何佳榮.印痕物語——版畫材質的物質性美感[J].美術觀察,2020,(02):65-66.
[4]羅娜.數字版畫的藝術語言與創作觀念探微[J].美術,2020,(10):142-143.
[5]孔國橋.“在場”的印刷:歷史視域下的版畫與藝術[M].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