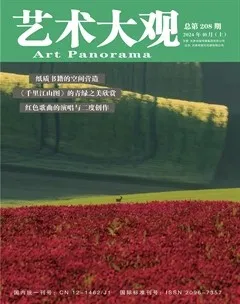感性結(jié)構(gòu)中的音樂體驗

摘 要:感性發(fā)端于主體自身,伴隨著被動接受的能力,其形態(tài)受客觀對象的影響,由主體的意識做出反應(yīng),進(jìn)而形成感官方式的交流。感性結(jié)構(gòu)來自對認(rèn)識對象的活態(tài)構(gòu)建,伴隨著聽,接受者在感知聲音的過程中不斷進(jìn)行一種感性的認(rèn)識,最后形成感知聲音結(jié)構(gòu)。面對直觀的藝術(shù)作品,如何形成一種審美理念?在查婭·捷諾文《心室》中究竟能聽到什么,一個屬于美學(xué)的感性之問,文章以《心室》為例,分別從感性結(jié)構(gòu)、《心室》的創(chuàng)作、聲音材料的使用,探索其感官上的音樂體驗,凸顯捷諾文歌劇創(chuàng)作中聲音理念的獨(dú)特性。
關(guān)鍵詞:感性結(jié)構(gòu);查婭·捷諾文;無限的現(xiàn)在;心室;聲音理念
中圖分類號:J614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357(2024)28-00-03
“歌劇已死”的論調(diào)在21世紀(jì)被反復(fù)提及,這種論調(diào)建立在接受者對歌劇的理念還一直停留在19世紀(jì)傳統(tǒng)的大歌劇形式,直到19世紀(jì)末臨近20世紀(jì)初,普契尼、理查·斯特勞斯之后,它的黃金時期就結(jié)束了。愈來愈多的青年作曲家以及現(xiàn)代派的作曲技法的出現(xiàn),打破了傳統(tǒng)歌劇的結(jié)構(gòu)樣式。歌劇除音樂、戲劇外,最重要的就是聲音。傳統(tǒng)歌劇的聲音以詠嘆調(diào)、宣敘調(diào)、重唱、合唱等表現(xiàn)歌劇的音樂性與戲劇性,查婭·捷諾文對于歌劇的創(chuàng)作聚焦于用聲音表達(dá)新觀念、訴諸新媒介的探索。捷諾文的歌劇中,聲音的材料是什么?聲音如何表達(dá)?這樣的聲音材料是否能承載一種感官體驗,或者感性經(jīng)驗?韓鍾恩老師在其文《情動于中形于聲——通過經(jīng)驗情況寫音樂》談道:“所謂的感性結(jié)構(gòu)力,就是基于原始情感的純粹音調(diào)與原始美學(xué)規(guī)范想象,依托藝術(shù)經(jīng)驗,通過審美觀照,所生成的音響意象及其結(jié)構(gòu)驅(qū)動力。”如何面對直觀的藝術(shù)作品去呈現(xiàn)與之相應(yīng)的審美關(guān)照?或者說通過形而下的音樂藝術(shù)作品,是否能夠成就形而上的音樂審美對象[1]?本文通過探討歌劇《心室》的聲音理念,探索其在感性結(jié)構(gòu)中的音樂體驗。
一、感性結(jié)構(gòu)與感性結(jié)構(gòu)中的音樂體驗
現(xiàn)代哲學(xué)在康德之前有兩個主要流派,一派叫理性主義、一派叫經(jīng)驗主義,理性主義者認(rèn)為,知識來自先天的觀念,這些觀念是人與生俱來的,要獲得知識,只要反思這些先天的觀念,加上基本的邏輯就夠了。經(jīng)驗主義者認(rèn)為,人的知識是后天形成的,一切觀念包括個人思考的觀念都需要建立在后天感覺經(jīng)驗之上。雙方一直爭論不休,這時,康德提出了一個新的框架,結(jié)束了一百多年來的爭論,給予哲學(xué)一個新的起點。首先提到的“感性”,此“感性”非彼“感性”,康德所說的感性并非我們平時說“一個人很感性”,他所說的感性可以叫作感覺能力,也就是視覺、觸覺、聽覺、嗅覺等。不過康德并不關(guān)心這些感覺能力的生理結(jié)構(gòu),而是要解釋感覺能力的本質(zhì)——接受性和直觀性。
那這兩種感性認(rèn)識能力是什么呢?康德在其《純粹理性批判》中,并未對“純粹理性”發(fā)起攻擊,而是指出其局限性的同時,展示其潛在的可能性,并將其置于通過感官途徑獲取經(jīng)驗之上。康德把感性理解為一種外部對象給予我們表象的能力,直觀形式就是把感性對自在物的刺激做出反應(yīng),并認(rèn)為感性的作用是能提供一種認(rèn)識形式。康德認(rèn)為感性由兩種成分構(gòu)成——空間和時間。空間是外感官的形式,即感知一切外部現(xiàn)象的先天直觀條件;時間是內(nèi)感官的形式,即感知一切內(nèi)部現(xiàn)象的先天直觀條件。康德對感性的理解與研究,為藝術(shù)審美提供了明確的導(dǎo)向。
就“音樂體驗”而言,更多傾向于一種審美判斷,在聽的過程中,對接收到的音樂語言或聲音材料進(jìn)行組織,在感性中形成一定的聲音秩序,關(guān)聯(lián)于感性結(jié)構(gòu)中的音樂體驗,存在方式在于主體被動地寄身于聲音對象中。吳佳老師在其博士論文《感性聲音結(jié)構(gòu)并審美判斷形成的感性契機(jī)研究》中,提出了原創(chuàng)性的概念“感性聲音結(jié)構(gòu)”,這一概念強(qiáng)調(diào)感性在音樂體驗或音樂審美中的結(jié)構(gòu)性作用,尤其是在音樂的聆聽和理解中[2]。捷諾文《心室》是一個非常真實的聲音體驗場合,兩個人在樓梯上偶然相遇,并通過一個平常的事件意識到了他們彼此。這導(dǎo)致了一系列事件、感覺和感受,這些事件、感覺和感受是不連貫的,但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他們的展示中,它們形成了一個聲音序列的世界,這些聲音序列導(dǎo)致了接受者在聆聽過程中具有的一種感性聲音結(jié)構(gòu)的主動性和趨向性。《心室》的感性中的音樂體驗旨在對作品、聲音進(jìn)行結(jié)構(gòu)性感性的聆聽,以及在聲音之外的意義如何通過聆聽的方式獲得。
二、《心室》的創(chuàng)作
查婭·捷諾文(Chaya Zernowin,b.1957)作為21世紀(jì)的探索者,她的作品打開了我們的內(nèi)在和外在世界,讓我們獲得了新的聲音體驗。捷諾文在其作品中關(guān)注的是隱藏在內(nèi)部的東西,但它也處于可感知的邊緣。音樂元素的本質(zhì)是直接處理的,而元素之間的直覺關(guān)聯(lián)似乎會產(chǎn)生其他看似“基本”的材料,就如同《心室》的結(jié)構(gòu)中,有許多可識別的聲音材料,每個材料都有自己的身份主張,但是當(dāng)這些材料相互作用時,將永遠(yuǎn)改變材料的結(jié)構(gòu)和身份,逐漸形成一種關(guān)系。用捷諾文的話來說,這些材料可以被認(rèn)為是思考音樂內(nèi)部的東西,音樂的基礎(chǔ)是什么,以及音樂產(chǎn)生可能性的方式。這些原始形式——音樂的基礎(chǔ)——恰恰是音樂所隱藏的東西,使人難以聽到的東西:音樂的材料必須被放大,才能透過裂縫窺視,伸展一個人的耳朵。
捷諾文在美國眾多學(xué)院現(xiàn)代派里更傾向于歐洲實驗音樂復(fù)雜的配器法、十二律音與微分音混合的音高材料、模仿電子音樂的聲響效果、液態(tài)化的和聲呈現(xiàn)、難以察覺的拍點律動、發(fā)音點距離微小或巨大的極不規(guī)則的節(jié)奏等歐洲當(dāng)代作曲家標(biāo)準(zhǔn)的技術(shù)配置。因此,受現(xiàn)代派作曲技法的影響,捷諾文在她作品中也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使用顆粒感的聲音材料——滴滴答答的顆粒音成為背景;樂思斷裂成為常態(tài);樂音的使用常常是孤立的單音;材料并置是縱向,想象不到的兩個材料放在一起;聲音體驗——注重聲音的本質(zhì),聲音材料視為聽覺景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材料是什么、會發(fā)生什么、將要表達(dá)什么,通過不同材料,挖掘聲音的深處。
《心室》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真正的多感官體驗,一種感性結(jié)構(gòu)中的音樂體驗,音樂成為嗅覺、觸覺、疼痛、極度脆弱、純粹的快樂或快感。這些狀態(tài)之間的轉(zhuǎn)換是不受控制和不可預(yù)測的。《心室》只有兩個角色,每個角色都與一位額外的歌手(內(nèi)部聲音)相連,他揭示了主角深處的潛意識,女高音的內(nèi)在聲音由女中音演唱,男中音的內(nèi)在聲音由男高音演唱。只有一個故事的暗示——一連串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情境、夢境、某些東西打開或關(guān)閉的節(jié)點時刻(因為某些事情或狀況想在一起或不想在一起)——因為戀人的內(nèi)在精神景觀被推向了結(jié)構(gòu)性的變化,所以內(nèi)部和外部的聲音并不總是一致。每一個角色都充滿了矛盾和曖昧。這對戀人在各自的混沌中掙扎,就像當(dāng)代許多都市人一樣,隱藏了自己的敏感,卻又獨(dú)自深陷在悲觀、焦慮、恐懼和迷茫中。
歌劇整體呈現(xiàn)出一系列墜入愛情的元素,這些元素主要以聲音材料交織在一起,當(dāng)男人和女人在不斷接觸愛的過程中,一方面會強(qiáng)烈感受到對方的美麗,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脆弱和不安全感,內(nèi)部心理的狀態(tài)使他們走上了不可預(yù)測的道路。
結(jié)構(gòu)方面,《心室》的時間思維以及敘事方式與傳統(tǒng)的歌劇大不相同。這部歌劇敘事速度很快,它在不斷地發(fā)展、變化、融合、分離、交匯。《心室》標(biāo)志著一種新的歌劇結(jié)構(gòu)或形式范式:流體形式(流體身份)——一種逐漸演變成無窮的形式結(jié)構(gòu)。傳統(tǒng)歌劇的結(jié)構(gòu)(或我們所說的音樂材料)是固定的,它的發(fā)展是建立在“音樂承載戲劇”特征之上的,因為它們在時間上展開(或不展開)。捷諾文的《心室》提出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有許多可識別的材料,每個材料都有自己的身份,但當(dāng)這些材料相互作用時,會永遠(yuǎn)改變材料的結(jié)構(gòu)和身份,逐漸衍生出一種或多種關(guān)系。當(dāng)這種關(guān)系的特征成為焦點時,它就變成了一個新的整體,它大于其各部分的總和,因此它包含的元素在只有原始材料存在時是無法想象的。《心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流體形式與愛的連接達(dá)到一種新的創(chuàng)造力。即使一個人認(rèn)識這對戀人,也永遠(yuǎn)無法想象一段感情會變成什么樣子。這種結(jié)構(gòu)呼應(yīng)了一種在感性結(jié)構(gòu)中不可預(yù)測和純粹對未知的興奮的音樂體驗[3]。
三、《心室》的聲音材料
(一)特寫
四位獨(dú)唱者演唱的文字,演繹了“情節(jié)”。它們包括主角的內(nèi)部和外部文本及其對話,臺詞由平淡到爆裂。比如,特寫一:116—143小節(jié)。第一次見面以及男主人公的夢:描述居住在現(xiàn)代都市的男女一次偶然機(jī)緣下的相遇、相戀。接著男主角內(nèi)心的幻象出現(xiàn),無數(shù)只螞蟻在爬,表現(xiàn)了個體對人類生活的恐懼和煎熬。特寫二——他:湖/她:水下溝渠:分部講述男人和女人作為“個體”與“集體”“與客觀世界”的對抗。男人陷入集體世界的窒息,女人個體的破碎。特寫三:412—442小節(jié)。她的來電、夢:外部表現(xiàn)為兩個人的通電,潛意識為女人內(nèi)心的焦慮。特寫四:512—535小節(jié)。第五次的談話和女人的夢:剝離——女人夢到臥室的苔蘚,拼命想剝掉,可苔蘚還在不停生長,感到焦慮和窒息,象征女人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恐懼。“女性獨(dú)立”的吶喊。特寫五:763—897小節(jié),沒說出的疑問:關(guān)于家庭、父母、孩子。我們會不會有孩子?你會不會成為一個好父親或者好母親?你會照顧我嗎?保護(hù)我嗎?
(二)聲音流
當(dāng)整個大廳被淹沒并充滿強(qiáng)烈的物理聲音時,這種聲音可能是移動的,也可能是靜止的。
譜例1
音響空間化,譜例1最開始的圓圈代表大廳,而伴隨的標(biāo)記表示聲源與大廳之間的空間排列(三重奏、四重奏、整個管弦樂隊等)。聲音從大廳的前部和后部傳來,這些聲音現(xiàn)在從大廳四面八方漂浮在房間里:低沉的鼓聲,弦樂中的喵喵聲,歌手聲音中對愛情失敗的刺耳聲。將色彩與動態(tài)色調(diào)相交,將原聲與電子疏離的聲音相交,將和弦與斑點般的音調(diào)相交。
(三)ASMR
安靜而極其親密的呼吸和微小的微觀噪聲,能喚起嘴巴或身體的微小運(yùn)動。通常連接到低音提琴、高音、歌手、管弦樂隊和電子設(shè)備承擔(dān)。
(四)夢
這對戀人意識到,與性有關(guān),無形中被迫成為家庭,對他們施加了強(qiáng)大的社會壓力。這些都由合唱團(tuán)和主角承擔(dān)。
第一場夢:(187—237小節(jié))男低音和男高音共同飾演男人內(nèi)心的獨(dú)白。初次見面、相愛后,先是夢見自己走過房子,有一棵樹,男人看到地板變透明,另外,成千上萬只螞蟻,像一張移動的網(wǎng),小房間構(gòu)成的無數(shù)家庭。房子和樹是家庭的象征,樹的出現(xiàn)代表攻擊性的力量。“螞蟻”象征生育繁殖,造成一種壓迫感,男人對未來婚姻的恐懼和焦慮。此時樂隊的聲音變成密集的點狀織體,顆粒音形容螞蟻。
第二場夢:(469—511小節(jié))合唱團(tuán)演唱,代表強(qiáng)迫性的社會壓力。女人主動邀約男人外出散步,內(nèi)心的聲音在說:我們像行走在一根拉緊的繩索上,沒有安全感。
合唱團(tuán)的唱詞:“太陽的心臟,在深處召喚,我被牽引著進(jìn)入你,愛在靠近。”第二場夢嵌套在第三場特寫中,隱喻之意存在于主角與合唱團(tuán)之間,或者男人女人與社會強(qiáng)加給他們的婚戀目的。這段唱詞真正的意義并不是字面上“愛情來到”的美好,而是捷諾文在設(shè)計五組聲音模組中“夢”所指的“社會壓力的無形逼迫他們成立家庭”,這部分都是由合唱團(tuán)和主角承擔(dān)。合唱團(tuán)從第三場特寫中作為一種噩夢出現(xiàn),隨后又在第四、第六、第七個特寫中加入,演唱與男人、女人不同的臺詞。
第三場夢:(660—762小節(jié))女高音和女低音共同飾演女人內(nèi)心的獨(dú)白,和第一場夢呼應(yīng)。大顆粒聲音材料(形容苔蘚,與螞蟻的小顆粒作對比),“苔蘚”被轉(zhuǎn)化為一秒鐘4—6個發(fā)音點的大顆粒。但這些大顆粒并未因為密度稀疏而顯得比小顆粒松散,樂隊各聲部演奏者已達(dá)到聲音極限。女高音快速同音節(jié)重復(fù),類似管樂的弦樂演奏頓音,合唱團(tuán)成員邊擊掌邊交換位置。女人的夢主要是苔蘚,我的臥室很長,沒有盡頭被苔蘚包圍和侵蝕,不能呼吸。這主要象征依賴,是否和女性主義有關(guān)?父權(quán)社會女性依附家庭,面對婚姻的恐懼。
(五)音從
這主要指由管弦樂隊不同部分演奏的不同音從,以及看不見的音從、肌肉和靜脈的音從、頭發(fā)的音從。
四、結(jié)束語
《心室》的首演向觀眾展示的是一種日常生活表象下的暗流涌動,簡約的舞臺設(shè)計在不斷反轉(zhuǎn)之間構(gòu)筑了清晰的戲劇結(jié)構(gòu)。激進(jìn)的樂器音色調(diào)制出來的聲音和圖像搭建了視覺與聽覺雙向的意識流。全劇在多方面打破了我們在常規(guī)認(rèn)知中對于舞臺作品風(fēng)格的傳統(tǒng)認(rèn)知。你不能真的用語言來描述它,而必須屈服于這些體驗并感同身受,或者讓自己被拉著走。這里的感性體驗是在樂器的聲音、插入的語音和思想片段以及電子支持的幫助下創(chuàng)造的一種聲音結(jié)構(gòu)。通過其情感力量引導(dǎo)到一個人可以聆聽的感知,以便成為所創(chuàng)造的感性的被動部分。
參考文獻(xiàn):
[1]韓鍾恩.情動于中形于聲——通過經(jīng)驗情況寫音樂[J].中國音樂,2024,(01):50-64.
[2]吳佳.“感性聲音結(jié)構(gòu)”及其音樂美學(xué)意義探析[J].音樂藝術(shù)(上海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9,(04):110-117+5.
[3][德]康德,著.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楊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