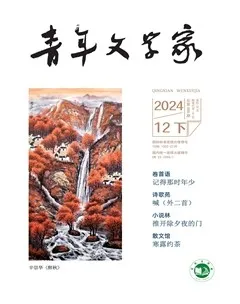正裝(外一篇)


周二,成旺接到通知,周五上午集團公司工會“情系礦山”文學采風團要來,礦工會讓他和幾名礦上的文學愛好者參加采風和文學座談會。除了全公司的二十余名業(yè)余作者代表以外,地區(qū)文聯(lián)有幾名作家編輯也要來。其中,有一位穆藝老師,他見過一次。接下來的幾天,成旺魂不守舍,他期盼著那個重要時刻的到來,說實話,他太需要穆老師親自來一趟礦上了。
成旺小時候就淘氣搗蛋,大人打不下,老師管不住,在人們眼里一無是處。后來上了技校,性格變得更加孤僻,老師在講臺上講井下知識,他卻抱著一本新華字典啃,以致后來他的專業(yè)課是通過補考才剛剛及格。后來,技校畢了業(yè),他被分配到柳西礦,下井、結(jié)婚、生子,不知不覺二十個年頭兒過去了,他也從井下被調(diào)到地面,成了單位一名倉庫保管員。
別人閑暇時打撲克、搓麻將、劃拳喝酒,而成旺卻把休息時間全用來讀書,礦上職工圖書館不多的文學書他幾乎都看遍了,他抽空就跑到距單位10公里的縣城圖書館辦了個借閱證借書來讀。后來,他把家安在了縣城,每周回家一次。
讀書是一方面,不為人知的另一方面是他竟然偷偷寫起了文章,但是他只寫給自己看,寫完了放在自己的床頭柜。別人寫個東西到處投稿,在公司報紙上發(fā)表個“豆腐塊”也大肆宣揚,唯恐沒人知道。成旺沒有被這些人感染,也不愿意同流合污,小時候被打罵,被排斥,給他心靈造成了嚴重傷害,所以他養(yǎng)成了獨來獨往的性格,換工作時領(lǐng)導(dǎo)問他想去哪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倉庫,那里和人打交道少。
如果不是舍友看了他一篇回憶奶奶的文章,如果舍友沒有偷偷把他寫在稿紙上的文章拿給礦文學協(xié)會會長,如果會長沒有打印出來投給地區(qū)文聯(lián),成旺也不會在幾年前在地區(qū)文聯(lián)年度文學評獎中獲得散文一等獎。
成旺就在半推半就之間被礦上派到地區(qū)文聯(lián)領(lǐng)了獎。文學協(xié)會會長把他介紹給文聯(lián)副主席、著名作家穆藝老師。穆藝老師比他還小幾歲,但沒有一點兒架子,在會上讓會長介紹了成旺的成長經(jīng)歷。穆藝老師不管是在會議總結(jié)時,還是后來參加本地區(qū)各類文學活動時,都把成旺作為一個典型,給他定位為一個失足青年變成了一個文學青年,說是文學改變了他的命運,而且還希望他成為一名文學新秀。再后來,成旺加入了集團公司文學協(xié)會和地區(qū)作家協(xié)會,在地區(qū)文學雜志發(fā)表了大量書寫煤礦人和事的散文隨筆,本地幾個公眾號也紛紛轉(zhuǎn)載他的文章。
煤礦注重的是安全生產(chǎn),人們關(guān)心的是收入高低,而對于文學這個逐漸小眾化的愛好許多人顯得漠不關(guān)心。成旺除了與文學協(xié)會會長和幾個寫文章的工友有時交流交流,其余人則熟視無睹,不和他聊這方面的話題,他有時候主動提起,問別人看自己最近寫的文章沒有,大多含糊其詞,個別人糊弄他說看了,當問起寫得怎么樣時,一個“好”字就交代了。
穆藝老師的即將到來,無疑給成旺這顆敏感的心增添了信心。連著兩個晚上,他都沒有睡踏實。
周四上午,礦工會又通知,為了體現(xiàn)煤礦職工良好的精神風貌,要求參加活動人員按照出席大型會議時才有的要求,穿正裝,戴企業(yè)徽章。現(xiàn)在是七月下旬,正是大熱天,那正裝就應(yīng)該是白色半袖襯衫和黑色褲子。
成旺吃了午飯,在宿舍想躺一會兒補補覺,卻總覺得有什么事情沒有辦,心里慌慌的。他從床上起來,打開自己的衣柜,從里面翻找襯衣和褲子。
作為一個倉庫保管員來說,他參加礦上各種會議和活動的機會極少,而且需要他參加的培訓(xùn)班或職工大會,都不需要穿正裝。他平常沒有穿白襯衣的習慣,總覺得穿白襯衣是機關(guān)干部的專利。他翻箱倒柜,找出兩件白襯衣還是長袖子的,黑色褲子皺皺巴巴不成樣子。他和隔壁住著的倉庫主任打了一聲招呼,打了一個車,直奔縣城。
晚上,成旺做了一個夢,他夢見穆藝老師在座談會上又狠狠表揚了他一番,礦領(lǐng)導(dǎo)、隊領(lǐng)導(dǎo)、文學愛好者或多或少也都在發(fā)言中提到他,文學座談會開成了他的表彰會,讓籍籍無名的他在一夜之間紅遍礦區(qū)。他甚至在夢中把自己的發(fā)言捋了三四遍,感謝領(lǐng)導(dǎo)們和老師們給自己參加座談會的機會,感謝穆藝老師的一再鼓勵和幫助,甚至提到朋友歪打正著幫自己投了稿獲了獎,最后感謝文學把他從一塊河灘里普通的頑石變成了文學園地里一塊可以雕琢的玉石……
可惜,美夢最終沒有成真。周五上午,穆藝老師沒來礦上,他去省城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去了,其他來的老師對成旺沒有太大印象,座談會上根本沒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中午,成旺心不在焉地陪采風團的人到食堂去吃自助餐。一根粉條從筷子上滑落到餐盤里,他胸前被甩了一滴帶辣椒的油點子,那紅色油點子瞬間在胸口暈染開來,他到縣城千挑萬選新買的雪白的襯衣仿佛撕裂開一個口子,好像能窺見他血紅的跳動的心臟……
補 牙
當我五十五歲內(nèi)退的時候,我的牙齒也紛紛撂挑子,不斷出現(xiàn)各種狀況,我不得不一次次走進牙科醫(yī)院,重復(fù)進行拔牙、補牙這樣一個惱人的過程。
我第一次牙疼的時候是在我換完牙不久。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吃晚飯的時候,當我把一粒醋泡花生放入口中,左邊的上下牙齒咀嚼的瞬間,一股錐心般的疼痛從左下邊第三顆臼齒穿過肩胛骨、心臟、盆骨、膝蓋,直至后腳跟,那個鉆心疼啊,是我有生以來遇見的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我扔下碗筷,捂著嘴,在床上疼得直打滾兒,并不時發(fā)出各種怪叫。以前見過母親牙疼時候的樣子,以為她有些虛張聲勢,如今發(fā)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姐姐在一邊說著風涼話:“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母親則告誡父親,以后再不能讓我吃糖了。我是記吃不記打,家里的白糖、紅糖、冰糖,母親藏在哪里我都能找到,而且我擅長打持久戰(zhàn),總會把它們在母親要做甜點之前都逐一消滅。父親則自我檢討,他經(jīng)常帶我出去,他工友們送給我的糖果之類他從來沒有制止,出現(xiàn)蛀牙是遲早的事。這顆
蛀牙整整陪伴了我四十年,不時會搗亂那么幾天,讓我把過往品嘗糖果甜食的時光再回味一番。
我的第二顆牙開始疼是在我蛀牙掉落的第二年。這顆牙是左下邊的第二顆臼齒,只要一上火就疼。我用了許多偏方,花椒泡酒后含上,用藥物牙膏早晚刷牙,吃牛黃上清丸和龍膽瀉肝丸,不知道哪一個起了效果,兩天后牙雖然不疼了,但開始周而復(fù)始,疼一陣停一陣。后來,它開始晃動起來,影響了我說話和吃飯。我說話時變得走風漏氣,唇齒不清。自從十多歲第一次牙疼以后,我就一直用右邊的牙齒咀嚼,害得兩邊的臉不一樣大,右臉比左臉大了二指寬。有時候試著用左邊的牙咬東西,咬不了幾下,就觸發(fā)疼痛的神經(jīng)了,所以輕易不敢嘗試。我閑下來仔細琢磨了一下,這顆牙疼痛的原因,除了和第一顆牙同樣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二十多年前,我周末愛去麻將館和人們搓幾把麻將,無論誰輸誰贏,最后晚上都要在面攤上吃飯。那時候豪爽得很,我根本不用起子,拿起啤酒放在嘴邊,用后槽牙一咬,瓶蓋便從嘴里掉在地上發(fā)出清脆的響聲,感覺自己那時候非常瀟灑,帶來的惡果就是如今牙齒松動疼痛。本來有心去牙科醫(yī)院看看拔掉它,但好多人勸不要亂拔牙,容易感染,會降低免疫力,還會得心肌炎,有的還造成死亡。我心中畏懼,便慢慢等著它成熟后,在某一個不經(jīng)意的時刻自己掉下來。我也沒有洗,直接拿了一張紙巾包裹起來,輕輕放到了平常存放各種證件的抽屜里。
我第三、四、五、六、七、八顆牙疼的時候是在我第二顆臼齒掉落的半年以后。這時候,我覺得自己斷崖式衰老,身體各個器官大不如從前,兩鬢的白發(fā)迅速向頭頂蔓延,右邊的眼角旁出現(xiàn)了五六個豆大的老年斑。這六顆牙齒全是上面門牙右邊的牙齒,像是商量好似的,一齊疼,一齊晃。我每天用舌尖舔它們,看它們搖晃到了什么程度。這幾顆牙疼痛的原因,除了和第一顆牙、第二顆牙同樣的原因外,我覺得應(yīng)該是它們的服務(wù)年限到了,我自小到大沒有整修過它們,提前報廢是必然的。
如此大規(guī)模的牙病,我不得不走進牙科醫(yī)院尋求診治。
大夫在檢查室讓我躺下,他則戴著口罩和頭燈,一手一個鑷子,讓我張開嘴,仔細檢查了一番。然后,我們回到他的辦公室,我和他相對而坐,他拿著一張表,開始詢問:“牙疼有多長時間了?”
我答:“半年多。”
大夫問:“你的牙總體損壞嚴重,為什么不早些治療?”
我答:“以前我看人們種一顆牙得一兩萬,想著以后攢下錢再來。”此時,不禁想起原先我們那個煤老板鄰居,天天露著滿口金牙招搖過市,一說話晃得你睜不開眼。
大夫問:“你有什么慢性病,比如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
我想了想,答:“高度肥胖,我家遺傳。”
大夫頓了頓,又問我:“你喜歡什么體育鍛煉?”
我這次沒有猶豫,隨口就說:“打麻將!”
大夫被我逗樂了。
我趕忙替自己辯白:“打麻將就是體育項目啊!”
大夫忍住笑說:“我又沒說不是。你去放射科拍個片,拿上片來找我。”
結(jié)果,大夫一看片子,說我牙齒腐蝕厲害,牙根都沒有了,最后只能做假牙套來固定假牙了。
我說:“我老覺著那幾顆牙長長了,怎么會沒有牙根?”
大夫:“什么長長了,是牙齦萎縮,懸在那兒了。”
消除炎癥后,我才能繼續(xù)拔牙、安假牙,所以還得來牙科醫(yī)院多次。
妻子有一次陪著我上醫(yī)院,順帶洗了一下她的牙。大夫說她的牙齒非常好。妻子就悄悄和我說:“一樣的水土,每天一個鍋里吃飯,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問我?我哪兒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