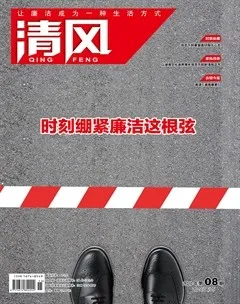聚天下賢能而用之

“任官唯賢才,左右唯其人。”《尚書》中的這句任人之論,影響了中國數千年,從此“任人唯賢”就成為國家選人用人的政治原則和優良傳統。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論語集注》卷七)“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資治通鑒·周紀》)在古人看來,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第一位的。既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又有過人的才干,二者高度統一于一身,這樣的人才能稱為賢士。
正因為賢士的可貴,周文王才心心念念四處訪賢,渭水一遇,則視如珍寶,奉若神明,使姜子牙的經天緯地之才得以充分施展和發揮,佐周滅商,改天換地。
伯禽受封魯國,其父周公很不放心,“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杜鵑啼血,苦口婆心,核心就是一點:你不要因為受封于魯國成了一方發號施令者就怠慢賢士。
諸葛亮是個遠近聞名的大賢,在當時紛亂的東漢末期,臥龍先生的名號格外引人注目。為得到他的輔佐,有皇叔身份的劉備不惜自降身份,三次屈尊拜請躬耕于南陽且小自己他不少的一介“村夫”。“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劉備的精誠之心深深打動了“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諸葛亮,從此,無論形勢多么險惡,時局何等艱難,始終如一,志比金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終成大功,三分天下有其一。故此,劉備生前曾由衷贊嘆:“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此外,還有蕭何月下追韓信、燕昭王筑黃金臺等千古佳話,充分印證了“尊圣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的千古鐵律。
任人唯賢顯然不是一個小題目,而是具有成敗興亡的戰略性。《呂氏春秋》中記載了一則著名的晉國大夫祁奚薦賢的故事,就極好地體現了唯德唯能、任人唯賢的精神。“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四問四答,不過區區數語,但字字閃耀著不滅的光輝,“國人稱善焉”就是最高的贊譽與肯定。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賢才與否,不能單憑主觀認定,所用非人,后果還是十分嚴重的。趙括的紙上談兵,坑殺了趙國數十萬虎賁勇士,蔣干的夸夸其談,葬送了曹操的一統雄心。此例多多,舉不勝舉。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將不可多得的寶貴賢才選出,并將其用在合適的位置,使其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呢?兩千多年前,孟子就給出了堪稱英明的思路和辦法:“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
這就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識賢,辨賢,然后大膽用之。
當今世界,競爭日益激烈,其中的關鍵就是人才的競爭,禮賢下士,求賢若渴,聚天下賢能而用之,不只是時代之要求,也是擁有光明未來的萬年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