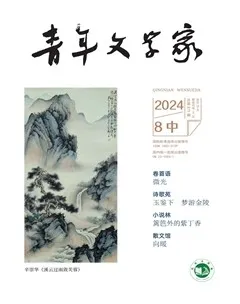吃飯
記得小時候,生活困難,很多人家只能保證一日兩餐,其實也有早餐,但極簡單,煮一個紅薯,燒一個土豆就權當早餐了。
1970年,8歲的我上小學一年級,父母均為雙職工,姐姐在北方老家,雖然我排行老二,但實質只有我一個孩子生長在父母身邊。父親是南下老干部,行政18級,月工資83.4元;母親在五金公司,月工資也有30多元,所以在當時我算是很幸福的了。每天早晨,母親都會為我熱一碗豆米飯,而我也總是站在窗臺上吃。上學的同學們從我家門前路過,指著窗臺上的我說:“快看,何老二又在吃蛋炒飯了。”每個人都投來無比羨慕的眼神。
后來,改革開放了,當我考上大學回來,同學們也經常在一起吃飯喝酒,那時館子很少,都在家由老人做,現在想起來也算奢侈了。
參加工作踏入社會后,我做了醫師,請吃飯的場合也越來越多。我還有點兒酒量,只要有請必到,到了必醉。回想起來,那時人與人之間關系非常單純、質樸。漸漸地,人的處境地位也發生了改變,我身邊的同學和朋友有的當上了大官,有的當上了老板,有的當上了銀行行長等。參加的次數多了,我漸漸明白,其中的奧妙還真不少。
有的飯局雖請你去了,但你只不過是陪襯而已,那種尷尬場面真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有的飯局吃了還欠別人的人情。俗話說:“吃人三餐還人一席。”每次回故鄉,我都會約上過去的發小兒和同學一聚,幾年下來,次次都是我在約他們,而就不見他們約我一次,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后來再回去,雖然也很想見面聚會,但始終沒有了心情。多年前,一名同窗被單位除名,大家爭先恐后請他吃飯,給他安慰和鼓勵,我當然也不例外。后來他身陷囹圄,我到監獄看了他兩次,每次給他三五百元聊表心意。常言道:“人在落難時,對別人的幫助和關心是最令人記憶深刻的。”時過境遷,他早已出獄。今年春節前的一次聚會,我帶著醉意略開玩笑地對他說:“我調離家鄉十四年這么長時間,回來兩次都是我請你,你從來沒請我吃過一次飯呢!”萬萬沒想到,他竟當場勃然大怒,說給我1萬元還清人情,嘴里還不干不凈!我頓時無語。
其實,很多做人做事的淺顯道理誰都清楚,然而實際生活中并非人人都這樣想,這樣做。我是一個天生隨性的人,了解我的朋友稱我為“性情中人”,不了解的就叫我“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即便今年我62歲了,依然如此。與故友開懷暢飲,無拘無束,酒過三巡,我會情不自禁地朗誦一首自己寫的詩詞,或唱上一首自覺得意的歌曲助興,也往往把自己的想法亮個底朝天,以致經常得罪人,醒來后悔莫及。
退出了職場,我對于飯局又有了新的體會。上班時,有一病人,全家老小經常找我看病,我總是熱情接待,傾力相助。他三天兩頭兒約我吃飯喝酒,酒后那些話真是感天動地。一來二去,我也安排家宴回請他,從內心把他當兄弟了。可誰知,我退休半年有兩次接到他的電話,說某天約我聚會,我當時還很感動,畢竟退休了,別人還惦記著你,就爽快地答應下來,誰知竟再無消息。第三次,他又發微信說再請我吃飯,我未回復,打電話來我也不愿接了。
就在前天,大學同學從英國回來,同學紛紛趕來,我也榮幸被邀請。時值中午,以茶代酒,大家相談甚歡,有人生的回味總結,也有老年的夢想和憧憬,有東西思想的碰撞,更有時光飛逝的感嘆。不知是誰提議,今后同學和朋友應經常聚會,但要采取AA制,得到大家一致贊同和熱烈響應。
一位朋友說:“現在請吃飯不是別人領你人情,而是別人給你面子!”的確,吃飯有很多講究,但和誰吃最為重要。我常自責,用自己的心態去要求別人,是多么幼稚可笑。人和人相處自然平淡最好,保持適當距離才能產生美感,“相見不如懷念”。沒有誰欠誰的,沒有誰該誰的,只有誰在乎誰,只有真心換真心。對于那些不懂得珍惜友誼,不懂感恩,滿身銅臭的人,就當是過眼云煙吧。飯,我們每天還得吃,還要開開心心地吃。愿歲月靜好,你我慢慢變老。生活教會了我們,只有放下才會快樂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