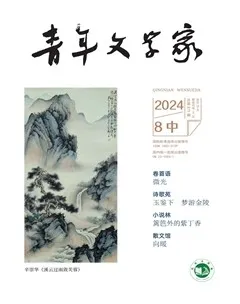雜說“憋得慌”
之所以給“憋得慌”冠以雙引號,是因為我想另類地評說一些事,給他貼上一種別樣的標簽。
自從走上詩詞創作和文章寫作的道路,我就一直在鍥而不舍地碼字,現在也算是一枚文學“碼農”了。雖然天資無奇、文采一般、底蘊平平,但我仍然是激情滿滿、樂此不疲。我突然冒出一個怪誕的想法:我為什么要不停地寫?因為不寫憋得慌。自從遇見這個“憋得慌”后,他便時不時地騷擾我一下。隨著時間和過程的積累,他的誘惑也在不斷增強,因此進一步解讀他的念頭也就越發強烈,當真有些不吐不快就“憋得慌”的感覺了。既然放不下,索性拿起筆,勾勒一些粗枝大葉吧。
我曾和“憋得慌”有過一次短暫接觸,就是在拙文《我的興觀》寫作時。文中有這樣一段敘說:“我在敬仰蘇軾和李白等大文豪、大詩人的同時,總有一個怪誕的想法。我猜想,他們滿懷天下、滿腦思想、滿腹情懷、滿身風骨、滿手文章,因此他們提筆天成。他們才華橫溢、不吐不快,要不我總覺得,他們憋得慌。反觀自己是偶興奇思、偶觀世道、偶露傲骨、偶爾風流、偶得幾字,舞弄些許點墨,紅頭漲臉,落筆艱難,也是憋得慌。雖然和他們不在一個維度,境界懸殊,但‘憋得慌’,也不失為一種創作動力吧。”我把他列為一種創作動力,主要是源于我個人的創作感受與文學初心。懷揣著這份沖動,摸索著這條藤蔓,我想嘗試一下,能否摸到一個瓜。
先追根溯源,穿越時空回去拜見一眾先賢圣哲。
白云繚繞的崆峒山,常年覆蓋著茂密的青松翠柏。在一處山峰的平地上,有幾間掩映于小竹林中的茅草屋,院落中的石桌旁圍坐著一眾老者。為首之人黃冕、黃袍,其余之人白冠、白袍,他們在靜觀修道、參悟自然、體察萬物。是他們定音律、造文字、置內經,是他們計畝設井、劃野分州、規制民范、培育耕織。其中,黃衣老者乃中華始祖黃帝,白衣老者中有伶倫、倉頡、岐伯等先哲。正是因為黃帝胸中充滿了教化天下、廣濟蒼生的宏愿,他才為中華民族釋放出磅礴的文明力量,生生不息千萬年。完成使命的黃帝,瀟灑、寫意地乘龍飛天。
西行路上的函谷雄關,在東來紫氣中迎來一位老者。老者一身灰色衣帽,手中一布袋,座下一青牛,緩緩進入關城。善觀氣象的關令尹喜識得來人便是老子,當世大能。于是,尹喜便以放行出關,外加幾個饅頭為條件,請老子留下了萬世經典《道德經》。如果老子沒有參宇宙運行、觀天地變化、聞萬物生機,他就不可能納德道于胸、合天人為一,更不會有《道德經》從他的筆端奔騰而出。而后,一身輕松、淡泊的老子,騎牛西去,消失在黃沙煙霧中,成為一個傳說。
“沂水清波濯吾纓,浩歌一曲伊人行。”玄服孔子率一眾弟子,疲馬凋車,行道遲遲于周游列國的途中。無論窮通否泰,他都能守道彌堅,而且老當益壯。盡管顛沛流離,他卻并未稍貶其志,仍然恪盡教學布道之職。他有“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修養,他能“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歷經滄桑、遍游列國、積淀一生的他,噴薄而發“德不孤,必有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經典言論。最后,一生從容的他,翩然邁入圣道,步入人心。
以上三賢位列中華民族史神人、哲人、圣人的巔峰。他們的使命就是破鴻蒙、立德行、開太平。他們胸中裝著天地宇宙,心中裝著天下蒼生,腦中裝著和諧萬邦。他們以德、以道、以仁砥礪自身,他們以生、以合、以和為己任。他們抱負滿懷、志向盈懷,他們抱堅守志、知行合一。他們盡情釋放、恩澤萬世。他們思想的“憋得慌”蘊含天地大道,噴薄而出則大氣磅礴,實乃至高境界也。
繼續穿梭,來到白帝城,又順著滾滾長江東下,遠遠望見一葉扁舟。船頭一道人影,正張開雙臂擁抱著無盡長空。而他的那聲“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卻久久回蕩在歷史長河中,宣泄著他憋在心中的萬般情緒。
他就是李白。大唐盛世降下了李白,也成就了詩仙。他飽含天馬行空的想象,大氣磅礴的氣勢,飄逸奔放的格調,恢宏壯闊的意境。他的心中永遠有一只展翅的大鵬。雖然他一生歷經坎坷曲折,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艱難行路中,但是他從未放棄過對夢想的追求,他一直追逐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他“斗酒詩百篇”,恣意縱橫、天成妙筆,揮灑人間處處詩。然后,他乘著鯤鵬,奔向了屬于他的仙境。
我們繼續追尋“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就是聞一多先生筆下的杜甫。他胸中裝滿家國天下的儒家思想、悲天憫人的大愛情懷、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他用詩詞書寫完美道德之形象、跌宕起伏之人生、至性至情之真身,行走天下。他替黎民百姓呼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切膚之痛。國雖破、山河在,一直是他的心心念念。一道收復薊北的消息,便令他欣喜若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就這樣,我們身邊的杜甫,煙火人間的杜甫,在詩圣之路上徐徐前行,周身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和真善美的光芒。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也,天才、奇才、全才“三才”蘇東坡。實際上他離我們很遠,但感覺又離我們很近,似乎每個人都能在他那里討一勺維生素。他豪放起來可以“老夫聊發少年狂”,去射天狼;他曠達起來可以不怕,“也無風雨也無晴”;他通達起來可以攬“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他堅韌起來,雖“人生如逆旅”,他亦是行人;他調侃起來,三十年前,自詡風流;他風雅起來,“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他風情起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他憂愁起來也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他悲涼起來敢問“君門深九重”“也擬哭途窮”;他纏綿起來,“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他用起情來,可以哭訴“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他自嘲起來也不留情面,“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他向往起自在來,“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他超然起來,“此心安處是吾鄉”“詩酒趁年華”;他寧靜下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這樣的他,可以說是一人千面,可他又可以瀟灑地做到千面一人。而那個純粹到極致的蘇東坡,長嘯聲中,任江上之清風拂面,憑山間之明月垂青。而他羽扇綸巾、竹杖芒鞋徐徐地走在蘇堤上,再無風雨再無晴。
就這么驚鴻一瞥地和三位大詩人、大文豪匆匆一遇。他們不經意間流露出的絕世才華,正如滔滔江水奔涌不息。他們隨意揮灑的至純、至性、至美的神韻,如皓月當空,光耀千秋。他們確實是敞開胸懷、擁抱天下了,進而達到文士從“憋得慌”到收放自如的巔峰。
上天降下這些綿延不絕、跌宕起伏的至高峰,就是讓他們共同架構起中華文脈,孕育出中華文明,進而哺育泱泱中華民族。今天的我們,先天擁有鐫刻著厚重文化密碼的基因,而且,在擁有這座巨大寶藏的同時,還擁有了神奇的解碼人生。這是何其幸運啊!借用太史公的一句話自勉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還是趕快回來吧,在這些圣哲文豪面前,我不是“憋得慌”,而是“壓得慌”。他們與日月同輝,而我只能懷著崇敬之心,遠遠地看著他們,一點一點地追尋著他們的足跡。幸運的是,他們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才使我們有跡可循、有樣可學、有標可對。實在是忍不住,再重復引用一下我那怪誕的想法:他們滿懷天下、滿腦思想、滿腹情懷、滿身風骨、滿手文章,因此他們提筆天成;他們才華橫溢、不吐不快,要不他們“憋得慌”。這下感覺舒服多了,否則我“憋得慌”。
接下來講講我的“憋得慌”吧。雖然和上面所述不可同日而語,存在云泥之別,但他獨屬于我。為此,我為他留了一點兒空間,以便接下來往里裝入一些關于他的敘事。
回首望去,我好像天生就擁有“招憋”體質。很有意思,簡單說幾件事情。我出身理學學士,執著于據理深究,把自己由一枚專業白菜培養成了專家大拿。再往前走,一頭便撞到了天花板上,“憋”在那好幾年。后來加持了工學博士學位,才沖破了這第一層天花板。站上管理維度后,也曾掙扎在百變糾纏中,經歷過各種捶打、磨煉,漸漸體悟出了一些真諦。隨后,慢慢擁有了一點點從容姿態,進而給貧瘠的心田注入了一絲絲美感。由此漸入佳境,竟修煉出了《文化型企業“道”與“術”》。之后,在第二層天花板處摸索了好幾年,才又艱難地開辟了新賽道。攜帶著文學詩人、作家的力量,跌跌撞撞地突破出來,走上了文學之路。沿著路的方向一眼望去,前方巨峰林立、星空璀璨。嗯,這回沒人再賜我天花板了吧。雖然這層壓力沒了,但道依然阻且長。中間的闖關經歷,讓我清醒地意識到,“憋得慌”的常態化,其實才剛剛開始。
我與詩詞的緣起,是那株長在牛糞上的格桑花。這故事在拙文《鮮花插在牛糞上》有詳細描述。而真正動筆的原因,則是寫書法要有內容可寫。與此同時,又衍生出一個小小夢想:既然想走文學道路,那就從“搬磚和泥”干起,一磚一瓦向重樓。為此,我還填了一首《臨江仙·自嘲一》記錄下了當時的心境:
浮云輕漫神恬淡,凌峰傲海曾經。讀書問學月暉輕,初心華發,仗筆寫心聲。
情吟韻律言無束,遣懷隨性冰清。夢中醉里展旗旌,之乎者也,笑統萬千兵。
紙上談兵相對容易,真刀真槍拼的是實力。志也立了,牛也吹了,相繼的苦也就到了。一是功底淺薄,補課之苦。拜過各路教學神仙,看了各種文學、歷史典籍,背了千百首詩與詞,一通惡補,算是打下了一些基礎。二是內外兼修,美感之苦。詩詞講究情真、詞美、意深,這就要求詩人要有一個詩化的靈魂,能化情、化景、化世界;還要求詩人要有一顆敏感的心,能感受、感悟外在纖毫的情景變動,從而引發敏感的心境觸動,進而迸發詩化的靈魂波動。客觀上講,這些應該納入詩詞天賦的范疇。顯然,我天賦一般,好在我足夠努力且韌勁尚可,因此也就堅持了下來,而且已經養成一種習慣—“憋詩”的習慣。
因為懂些格律又不時萌發點詩情,所以經常舞弄些文墨。過程中那“憋得慌”的感受卻是越來越強烈了。不寫詩的時候,對周邊的人事和物事,看到了也就過去了。寫詩后,總忍不住瞎琢磨其背后的些許韻味,并且想寫出來。即便一時按捺下去,還會不時浮現出來,直到拿起筆,讓其從筆端流淌出來,才算過去這一關。這是我的“憋得慌”其一。
在詩詞創作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旦你進入創作狀態,不達成滿意效果而告一段落,根本停不下來。意境構建、辭藻潤色、邏輯梳理、情感表達、文氣表現等,統統縈繞于懷、翻江倒海。大腦高速運轉超三千轉,夜月照我床,輾轉到天明。為了不影響領導(特指夫人)休息,我只能把身體探出床外,雙手拿著手機在床側下方,一字一詞地推啊敲的。剛剛完成一點兒,放下手機躺好,一會兒又翻身再來,如此反復,直至滿意為止。經常是過了三更到五更,詞句已是百千更!這是我的“憋得慌”其二,也是最強烈、最執著、最具魅力的。而我那所謂的詩意、詩情,也都翩翩而出,融進那片微光,溫暖滋潤著那顆純凈的詩心。只是這樣的狀態太耗神了,以至于現在晚上過了九點,我一般不敢再去觸碰那敏感的神經了。
詩詞創作很難,出好作品更難。《尚書》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陸機《文賦》有言:“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載著言志、緣情之道,雖意境深遠,但體量精練,所以,平凡如我,也能在這片海洋里摸摸魚,以“憋”詩為自娛了。令人意想不到和感到欣慰的是,愣是憋出了《心岳集》《心岳詞》兩本詩集來。
由于《心岳詞》是自序,所以我就寫了一篇散文《我的興觀》作序。索性便以這篇文章為契機,又走上了文章寫作之路,開啟了我的詩文之旅。雖然步履蹣跚,卻也算且行且平穩吧。原因主要有:一是我的人生體悟還算豐富,有一定的內容輸出;二是多年跨界、跨學科的學習,我的底蘊還算深厚,有一定的靈感捕捉能力;三是長期的詩詞創作,使我具備了一定的思想表達、情意抒發、韻律協調等文氣基礎。因此,在文章寫作方面也還算順利,把藏在或憋在腹中的體悟素材,自以為是地當作一團錦繡而宣泄于筆端、縱情于紙上。因此,我就這樣一路走來了。
我曾經簡單粗暴地認為,文人的多愁善感有一些偽裝成分。因為我本身性格內斂,很少動情,更少被文學作品所代入。在閱讀過程中,我更多是一個理性旁觀者的角色。然而,等我真的走上了文學創作苦旅之后,才發現自己是多么無知、多么貧乏。因為在與文字同行、相依相伴中,其所凝聚而生的澎湃激情,讓我震撼、讓我動容、讓我情不自禁。其中有兩次最為讓我印象深刻。
因著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我傾情投入其中,在汲取滋養的過程中,漸漸體會到,農耕文化是一種關鍵的文學素養。而農村的成長經歷,使我對此理解得更加深刻一些,為此我寫了一篇散文《農耕為我種下詩的根》。其中一個章節寫到主人公回故鄉,站在拆遷的老宅空地上,感懷落淚。就在那一刻,我心一陣悸動,眼淚奪眶而出。放下手中筆,我平靜了好一會兒,又與領導交流匯報了一下所思所想,才慢慢平復下來。我知道,這是有感而發,把積淀在心靈深處濃濃的鄉愁宣泄而出。我也知道,這份鄉愁不僅藏得深,而且憋得久。
另一次是在創作散文詩《美麗的南開我的家》時,情感一路抒發下來,流暢地完成了創作。讀了幾遍,自我感覺良好,便發到美篇并配樂。背景音樂旋律是《美麗的草原我的家》,當我順著旋律流連在詩句中時,感情的漣漪在波動。當“回得來的母校,回不去的學校”進入眼中、闖入心中時,我的情感堤壩再次決堤,兩行熱淚傾瀉而下,沖進情感洪流。強烈的傾訴感驅使我,把那份留戀和惆悵傾吐給了一位文學知音,在她娓娓道來的共情中,我才慢慢平復下來。我知道,這份母校情懷,也是藏得深、憋得久。
這兩次情感與文學的碰撞爆發,讓我對文學的理解邁上一個臺階。這是我的“憋得慌”其三。隨著這若干“憋得慌”的釋放和疏解,我慢慢地發現,我的心靈變得愈加敏感,我的情感變得愈加飽滿,我的文氣變得愈加明顯。就算是獨上層樓,至少不用再強說愁了。
幸得自己被碼字功夫所武裝,給心靈打開了一扇窗,能夠時常地把柔軟之地的一絲波動宣泄于筆端,鋪陳于紙上,袒露于紅塵。慢慢地,竟也成了習慣,且和我的“憋得慌”友好友愛、知音知己。一路走來,我對“寫”的思考,一直在反思迭代中。我曾一度執拗地認為,詩言志、詩緣情,詩為自己而寫,也確實在創作中抒發了自我、愉悅了自我、升華了自我。漸漸地,我感覺,小我的容量有限,情感偏輕,世界太小,也就漸漸地理解了文以載道的深刻性。這時,我的眼里看到了大千世界,鼻中嗅到了磅礴氣息,耳中聽到了山呼海嘯,從此我的心在漸漸長大,似乎沒有極限的感覺。此時,手中的筆開始變得莊重、凝重、厚重,胸中開始凝聚萬千氣象,也因此更增加了“憋得慌”的持重感。再接下來,隨著觀察的深入、思想的深刻、體悟的深遠,與緣于心、發乎情、近于道的悸動,時常偶遇。既然遇到,就不能走過、路過還錯過,所以筆端的靶向由此開始走向專一、走向專心、走向專情。再后來呢?不知道,就像如何來的一樣,再那樣如何地走下去吧。
寫
自咿呀始" 便學會說
學了幾個字" 看了幾本書
卻不會寫
爬了坡" 過了坎
知道了曲折
摔了跤" 受了傷
知道了坎坷
經過風" 走過雨
知道了滄桑
語過花" 對過月
體會了美好
傷過心" 流過淚
品味了痛苦
執子手" 與子行
找到了方向
微笑自此" 成為面容的常客
堅毅在此" 刻下帥氣的棱角
愛心于此" 扎下永固的營盤
不知不覺
靈魂中萌芽出" 悟的幼苗
腦海里波動起nbsp; 思的浪花
心田間蕩漾著" 愛的微瀾
受感染了嗎
手中的筆
在不停地躍動
你是想教我寫
是想讓我寫
隨著你的躍動
我的思潮亦在涌動
會不會寫
已然不重要
因何而寫
有何可寫
為誰而寫
至關重要
想寫" 一定有激情
可寫" 一定有內容
寫誰" 一定有緣分
如此" 筆已入心
就讓我們一起
寫著
愛著
活著……
其實,還有一個點也很重要,涉及傳播、傳承、傳揚。高雅的圣賢叫立言,傳統的文人叫立說,凡夫俗子的我就叫嘚瑟。因此,才有了《詩經》《樂府詩集》,有了曲水流觴的《蘭亭集》,有了王維的《輞川集》等。而我“憋得慌”的點就是嘚瑟。每每有新作品問世,我會各種嘚瑟求點贊。有網上發布、發朋友圈,更有拉著三五知己求分享。再往前走,隨著作品數量和質量的提升和積累,便滿懷期待地努力去期刊發表、結集出版。再高遠點,又開始希望作品能有一點兒影響力,自身能有一些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了。能否做到?努力去做就好了,至少可以快樂自己、豐富生活、美麗人生。
行文至此,一絲輕松、舒暢的感覺順著筆端涓涓流出,釋懷了、解壓了。看著這些剛剛誕生的文字,想象著她們孕育出的獨立靈魂,牽手初心、一路同行,繾綣于美妙的心境,徜徉于美麗的意境。即便無果,也算是了卻了一樁小心愿,積累了一個小逗號。而后,繼續于山前水后、案頭筆下,流連在句讀之間,雕琢一顆文心,修養一個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