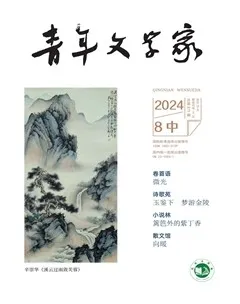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明清俗曲是指明清時期出現的一種文學與音樂、表演相結合的藝術形式。作為明、清兩個時代特有的音樂文化現象,明清俗曲是在各地民歌基礎上,吸收諸多文化因素發展、興盛起來的一種古代歌曲形式,主要流行于內地。作為內地特有的一種音樂藝術形式,處于邊陲的云南地區本是沒有的。但隨著歷史上中央政府對云南統治的逐漸加強,以及明清時期大規模內地移民遷徙入滇,再加上政府對于儒學教育的大力推行和“改土歸流”等政策的實施,云南的政治、經濟、文化得以快速發展,這也為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發展培育了良好的藝術土壤。在孫明躍老師所著的《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與衍變》一書中,其首次運用傳播學理論,就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發展過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觀照,分別對明清俗曲在云南傳播的歷史文化背景、自然傳播、制度傳播、傳播特點、傳播效用和衍變等六個方面展開了詳盡的論證和研究,并就明清俗曲在云南傳播衍變的四種模式和其形成的原因特點進行了綜合分析。
一、明清俗曲在云南傳播的歷史文化背景及傳播形式
明清時期,云南城鎮與經濟文化發展顯著。明初,朱元璋廢除元代行省制,設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并實行移民入滇和儒學教化,以期實現“以夏變夷”。清朝統一云南后,改明代三司為云南省,設巡撫和云貴總督,沿用明代移民入滇和儒學教化方針,尤其雍正時期“改土歸流”政策使更多漢族移民入滇。漢族移民和漢文化的推入促使云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快速發展,與內地文化趨同。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萌芽發展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崛起,內地明清俗曲隨移民傳入云南,并深刻影響本地說唱、戲曲和器樂音樂文化的發展。正如馮光鈺先生在《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播演變》中所說:“一切傳統音樂都是傳播的音樂,在傳播中不斷演變,又在演變中不斷發展。可以說,沒有傳播及演變就沒有音樂文化的發展,不再傳播演變的音樂文化,將是僵滯的音樂文化。”
明清俗曲的傳播與衍變主要包括自然傳播和制度傳播。作者在書中詳細論述了這兩種形式,此為本書的重要內容。自然傳播是指無意識、無目的的文化因素或特色傳播。內地移民將俗曲帶到云南,并將其傳承傳播。移民是俗曲在云南的主要傳播者和欣賞者,也是主要媒介。戰爭、軍屯、民屯、商屯和文人傳播等屬于自然傳播,無智力或技術媒介介入,非政府機構組織。明清移民入滇促進了內地與云南文化的交融,漢人成為云南主體,夷漢雜居成為主要聚居形式,俗曲便由此融入本土文化,不同傳播群體和類型的相互聯系與滲透,構建了俗曲在云南的傳播網絡,促進了其傳播和發展。
“禮”作為中國禮制文化的核心,其外顯形式就是禮樂制度,而這一制度具有教化功能。當禮制俗化形成民俗,禮樂又同民間風俗對應,五禮(軍、嘉、兇、吉、賓)在鄉村禮俗中表現為結婚、喪葬、祭祀、宴客等,這都是禮制俗化的具體體現。五禮中音樂成為民俗用樂范本,鼓吹樂為代表。云南明清時期的俗曲中,鼓吹樂便證明了官方禮制用樂與民間禮俗用樂已經融為一體,通過樂籍制度相互溝通。樂籍制度是古代對專業樂人的管理制度,服務于官方,負責承載民間禮俗音樂的表演。雖在雍正時期該制度被廢除,但禮樂制度仍有所保留,被除籍的樂人將官方禮樂傳播至民間,使得禮俗之間的互通性更為明顯,明清俗曲在云南得以迅速傳播和發展。
二、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特點
明清俗曲作為一種興盛于明清時期且具有承前啟后性質的特定的藝術形式,興起于北方,蔓延至南方,在各個地區廣為流傳。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中央政府為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動了內地移民和漢文化的滲入,使得明清俗曲得以隨內地移民的遷徙而在云南生根發芽。作者就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特點進行了悉心歸納,將其作三點進行概論。
首先,明清俗曲作為一種移植性傳播文化,具有“移民到哪兒,‘俗曲’就流傳至哪里”(孫明躍《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與衍變》)的特點。明代移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云南腹地的城市和壩區,這也是漢民族的主要聚居區,俗曲的流傳也主要集中于此,也是俗曲最為發達的區域,其中包括以俗曲為唱腔的花燈、揚琴、蓮花落、漁鼓等。相較于漢民族聚居較多的地方,那些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區,明朝時期還是實行土司制度,俗曲成了服務土司階層的一種娛樂手段,對于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而言則很少有機會接觸。對比明朝的移民模式,主要是以服從中央政府統治的強制性而言,清朝時期的移民就偏于自發性。在“改土歸流”和移民墾荒政策的實施下,大規模移民涌入云南地區,其中就包括與云南接壤的蜀地,以及江西、湖廣、山陜、江南的移民。由此,內地的音樂文化也深刻影響了云南本地音樂的發展,如云南的滇劇、花燈、曲藝等深受四川音樂的影響;湖廣移民的襄陽腔、秦晉移民的秦腔、江南移民的昆腔等,這些通過移民而來的不同地方戲劇,在同本土音樂的交融中不斷摩擦出新的火花,為云南本土戲劇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通過對云南地域文化的特征性進行文化圈的分層:一是漢族移民聚居區,二是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區,三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聚居區。不同的聚居區,明清俗曲的分布與傳播效應也有所不同。根據分層來看,漢族移民聚居區的明清俗曲分布較為廣闊,即現在的昆明、曲靖、昭通、保山等地,最有代表性的屬云南花燈,該區域的花燈唱腔多以明清俗曲為主,所存的明清俗曲曲牌最多、曲調最為古老,如【打棗竿】【掛枝兒】【哭皇天】【寄生草】【紅繡鞋】等。再到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區,即現在的麗江市、文山州、紅河州,該區域漢族依然為主體民族,但麗江的納西族、文山的壯族,以及紅河的哈尼族和彝族依然數量較多,因此該區域的戲曲音樂也多與當地少數民族音樂互通交融,像彝漢雜居的建水、蒙自、彌勒等地的花燈唱腔音樂就具有明顯的彝漢風格,曲牌與明清俗曲有關的就有【打草歌】(即【打棗竿】)、【弦蘇調】(即【茉莉花】)、【合婚調】(即【孟姜女調】)等都融入了彝族音樂元素,尤其是滇南彝族的“四大腔”音樂。而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即現在的普洱市、西雙版納州、德宏州等,這些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是大于漢族人口的,俗曲音樂在當地屬于小眾,但因漢族也非極少數,俗曲音樂在不同程度也同周邊民族音樂有融合交匯的現象,如以傣族和景頗族為主的德宏州,其芒市的五岔路鄉作為漢族聚居地,也有同明清俗曲有所關聯的曲牌,包括【一杯酒】【采茶調】【散花調】等。
最后,明清俗曲的“俗”最早源于“雅”,而脫離“雅”之后的“俗”,就成了民間的自然選擇。流行于內地的明清俗曲,其發展離不開文人雅士,在他們的推動下,那些民間音樂成了一種“雅化”代表,且總有些文人的矯揉造作之氣。尤其到了后期,脫離生活和群眾的明清俗曲,最終也落得被民間拋棄的下場。作者以云南傳統花燈劇為例,雖還存有部分較為“雅化”的曲牌,但其在唱詞上也都有變“俗”,曲也變“簡”,如流傳于元謀、祿豐、紅河等地的【打棗竿】,被簡化為單樂段或多樂段結構,以分節歌形式演唱,歌詞變得通俗易懂。在這場雅衰俗勝、由雅變衰的過程中,作者將其主要原因歸于文人雅士群體的逐漸消失和樂籍制度的廢除,而傳播者和接受者的消亡,使得雅化俗曲曲牌的整體衰落也就成了必然。
三、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效用
明清俗曲以其鮮活性和真摯性反映著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不僅為眾多文人所看好,也為市井所傳唱,成為當時城市生活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在當時政策的推行下,云南地區對于中原文化具有強烈認同感,明清俗曲在隨內地移民入滇的過程中,不僅以單曲或小唱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在此基礎上還通過融合云南本地或其他少數民族文化藝術,促進了本土戲曲戲劇的發展。今時今日,內地傳入至云南的明清俗曲都還保存在云南的傳統音樂之中,包括云南花燈、云南揚琴、云南洞經音樂、云南各地的鼓吹樂和云南民歌等。
在書中,作者就云南花燈、云南揚琴、云南《洞經音樂》中的明清俗曲都做了舉例論證,印證其“活化石”的意義。與此同時,漢族移民及漢文化的不斷擴寬,使得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與演變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在壯大自己的同時,也推動了云南多民族音樂藝術的發展。像云南漢族的曲藝藝術有的就是在明清俗曲基礎上發展的,如云南揚琴、云南花燈等。云南揚琴在后來的發展中,又不斷吸收各類曲藝的養分中逐漸形成了新的戲曲形式,即云南曲劇;而云南花燈在廣為流傳的過程中也深受云南本地少數民族的喜愛,如紅河彝族地區的花燈,在演唱中使用彝語還有彝族特有的演唱技巧,正因如此,該地區的花燈也被當地人稱為彝族花燈。
不過,明清俗曲雖是一種娛樂性的產物,但其作為明清時期統治者推行的邊疆治理政策下移民入滇所帶來的“移民文化”,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從明清中央政府的政治角度來看,以文化藝術形式去傳播儒家文化是再適合不過的了。云南揚琴中的唱腔就多以曲牌連綴為主,板腔體為輔,唱腔分為書腔類和唱曲類:書腔類的劇目多以佛道的勸善為主要內容,宣揚善惡有報的因果報應來教育人們;唱曲類所用聲腔基本為明清俗曲,劇目多以傳播漢族歷史文化和儒家道德倫理為主,具有“高臺教化”的功能。云南花燈藝術中也體現了許多“忠孝節義”的主題,那些內地而來的文人仕宦來到云南后,接受政府“以夏變夷”的政治思想和肩負邊疆“教化”功能的責任,使他們在娛樂中更傾向于“寓教于樂”。而云南花燈和揚琴的流傳范圍不止于達官顯貴、文人雅士等,同時也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其次還有具有移風易俗、敦品勵行的云南《洞經音樂》和有著“忠孝節義”為宗旨的云南儺戲,在潛移默化之中都深受漢文化影響,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就如陳獨秀先生在《論戲曲》中所說的:“戲園者,實普天下之大學堂也;優伶者,是普天下之大教師也。”在歌舞演故事的過程中,明清俗曲身上所帶有的“政治教化”性,也得以在云南地區廣為流傳滲透。
四、明清俗曲在云南的衍變模式
在對明清俗曲在云南發展過程的詳盡敘述中,作者總結出了明清俗曲在云南傳播衍變的四種模式:第一種模式為漢族聚居區,傳播者和接受者是移民;第二種模式為漢族聚居區和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區,傳播者和接受者為移民與少數民族;第三種模式為土司府統治地區(包括“改土歸流”以后依然實行土司府統治的地區),傳播者為少量內地樂人和少數民族樂人,接受者為土司府上層貴族;第四種模式為“改土歸流”后的土司府統治地區,傳播者為移民和少數民族樂人,接受者為移民和少數民族。從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來看,明清時期漢族移民及其后裔作為傳播俗曲的主體、載體和接受群體,對明清俗曲在云南傳播和衍變產生了重要作用,但就樂籍制度在內的國家禮樂制度則在其中更為關鍵,畢竟在國家政權力量所控制的地區才能發揮由政府主導的政策實施,漢族移民也能得以順利去往云南并將俗樂進行傳播。因此,作者將明清俗曲在云南的自然傳播和制度傳播進行了一個主體和關鍵的劃分,即以自然傳播為主體、制度傳播為關鍵。
作者在對明清俗曲是如何在云南進行傳播和衍變的研究中,首次運用傳播學理論,在善用馮光鈺等人的自然傳播理論的基礎上,又引入項陽等人的樂籍制度傳播理論,就文化傳播所處的環境、主體、客體等方面,對明清俗曲在云南的發展過程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觀照,同時站在歷史的角度對其傳播衍變過程進行了具體分析,這對擴展明清俗曲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具有積極意義。但就本書的撰寫來看,還存在一些值得完善的地方:第一,有關明清俗曲的界定可以再明晰一些;第二,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和衍變過程中的具體呈現,可以再多一些田野材料作為例證依據;第三,作者針對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與衍變,主要傾向于歷時性研究,若是在此基礎上多一些共時性研究,那么研究內容也將更為飽滿。總的來說,瑕不掩瑜,孫明躍老師所著的《明清俗曲在云南的傳播與衍變》的價值性不言而喻,有興趣的學界益友不妨一睹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