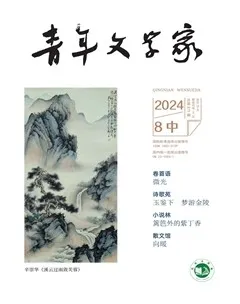權力迷宮之下自我意識的湮滅

張煒在《艾約堡秘史》《去老萬玉家》中通過獨特的視角深刻審視著時代變遷下紛繁復雜的現實圖景,鋒芒所及直指問題根源。本文試圖借助米歇爾·福柯關于規訓、權力等敘事理論,解讀張煒小說中強權者如何使用權力并導致人性異化的過程,表現作家對于生命主體意識的關注及對商業功利主義的批判立場,理解其文化建構的終極關懷與超越精神。
一、權力世界的構設
“權力”是當代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即無論在何種時空維度之中,當人與人發生接觸,就會產生一定的“力的關系”,一種存在于人與人之間難以擺脫的關系,其中既有政治上、經濟上的顯在關系,也有肉體規訓上的隱形關系。從這種視角出發,我們就可以克服許多有關張煒的《艾約堡秘史》《與老萬玉家》中權力敘事在特定時期書寫的理解障礙,這將為我們解讀小說中特定的人物權力書寫緣由及其曲折發展提供廣闊視野。在小說《艾約堡秘史》中,淳于寶冊對這位不同一般的女子—蛹兒采取的是“變相囚禁”,讓她掌管私邸的全部內務,貪婪地向蛹兒索取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價值。同時,他又對民俗學家歐駝蘭生發強烈的掌控欲望趨向,認為占領了磯灘角海灣實際上就是征服了歐駝蘭。這種錯誤的認知使他與歐駝蘭之間的距離愈加疏遠淺淡。歐駝蘭身上所散發著的純文人的高尚品質,正是他所想擁有的。淳于寶冊并不知曉自己嗜讀的文人理想在無形驅使之中已悄然演變為權力欲望,但他的權力掌控范圍不僅局限于此,他的權力威懾同時存在于貍金集團,他早已將野蠻血腥積累的資本轉化為商品時代眾多領域的投資,且子公司已經開到海外。作為淳于寶冊親自選定的貍金“前臺的角色”,總經理老肚帶是最能心領神會掌舵人意圖的。老肚帶從來隨叫隨到,唯唯諾諾、唯命是從,因為只有他知道淳于寶冊真正的手段,了然于心對方懶洋洋的假象下,有一雙洞若觀火的眼睛和霹靂性格。淳于寶冊對老肚帶道:“我只問結果不問過程,一伸手你就得把我要的東西放在這里!”“我孫子什么辦法都有!”諸如這樣的話語,正是其在權力之下肆無忌憚發出的命令。他為瓦解磯灘角,與老肚帶紅臉白臉,分工合作,真正的動手其實就在等他的一聲令下,對老肚帶“我就要沖散他這個小土丘”的叫囂,才表達了他真實的欲望。同時,這種對權力的展現在張煒最新長篇力作《去老萬玉家》中更是顯著,在沙堡島這座孤島之上,“說謊、搶劫、殺戮、欲望”交織成一首不停歇的交響曲,這是老萬玉所編織的黑暗樂章,也是她掌控這個沙堡島的真實寫照。從冷霖渡到小棉玉,從桀驁不馴的匪首到各占山頭的“司令”和“將軍”,他們都對萬玉大公俯首帖耳。小棉玉對舒莞屏說出其中所規訓的層級關系,“那些‘將軍’‘司令’不過是個名號而已,就連勢力最大的朱砂滾子萬東也不足千人。他們相互火并,再加上官軍追剿,要獨撐難上加難。萬玉大公先是把他們收編,然后再委派副將或都統,加上眼線眾多,巡督往來,要想反叛就不那么容易了”。這一切正是規訓權力運作之下的完美典范,是一種精神對精神、權力對權力的閉鎖統領。
“全景敞視主義”作為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的術語,其核心靈感源于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監獄”概念。該設計以其精妙而溫和的手法,將不同的個體編織進一個無形的規訓網絡,使個體在各自特定位置上發揮作用,共同推動整體機制的高效運轉。這一概念在張煒的《艾約堡秘史》與《去老萬玉家》兩部作品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在《艾約堡秘史》中,淳于寶冊為自己構建的宏大住處艾約堡,其結構異常,實質上成了一個失序的封閉式亂堡。艾約堡作為一個資本權力的象征,蘊藏著貍金集團的力量,并將堡壘內的眾人圍困于一個復雜龐大且被掏空的“山洞監獄”之中。淳于寶冊擁有至高的話語權,所有人都對他唯命是從、俯首稱臣。同樣,在《去老萬玉家》中,老萬玉所造的無枷囚島也展現出了類似的權力結構。通過“孤島”意象的創設,沙堡島呈現為一個封閉的時空結構,萬玉大公的權力盤踞于整個孤島之中,對沙堡島的權力控制無一例外地展現出權力在特定空間維度之內對人的干預、折磨、強制。這種全景敞視的監視和規訓機制,不僅作用于個體的肉體,更深入地滲透到個體的靈魂與精神之中。正如法國哲學家拉美特利在《人是機器》中所提出的“馴順性”理念,他認為肉體是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的,是政治的玩偶,是權力所能擺布的微縮模型。在《艾約堡秘史》和《去老萬玉家》中,淳于寶冊和老萬玉正是這股統治力量的代表,他們控制的不僅僅是肉體,更是肉體之下的靈魂與精神。這種權力的構設與書寫,實際上是對欲望社會之下社會現象和人性深層的投影與探秘。在權力的肆意揮霍之下,被統治者的馴服將表現在哪些方面,統治者是否能夠找到自己心靈最初的方向與歸途,始終是張煒作品中持續思索與探討的主題。
二、權力之下人性的異化
個體在權力結構的框架內被限制和制約,這種限制和制約來自權力的強制性和權威性,使得其行動、決策或表達受到權力中心的顯著影響,從而難以自由地實現其意愿或目標。張煒在小說《艾約堡秘史》中用蛹兒的視角切入,深刻剖析權力關系中個體生存體驗,通過對個體身體與精神層面的深入細致刻畫,詮釋了權力關系之下的個體身體與精神上的規訓,顯現出權力異化的現象。堡內運轉紊亂、氣氛混濁,這與蛹兒最初所期待的理想環境背道而馳。然而,受淳于寶冊影響,蛹兒接受了堡內的一種古老處罰方式。在一次巡查中,她發現通風問題未解決,由領班鎖扣領責,其不滿行為導致蛹兒對其實施了當眾解褲打屁股的處罰。面對這一局面,鎖扣顯得驚愕、無奈且充滿憤恨,但她只能接受這一處罰,身體姿態透露出深深的屈辱感,仿佛再也無法挺直腰桿兒,更不愿提起被解開的褲子。這一現象揭示了權力結構中一種微妙的轉變:地位較低的人,無論是被壓迫者還是施權者,在面對更低地位的人時,也可能在不經意間成為權力的執行者,這種權力關系的轉化不僅體現了權力的復雜性和相對性,也反映了在特定情境中,權力驅使之下所帶來的人性異化的悲劇。在未被個體主觀意識所察覺的深處,蛹兒精神與身體內的一股力量正在悄然積聚。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處于堡壘內部受周身環境的影響,這種力量逐漸從無形的潛在狀態轉化為有形的具體現實表現形式被釋放出來,使原本的個體在不知不覺中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施權者。這種演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一系列內在與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逐步塑造出一個這樣復雜而微妙的身份角色。蛹兒從苦惱于無法融入—設法進入艾約堡秩序—整治亂堡的過程,活脫脫是當代版的東宮皇后憑借圣旨立威建序。同時,在堡壘的封閉空間環境之中,蛹兒自我主體認知意識正在慢慢喪失,憑借曾經傷害過自己的兩位男人的經驗,她最初秉持著的理念是不再淪為男性的附庸,不再屈服于他們的統治之下。然而,在踏入艾約堡這座牢籠之后,在與淳于寶冊這一虛偽的統領者接觸并同化之中,她的行為、思想、心理狀態正不自知地與她最初的理念相背離,呈現出一種逆向異化的發展趨勢。她視淳于寶冊為主人,在他面前,她卑微到塵埃。蛹兒與淳于寶冊相處三年之中,已經達到“共命”狀態。她從不主動要求,察言觀色,善解人意,輕言款語,周到逢迎,骨子里的不對等狀態,從淳于寶冊根據其肉欲特征對“蛹兒”的命名,即可見端倪。小說從頭到尾,未出現蛹兒的本名,但蛹兒對此并不自知,只憑臣服心理與泛濫的母性做著主。在小說的敘事脈絡中,這種人性異化的趨勢逐漸顯露,其內在的邏輯力量不僅構成了故事情節的驅動力,還深刻地影響了對權力本質的進一步探究。
人性異化在《去老萬玉家》中的小棉玉身上更多地體現了矛盾與掙扎。她是被國師冷霖渡從亂葬崗撿回的棄女,被冷霖渡喚為“毛猴小玉”。冷霖渡的情緒極不穩定,人面獸心,在小棉玉幼年時就對其進行了身體上的施虐與精神上的摧殘,每每折磨小棉玉至深夜凌晨。冷霖渡在其婚禮上眼含淚花,虛偽的面孔之下是其骯臟腐臭的靈魂。小棉玉從小被視為玩物,寄人籬下于沙堡島這所權力的牢籠中,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內心卻蘊藏著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在給出征兵士進行宣講時,她嬌弱矮小的身軀,身披紅里黑面的斗篷,嗓音洪亮,震耳欲聾,她宣揚著萬玉大公的崇高與卓越,將其尊為守護神般的存在。然而,當舒莞屏因不明真相而對她表示欽佩與夸獎時,她卻流露出一種復雜的情感。這種情感既包含了被愛戀者所認可的羞澀,又蘊含了對自身與萬玉大公同流合污的深深懊悔。這種心理狀態展現了她內心的矛盾與沖突,一方面她沉浸于對萬玉大公的擁護與信仰中,另一方面她又深知萬玉大公的行為并非完全正義,這也使得小棉玉這一形象更加立體與真實,為我們探討在權力驅使之下被壓迫者心理異化與矛盾提供了絕佳典型形象案例。
在深入剖析之下,我們不難發現,權力禁錮之下社會的物質秩序與畸形心理共同構成了張煒權力世界最為基本的底色,他深切關注到現代化進程中的權力變動,傳達出對社會權力濫用的強烈關注與深切憂思,他通過描述人們在權力面前的無助與無力,揭示了權力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從而致使人的主體意識的喪失。張煒對人生存處境的關注,彰顯出知識分子獨特的人文精神,這不僅是對社會的關切和擔憂,更是對人性、文化和歷史的深刻理解和思考。
三、馴順之下的審視
作為一位在20世紀80年代嶄露頭角的作家,張煒的文學創作深受當時啟蒙思潮的塑造與引導,其作品顯著地體現出對傳統社會陰暗面的批判精神。同時,他還深受齊魯文化,尤其是儒教文明的浸潤,這種文化滋養不自覺地融入了他的文學創作中,進而塑造了他獨特的精神風貌。在張煒的創作實踐中,其道德精神展現為一種深刻的融合性。他通過批判傳統社會的啟蒙理性,以及審視商業社會中物質主義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兩者的片面性。這種批判性視角不僅是對現有道德理性與啟蒙理性單一維度的反思,更是試圖在作品中將道德理性與權力觀念進行深入的辯證考量。
《艾約堡秘史》在小說謀篇布局與視角上,對橫掃一切的貍金帝國的締造者、裸商淳于寶冊精神,以及他靈魂深處的追求、苦惱、迷失進行探索,塑造出了一位實際權力的主導者。小說透過對淳于寶冊的財富膨脹帶來的自負、欲望驅動下的沉睡、迷惘中的自我掙扎,以及他內心不為人知的無奈與不甘的細膩描繪,展現了這位商業巨頭在無法無天、肆意妄為的行為背后,所隱藏的無法自我明確定位,無法自我救贖的深刻心理困境。而這,正是源于作者心底對歷史發展的非理性的沉痛體認,對主體愿望與客觀現實之間不可避免矛盾的洞察,以及對個體生命在無法自我掌控的境遇下所展現出的悲劇性本質的深切同情。在老萬玉對沙堡島的權力統治之下,主體意識的喪失與馴順現象成為規訓制度的必然產物,然而,亦激發了一種更加深刻的反思:在持續的、強制性的壓力和限制之下,個體如何能夠保持甚至發展出更為深刻的覺醒意識,愈加凸顯個人意志獨立性的高尚與珍貴。
當我們聚焦于張煒筆下對權力規訓的細致審視時,不難發現,盡管主體意識的逐漸消解與個體馴順成為權力規訓機制下的必然邏輯,但更為引人深思的是,個體如何在這樣的規訓框架內認知并行使其本身所擁有的權利。在張煒對《艾約堡秘史》《去老萬玉家》等作品的文學探索中,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議題便是探討那些身處權力網絡中的個體,如何能夠超越并掙脫權力的桎梏,如何在權力的嚴密規訓下堅守并維護自身的主體意識。盡管在張煒的書寫中,這一議題并未獲得直接且明確的解答,但其所蘊含的深刻自我救贖的哲學思考卻尤為顯著。這種救贖并非簡單的逃避或反抗,而是對個體如何在權力關系中尋求自我、認知自我,進而超越由權力帶來的痛苦和束縛的深層次追問。
在《艾約堡秘史》與《去老萬玉家》這兩部小說中,作者張煒介入現實的強烈愿望得以展現,他通過對權力鏡像的書寫,探索權力與歷史、文化的復雜關系,并由此揭示權力文化對人生、人性產生的影響。通過這一獨特的敘事視角,張煒成功地將權力從單純的政治概念擴展至文化、社會乃至人性的多維度層面。小說中的權力書寫所彰顯的是張煒關注現實、正視現實的勇氣,以及思考社會生存現狀的精神,他不僅僅滿足于表面的批判,而是深入到權力運作的內在機制,剖析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和歷史脈絡。這種深度透視使得張煒的作品不僅僅具有文學價值,更具有重要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意義,對我們反觀所處的時代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