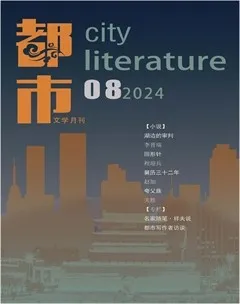木槿花自由綻放
1
我們家姐妹五個,沒有兄弟,大姐就成了家里最強壯的勞動力,她最早跟父母下田掙工分,跟著包產到戶,又得耕種十幾畝地。春天撒籽種豆,夏天收麥后種谷子、豆子、玉米和高梁,收了秋又得耕地種麥。冬天她也閑不下,織布、裁剪、蹬縫紉機,樣樣都干。可以說,這個家離了大姐根本就轉不開。
隨著年歲增長,我們幾個妹妹相繼跳出農門,只留下大姐陪伴父母。父母給出的理由是家里地里都離不開大姐,讀完小學認識幾個字不做睜眼瞎就行,到時招贅個男人,替娘家頂門壯戶、傳宗接代。起初大姐不肯,說姊妹好幾個,為啥獨獨留她?
不提這個還好,一提這話頭,就惹得父親嘆氣母親流淚。那晚,大姐在父母的輪番轟炸下,終于松了口。她抱著我的頭哭著說,四妮兒,爹娘說跟我是雙胞胎的兒子沒了,父母就把我當成了他,誰讓我命硬,克男孩兒,所以我得還債,還父母的債,還你那個沒活過一歲的哥哥的債。
大姐十九虛歲就結了婚,迫于當時的風俗,鄉親們說命硬的女子結婚,頭幾年是不能回家住的,所以父母就在山腳下尋了一間簡陋的土坯房給大姐安了家。待姊妹們相繼出門,大姐才搬回家住。農忙的時候,父母幫著大姐帶孩子做飯,她和姐夫在地里忙活,三代同堂,其樂融融。直到院墻內的兩株石榴樹,由盛到衰,再也結不出香甜的果子,直到外甥們也相繼成家生子,父母有了第四代,農家院的熱鬧才不知不覺開始慢慢歸人沉寂。
父母老了,還得承受三姐因病早逝的傷痛,不久之后,不知怎的,他們開始夜以繼日地折騰,還常常打狗攆雞。我就曾親眼見過由大姐親手孵化的一只紅尾巴大公雞被活生生打死了,大姐因此氣得發瘋,生平第一次跟父母大吵,雖然過后幾天每頓飯都照樣端給父母,但她始終不說一句話。
我知道那只大公雞,紅色的尾巴在陽光下閃爍著絢爛的光,它是大姐用偷偷攢了好久的雞蛋親手孵化出來的。大姐一共孵了十二只小雞,其中兩只公雞,十只母雞。兩只公雞中有一只在半大的時候掉進村西的水庫里淹死了,于是大姐對僅存的另一只公雞倍加愛護,它和其他小母雞們茁壯成長,很快成了一只健碩俊美的雞王。
大姐精心養育這只紅尾巴大公雞是有打算的,她說一個家哪能光養母雞?人分男女,物有雌雄。雞窩里已經夠陰盛陽衰的了,只有那只公雞像一個武士,領著十只母雞奔跑覓食,如一只鶴,帶領著母雞們飛翔。大姐說一看到那只雄赳赳氣昂昂的像帝王一樣神氣的大公雞,看著它在門前屋后的沙土上游來逛去,姿態悠閑,她就會心情愉悅,一天的勞累也會隨之拋到云外。
父母雖然糊涂,但也知道母雞能下蛋,所以他倆只對公雞有意見,認為這只公雞除了五更打鳴,就只會吃,還要耗費不少糧食。最主要的是,父母跟前一輩子沒個兒子,大姐養的那只大公雞戳中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痛,所以,他們覺得雄性的動物通通礙眼,豬圈里只有豐肥的母豬,羊圈里也只有能擠奶的母羊。大姐幾次無奈嘆息,說跟已經老糊涂的老兩口根本沒道理可講。
大公雞已經死掉了,面對混沌不清的父母,大姐只能把委屈摁了又摁、壓了又壓,她在電話里向我訴苦:四妮兒,姐得跟你倒倒怨氣,不然非得憋瘋。我在電話線這頭勸慰:說出來心里松泛些,要不我再給你買一只?
甭買了.爹娘老了,順著他們些吧。大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后掛了電話。
大姐時常對著十只母雞陷入回憶:想那一雙帶著傲慢、放肆,又煞有其事的小眼睛,四周逡巡一圈,確認自己的領地沒啥危險時,就會跳到樹杈或者墻頭上引吭高歌,它的歌聲很嘹亮,整個村莊的人都能聽到……大姐的兒女們都搬離了這個農家院,所以,她是把她親手孵化的這些雞當成了自己的孩子來養,自己的孩子死了,她怎能不傷心?
我還是沒忍住,回了趟家。再一次見到大姐和父母劍拔弩張,我有點害怕,想把父母接出來,讓他們分開住。可父母說啥也不樂意;我又想讓大姐到城里找個工作,可大姐放心不下父母,也不肯出來。他們住在一起,心里面總是別別扭扭的怎么行,那該怎樣把這疙瘩給解開呢?
為了這個,我們幾個妹妹很是傷腦筋。經過幾次電話會議,終于商定要轉移父母的注意力,于是共同出資買了臺全自動麻將桌,讓大姐把村里跟父母年齡相仿的老人請來家里玩兒,大姐也能有一點自己的空余時間,找點自己喜歡的事來做。之后果然各得其樂,關系漸緩。
大姐有一副好嗓子,年輕時她常參加村里組織的文藝會演,她的歌聲如畫眉、似黃雀,聽得人如癡如醉。只為了還父母不斷絮叨在耳邊的“債”,更為了我們這幾個小的不扛事,所以大姐愣是把百靈鳥一樣的嗓音憋回去,把自己變成了在田里犁地的“老黃牛”,永遠躬著身體,面朝黃土背朝天,雙手拽緊了拉繩,在這片熟悉的土地上,一步一個趔趄地向前拉著車,車上坐著父母還有自己的親人們……
我不敢再去想那個畫面,一旦想起就心痛不已。
于是我買了一套音響回去,大姐對著歌詞唱得酣暢淋漓,爹娘坐在沙發上,靜靜地聆聽,眼眸中有亮光閃爍,而此時的大姐完全用歌聲釋放掉了壓抑在心頭的委屈,她眉目舒展,滿面放光,像籬笆外的木槿花在自由自在地綻放。
看到大姐洋溢在臉上的笑容,我才放下心來,我們姊妹幾個能夠在城里安心工作生活,全部得益于大姐對爹娘的精心照顧。
逢年節回家,只要見到迎門墻兩旁的石榴樹,我心里就會感受到日子是踏實的、放松的。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飯,碗里是熱騰騰、香噴噴的大鍋菜,紅白相間的肉片兒、綠瑩瑩的蔥花兒、黃澄澄的雞蛋花兒,還有細長的粉條兒,加上脆生生的白菜葉兒,好像我們這些歸來的姊妹,風塵仆仆匯聚到這個鍋里,熱烈的親情,就在那一刻升騰起來,忙著炒菜的母親神情極為柔和,大姐就在壘砌的灶火前燒火,火光映紅了她的臉龐,也溫熱了她的笑容。
那時候我心里就想著,有父母、有大姐的地方,才是家。
2
涼風從屋后的角落里斜斜吹來,墻角下有蟋蟀低吟,狗的眼睛里泛起安詳的光芒,它很安靜地躺在土堆上迷茫地看著四野,似乎在等待什么人。在故鄉眼中,我就是個遠歸客,幾十年倏忽而過,我也像草木一般,由綠意盎然蛻變為成熟深沉的色調。
2017年10月底,母親溘然長逝,好比房屋少了一根頂梁柱,讓這個家搖搖欲墜,也讓父親愈發孤獨。暮秋本就荒涼,攀緣于墻頭的枯藤和老樹的殘葉在風中搖曳。
歲月無常,時光如水在慢慢地流逝。父親又蒼老了一些,常常咳嗽得喘不過氣來。大夫說,是他的肺開始萎縮了,所以必須戒煙。但是父親的煙是戒不掉的,尤其母親離去后,煙仿佛成了他唯一的伴兒。
父親是個極其寡言的人,他喜歡點著煙卷兒翻看古籍,然后在本子上做些筆記,這個習慣已經陪伴了他許多年,他似乎永遠沉浸在我們觸不到的世界里。我想,他是孤獨的,沒有人能夠走進他的世界;同時,他的世界又是豐富多彩的,就像我們讀書讀進一個神奇的世界一樣,那一扇窗打開,一定會給人帶來獨特的享受。
大姐性子急躁,面對如此沉默的父親,她急得唇邊起了一排燎泡,可任憑她磨破嘴皮,父親仍是自說自話,兩個人似乎永遠不在一個頻道上,根本無法正常交流。
咱爹是不是老年癡呆了?聽大姐這么說,我嚇了一跳,老年癡呆可不是鬧著玩的。
經確診,父親罹患的是自閉癥。
母親去世后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們姊妹幾個又都回到了家里,沉寂已久的農家院再次熱鬧了起來,家里一時間也擠滿了人。
我給父親帶了他最愛喝的竹葉青,二姐給父親穿上了為他新買的衣服和鞋子,還有從小被父母送養的小妹,也攜夫帶子來了,還給父親帶了煙臺蘋果和海參。全家二十多人聚在一起,別提多熱鬧了。幾個年輕的侄子在外面聊天,小孩子在一旁玩鬧,一大家子四世同堂,在鄉鄰們看來,那都是父親的福氣。
大姐忙著在灶火上燒飯,我和二姐擇菜,小妹先用勺兒刮著蘋果給父親吃,然后又拿了特色瓜果分給大姐家的小孫子,真是親情相聚、闔家歡樂的美好日寸光。誰知一眼沒瞅見,父親步履蹣跚地離開沙發,下臺階的時候滑倒在地,我和二姐沖過去,卻怎么也扶不起父親。
這時候大姐就像一陣旋風,邊跑邊嘴里大聲吼道:“腿腳不靈便還瞎跑啥?摔倒了還不是帶累我?”她邊吼邊將雙手從父親肋下插過來,將父親掀起來,我和她一邊一個,一塊兒將父親攙扶回了沙發上。
背后清冷的秋風里傳來二姐低低的埋怨:“我們出錢出物,換不來你一個和氣點兒的態度。”
大姐夫也從酒桌上急匆匆過來,語氣里寫滿嫌棄:“瞧你這粗俗的樣子。”
我的心肝驀地一顫:粗俗?我那百靈鳥一樣輕靈的大姐,不知何時成了親人眼中的粗俗!
我看看二姐,精致的發髻,鑲鉆的首飾,合體的旗袍,中跟的皮鞋,從頭到腳都是溫婉優雅;再看看小妹,也化著精致的妝容,完全是一個都市麗人;再看看我自己,也是一副精心修飾、出門做客的樣子。我們個個十指不沾陽春水,哪像大姐,家里地里,忙里忙外,風吹日曬,丟下耙兒弄掃帚,片刻不得閑,加上照顧父親,她夜不安枕,眼下黑圈暈染,臉龐黑黃,衣衫上留下的是孩童的奶漬和老人的口涎……是大姐用自己的粗糙,換來了我們的精致!
我越想越覺得心酸,先讓愛人將姐夫拉走,然后拉著二姐說了一通悄悄話。我從最初大姐的留村招贅,說到她日常照顧自閉癥的老父親,一樁樁一件件,二姐聽著便低了頭,她含淚拽出自己的行李箱,拿出一套高級化妝品,當著大姐夫的面遞給大姐:“大姐,對不起,我們每個人都是從心里敬重你的!”
3
因為在城里的妹妹們飯碗需得端牢,所以大部分時間用在了工作上,也因而錯失了不少“家人圍坐,燈火可親”的溫馨。年復一年,又是一年,有時候,我們無法回頭,也不敢回頭。
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軌跡,每個人都應該好好地活著。而大姐,只因為父母強加給了她頂門壯戶的責任和義務,她就承擔了原本不屬于她應該承擔的大部分,她將年輕時的特長抹殺,她將一個女人的精致拋棄,直到把自己活成了母親的樣子——照顧父親,體恤姊妹。然而她的付出,在父親和姊妹們眼里,卻像是一廂情愿,根本不值一提。
人們常說“遠香近臭”,的確,父親對我們幾個一年中僅有的兩次帶點錢和禮物來探望的女兒,還有我們的孩子,那叫一個好!遠來是客,而且是貴客。所以活兒是大姐應該干的。“她住著我的房子,將來財產都是她的。”父親覺得理所當然,稍不如意,他還會擺著一家之主的面孔呵斥她,送到手里的飯食也會雞蛋里挑骨頭,沒事找事,讓大姐無比憋屈。
“爹有一次不知道把錢藏哪兒了,大半夜不讓我睡覺,非說我偷了,要去報警。”大姐向我訴苦,“真想你們誰把爹接走,讓我也能松快兩天。”大姐如此喟嘆,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父親特別戀家,“故土難離”是他經常掛在嘴頭的話。盡管我們多次相邀,父親始終不松口。因而父親直至壽終,都沒離開老宅一天。
2022年,父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6月的某個凌晨,大姐打視頻電話過來,說父親彌留了,希望能見我們最后一面,但村里早就因疫情封控了,任何人不能進村。大姐將鏡頭轉向父親的時候,不經意間我看到她悄悄抹去了腮邊的淚。我在這邊也淚如雨下。
二姐在北京,我在山西,小妹在山東,大姐說,父親沒等到我們,久久不肯閉眼。
父親的喪事,大姐辦得極為艱難。因為是招贅,父親的本家們說啥也不讓姐夫摔盆打幡。疫情防控期間,多數人不方便來幫忙,大姐就東鄰西舍地央求,外加管事的找各種名目向大姐要錢,大姐不知白花了多少冤枉錢,村里人有同情的,也有仗勢欺人的,還有騎墻頭的。
“唉,能說會道的那幾個沒能回來,丟下這一輩子老實巴交的大閨女,任憑人欺負嘍!’
耳畔盡是閑言碎語,好聽的少,難聽的多,讓大姐心力交瘁,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憤,她在靈堂哭得暈了過去。
幾天過去,大姐更加憔悴,雙眼布滿血絲,聲音也嘶啞了。出殯的那天,大姐被父親的遠房堂侄兒攔住,讓她必須答應從家里的大院搬出去,否則不允許父親的棺槨進墓地。姐夫上前理論,也被他們挾制住來逼迫大姐。
大姐紅了眼眶,瘋了一般沖進廚房拎了一把菜刀出來,對著堂弟們揮舞著說,你叔病重的時候你們在哪兒?這時候跳出來充啥大尾巴狼?不讓出殯是吧,拿我男人說事是吧?好,豁出去了,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幾個大男人就這么被大姐的氣勢鎮得定在原地。大姐繼續控訴道:“當初就是你們的爹煽惑,說我命硬,一出生克死了弟弟,結婚時說下啥也不讓我們兩口子進門。我男人也是你爹那哥兒幾個從山溝里找來的,說他好拿捏,以后必定孝順,”她又揮舞了下菜刀,繼續說,“現在我才明白,是你們看他老實,就等俺家老人不在了,好來謀這個大院子是吧?”
大姐越說越激動,那幾個堂兄弟被她罵得張口結舌,最終被趕來的村干部拉走了。
鄉親們說,大姐老實溫厚了一輩子,六十多了才露出潑辣的一面。而恰恰是這一從不外露的一面,在那天震懾了全場。甭管認識的不認識的,沾親的帶故的,都統統被大姐威嚇住了,他們紛紛讓開一條路,有的還搭了把手,幫著大姐將父親送到了墓地。
村里人說,大姐終于活成了頂門戶的女人。
曾在現場目睹了那一幕的發小后來跟我說,她那一刻在大姐身上看到了大哥的影子!
4
又兩年過去了,今歲清明,我乘大巴車回到了生我養我的村莊。
只因前兩天,大姐又給我打電話,說夢見父親想喝山西的竹葉青了。而我也恰巧在汾陽的接待宴上,品了一杯竹葉青酒,當晚就夢到了父親,他走來我面前說,來,倒給我一杯!
父親生前愛極了竹葉青酒。
父親離世之后,我因更年期失眠,喜歡上了他最愛的竹酒,微醺之際,我總能看到父親,他帶著對大姐的歉疚,讓我時常想著大姐,多回家陪陪大姐,我含淚應諾,既是對父母,也是對大姐。
醉過才知酒濃。只有在自己經歷更年期病痛的時候,才會想到大姐十幾年前也有更年期。我的更年期能痛痛快快地說出來,因為有人疼,有人安慰,更有人醫治。而大姐的更年期呢,恐怕會隱匿在操持家務中,淡化在鋤草澆地中,深藏在照顧年邁父母的勞累中……
人生,禁不起思量,越是思量,內心就越會升起對大姐無限的感激和隗疚。
爹走了,孫男娣女也都一個個長大了,大姐這兩年才活得松泛了些,性格也改了不少。她說自己一戰成名,軟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如今村里人看到她,都是和善的眼神。“如今日子好過多了。”她的眼角溢滿了笑,綻放的時候,像一朵菊花。
天近黃昏,在大姐的帶領下,我們到了父母的墳前。
春風輕揚,讓我感覺自己是一個橫笛的牧童,騎著一頭不知疲倦的黃牛,在炊煙裊裊的村落中穿行,看天上云卷云舒,聽麥田水流潺潺。落日的余暉,把西天暈染成一圈一圈紅黃的漣漪,裊裊升騰,氤氳了時光,朦朧了遠山和情懷,如母親般守望著每一個月落烏啼的清晨和云淡風輕的黃昏,是煙火人間里塵埃飛揚的絕世風景,它用靜謐誘發出人們心中最柔軟的惆悵,用萬千的芬芳,指引著游子回家的腳步。
我倆在墳前虔誠地祭拜。大姐將竹葉青倒了兩大杯敬上,又替兩個有事沒回家的姐妹磕頭,最后終于忍不住落下淚來,她說,爹,娘,在二老墳前,我現在敢拍著胸脯說,我給咱們家頂住了門戶!四妮說人定勝天,這話我信,你們是沒兒子,可一輩子過得難道不比那些有兒子的人家滋潤嗎?
爹,娘,你們給予我的囑托,我一直記著呢,撐住門戶,咱家大院的門永遠給遠嫁的妹妹們敞開著,讓她們隨時有家可回!
時間一晃就老了,歲月又曾饒過誰?大姐早已年過花甲,兩鬢白發已添,從前的點點滴滴都像田溝里的水,緩緩地流淌過去,舊的已去,新的將來。
這次回鄉,見到的是改造一新卻陌生寬闊的街道,還有林立的高門大院,和似曾相識的孩子們的臉,似乎我的故鄉和其他任何一個村莊沒了多少區別。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大姐聽我念起了詩,笑著攬我人懷,“你放心,只要大姐活著,你永遠都不是路過這個村莊的客人!”
那一刻,在大姐的臉上,我又看到了自由綻放的木槿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