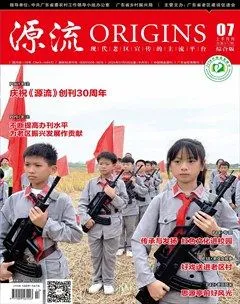在上海開展革命工作的林青
歷史照進現實,夢想引領未來。走進位于七星關城區司法路的林青紀念館,矗立院落中央的林青塑像目光深邃,凝望著遠方,恰如他的另外一個名字—李遠方!當年,他離開畢節山城,去到遠方,追逐引領未來的夢想;今天,歷史照進這一方安寧的世界,遠方的夢想已經實現,讓歷史照進今天發展的現實,這是家鄉對烈士的深情告慰。
林青,原名李遠方,又名李肅如,1911年出生于貴州省畢節縣(今七星關區)。早年因家境貧寒輟學,林青在商店當學徒,不堪學徒生活的壓迫,憤而出走重慶,1927年考入西南美術專科學校。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林青來到上海,在滬東區團委工作,1931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林青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后,在上海參加地下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秋回家鄉畢節,同進步青年秦天真等取得聯系,組織成立“草原藝術研究社”,以畢節中學為陣地,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和民眾運動……1935年7月19日因省工委機關被破壞,遭國民黨特務逮捕。林青在獄中堅貞不屈,嚴守黨的秘密,9月11日在貴陽英勇就義。這便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對林青的記載。
上海革命生涯的開啟
1933年初冬的一天,貴陽大西門港黔汽車公司的經理鐘大亨正啟程去香港,忽然接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通知:“馬上到大十字道觀對面去,有人在那里等你。”帶著滿腹疑問的鐘大亨匆忙趕到約定地點,“見到李遠方(即林青)和繆正元兩人等在那里。他們衣履破爛,面容憔悴,一見就知道處境十分艱難……為他們買了兩雙鞋子,又買了幾件衣服換上……打算在貴陽開展革命活動,希望我從各方面給他們以幫助”。如果鐘大亨是個勢利的商人,當時的林青和繆正元極有可能見不到他,更不可能會有吃飯、買衣物之類的故事了。
他們的故事得從兩年前說起,當時和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林青、繆正元住在上海江灣,有幾個貴州人來投考繆正元就讀的國立勞動大學,嚴金操(即袁超俊,后為八路軍駐貴陽交通站負責人)和鐘大亨也在其中。但他們都沒考上,生活無著落,繆正元和林青設法從學校食堂弄了一些米來救濟。后來,嚴金操和鐘大亨進了杭州公路局,學開汽車。學會之后他們都回到貴陽,嚴金操參加了革命,鐘大亨與黃述章(1953年后在原國家一機部任工程師)等合組港黔公司,代車主在香港購買汽車,再運回貴陽交貨。為此,鐘大亨經常往返貴陽和香港之間。
在林青入黨的這一年,他和家鄉畢節的小學同學、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讀書的繆正元在當時被稱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重逢,一起住在繆正元的宿舍里。他們在上海的重逢并非偶然,因為在畢節的時候,他們志趣相投,都不同程度地閱讀過一些進步書刊。這些書刊主要來自繆正元的哥哥繆象初。“五四運動”時期,繆象初受新思想的熏陶和周素園的影響,在家里存閱《新青年》《湘江評論》等進步書刊。“五卅”運動、沙基慘案發生后,他從廣州給繆正元寄來許多政治宣傳刊物。林青、秦天真、邱在先等曾到繆正元家閱讀和談論這些進步書刊。在其影響下,共同的理想和抱負把他們聯結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繆正元、林青和秦天真三人交往尤為密切,經常在一起讀書和爭論問題,政治見解日趨接近。很快,秦天真去貴陽讀中學;繆正元則在1927年響應繆象初的號召走出去,從畢節輾轉武漢到了上海;林青在無法忍受商店學徒生活的情況下,憤然離家尋找出路,從畢節輾轉重慶到了上海。
當年,15歲的林青到重慶后,愛好文藝的他參加了一個演出進步戲劇的話劇團。1927年,北伐軍攻占南京,遭到英美帝國主義炮擊的消息傳到重慶時,重慶各界群情激憤,舉行了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炮擊南京的暴行、支援北伐戰爭的群眾大會,林青積極參加,在四川軍閥制造的“三·三一”事件中被捕。雖只被拘押了幾個鐘頭后就出來,但林青所在的話劇團卻也因此被迫解散。他就改名李旭(肅)如,也就是考入西南美術專科學校所用的名字。1929年,林青在學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走上了他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革命道路,開啟了他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奮斗的生涯。
按照《林青傳略》的追述,“1931年夏,林青又輾轉到上海,進入提籃橋一家鎖廠當學徒”。但他到達上海的時間應該是1930年,其一是2005年《人民日報》的追述;其二是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總論·人物》,記載林青到上海的時間是1929年;最后是當年和林青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的謝凡生的回憶,他在1931年認識林青的時候說他剛出獄,說明林青此次極有可能是從上海的監獄出來,而非重慶的監獄。因為按照繆正元的回憶,他在重慶只被“拘押了幾個鐘頭”,不存在剛出獄的說法。所以,糜崇習在《貴州省工委第一任書記林青》中說林青“1930年,被中共組織派往上海,在滬東共青團區委工作,不久轉為正式黨員”。林青就這樣在革命低潮中出征上陣,在險惡形勢下接受嚴峻考驗。在滬東區團委的安排下,他到提籃橋鎖廠做個勞累的學徒,像一粒紅色的種子撒在工人中間。
奮戰在上海工人運動前線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中國革命的重心從珠江流域轉移到長江中下游地區,最后使武漢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中樞要地,領導著全國的各級黨組織及其革命活動。因為國民黨“寧漢合流”的達成,黨中央從武漢短暫遷往上海,使上世紀30年代上海工廠最為集中的滬東、滬西地區成為當時工人運動最為激烈的地方。在林青工作和戰斗過的滬東地區,瞿秋白、劉少奇、林育南、惲代英、鄧中夏、蔡和森等國內著名的革命前輩先后擔任過區委書記,領導這里的革命和斗爭。
這段時間,林青與貴州在上海活動的同鄉“黃英倫、繆正元、金嘯遠、樂石麓、謝凡生等人積極參與了上海滬西、滬東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上海工人總罷工”。但1930年至遵義會議召開期間,上海的各種革命思潮此消彼長,滬東、滬西地區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導致了林青在這里工作和奮戰的日子成了一段迷失的歷史。彼時,林青工作的上海“滬東區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時是政治斗爭最激烈的區,托派的中央就在滬東,我們黨、團與托派斗爭很激烈”。這段時間的黨、團組織,在與托派作斗爭的同時,還要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發起工人運動,推進革命高潮的到來。
由于李立三、王明“左”傾冒險錯誤先后導致黨的革命活動遭到嚴重破壞,工人運動開展最為困難、且處于最為關鍵的一段時期,即使是革命前輩惲代英都“深感自己不能力挽狂瀾,只能獻身堵口。他對妻子沈葆英說,困難啊,黨的事業現在處在最困難的關頭,群眾在受難,死,我早已看透了。眼前,蔣介石用血手制造了人間地獄。要摧毀這座地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想,血是不會白流的。革命志士的血,能增長同志們的智慧,擦亮勇士們的眼睛,但愿人們能夠從血的代價中很快醒悟過來,我們的事業還是有希望的,我為此而獻身也是死得其所”。此后不久,惲代英便在沒有發動成功的“五一總示威運動”中被捕,在周恩來、瞿秋白想方設法營救出獄有望時,卻因顧順章叛變而告終。所以,此時被黨組織派到上海參加革命的林青,在這種白色恐怖、叛徒窺視的環境中開展革命工作,面臨的危險可想而知。
因此,在見到謝凡生之前,林青極有可能在上海被捕過。謝凡生回憶和林青見面的時間大約是1931年11月某天,“來了一個和金嘯遠、鄭彥松認識的青年,他外邊衣著破爛,里面穿了一件白橫條的汗衫,容貌很清瘦,據金嘯遠介紹,他叫李遠方,也是貴州人。他剛從監獄出來,生活困難”。這一時期的林青,可謂集工人、革命者身份于一體,工人生活的艱辛與革命斗爭的復雜形勢時刻錘煉著他的堅強意志,塑造著他作為一名地下工作者的優秀品質。
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中
據繆正元回憶,林青和他在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的宿舍住了一段時間后,因為“九·一八”事變爆發,“同學們走上街頭請愿,當局下令解散學校”。繆正元拿到學校發的20元遣散費后,感覺在上海的生活無著落,就和幾個同學去無錫謀生了。在他去無錫的這段時間,林青找到組織,由“度(庹)予之介紹接上了團的關系,在滬東團區委工作。肅如接上團的組織關系后,也把我的團組織關系接上,組織安排我到滬西的小沙渡的街道支部后,我任區委發行部部長”。再次回到上海的繆正元,住在金嘯遠、謝凡生、樂石麓在新閘路租住的一間舊房子里。
而此時的林青為了對其革命工作進行掩護,就去提籃橋的一家鎖廠做學徒。這家鎖廠其實就是“楊樹浦那邊一條街上的一家銅匠鋪,林青在那里當學徒。可以想象,在那樣一家私人開的小金工修理店當學徒,實際就是奴隸式的苦工的代名詞”。生產鎖芯需要銅,可見謝凡生的回憶與林青在鎖廠做學徒并不沖突。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學徒大多只有飯吃,沒有薪金不說,還得承擔很多重活、臟活甚至是老板的家務活,“林青那時的工作和生活都很苦”。有了銅匠鋪工作之后的林青,來繆正元、謝凡生住處的次數雖沒以前那么密集,但個人的精神面貌卻有很大的改變。他來的時候,總在那件藍白條紋汗衫外面罩一件布滿油污的連褲工裝,整個人的精神面貌卻發生了質的變化,激情昂揚的革命斗爭意志絲毫不減,身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氣質讓當時的謝凡生“永遠不會忘記”。
“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林青將滿腔熱忱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動中,與當時在上海的金嘯遠、繆正元、謝凡生、鄭彥松等同鄉和上海的部分學生、工人組織了朝陽音樂社,“通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關系,在上海滬東和滬西工人區域演唱抗日歌曲,以文藝為武器,推動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發展”。那時的林青雖然沒有搬來和金嘯遠、繆正元、謝凡生同住,“但經常來我們這里吃飯,并參加歌詠隊,一道練歌和演出”。他們“每天都出去作宣傳和示威等救亡活動,為著更好地做好抗日救亡工作,還由金嘯遠領頭組織了一個朝陽歌詠隊”。“一·二八”事變后從閘北逃出的朋友申請加入歌詠隊,使其每次練歌時“人員充足,夜間練歌常常練到深夜,幾次被巡捕干涉。白天,我們上街參加反日大同盟領導的示威游行和募捐,到滬西和滬東廠區為工人演出”。
對此,謝凡生還回憶了他們“某次在法大馬路示威,被印度巡捕打傷左手”的經歷。此外,林青他們還走向街頭,發放一些黨的宣傳品。每次外出都必須兩人一組,一人放哨、一人散發。有時,他們還會把宣傳品先折疊好,分發到居民們的信箱里;有時也會成疊放到停在路邊的汽車頂上,用小石子壓著,汽車開動,傳單就會滿天飛;有時還把傳單蓋在報紙或廣告下面,往墻上貼。他們開展的這些活動,還是沒逃過當時上海街頭穿便衣的“包打聽”和馬路上隨時“抄把子”的巡捕,危機隨著活動開展次數的增多而步步緊逼。
提籃橋監獄中理論水平提升
林青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的時期,“積極參加了上海黨組織領導的‘文學研究社’‘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活動,閱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列主義書籍和其他進步書刊,進一步增強了對馬列主義的信仰,為他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尤其是被捕入獄后,又和“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活動家……普陀區首任區委書記吳亮平”同住一個監牢,“在吳的幫助下,肅如學習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他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提高很快”。
當時的上海提籃橋監獄,專門關押政治犯的是L牢、M牢,“房子和其他監牢一樣,三公分粗的鐵柵,門上的鎖足有十六開本書籍那么大,上面有表示鎖檔的紅箭頭,第一檔的鑰匙由外國人掌握,第二、三檔由印度人管,中國巡捕是挨不了邊的”;“每間關一人或是三人。嚴冬酷暑,日夜坐臥在水泥地上,大小便也在里邊。伙食很壞,而且吃不飽,終日饑腸轆轆。這些對于革命者來說算不了什么”。據吳亮平回憶,當時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不讓學習,因為獄中無書可看。后來,由于革命者的堅持斗爭和外界人士的支援,監獄當局最后被迫改變決定,允許經過嚴格審查的書送入獄中。獄中,革命者雖千方百計與外界聯系,但獄中還是“人多書少,大多數人無書可讀,有的難友不識字。大家都迫切要求學習,怎么辦?獄中難友為了在生活上、學習上以及斗爭上相互幫助,秘密成立了難友互助組織……從實際情況和斗爭需要考慮,決定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幫助大家進一步加強無產階級世界觀和革命人生觀。采取成立學習小組和作報告等方法進行學習”。學習的時間一般都在晚上,因為獄中巡邏次數較少,大家就會充分利用這一時間學習、討論。而白天的學習,只能在同室的難友之間開展,他們彼此悄悄地進行討論,交流思想和看法。
還有一種學習形式是獄中報告會,應難友系統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而開設。可獄中不可能有相關的材料和書籍。入獄前,吳亮平曾編寫過《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一書出版,互助組織就決定要他對此作有系統的講話。在獄中對此進行講話,白天肯定不行,只能是“入夜之后,看守人一般不大來巡邏,我(吳亮平)就趁此機會,站立在鐵柵欄邊用隔壁可以聽到的、較大一點的聲音給難友們講,每講兩句,就由左右鄰室的人依次向兩邊傳達,一個晚上講一段。講后,各小組按情況進行討論。講話時,由牢房兩端的難友望風,聽到看守人來巡邏,就立即敲墻壁,隔壁的難友聽到了,依次敲下去,很快地警告講話人停講。用這種方法,我順利地完成了報告任務”。
“革命何須問死生,將身許國倍光榮。”這是作為革命者的黎又霖在獄中的抒懷,它同樣適合在上海不畏生死、參加革命活動的林青。在提籃橋監獄的日子里,林青除了參加這種“鐵窗里面的學習,充實了獄中生活的戰斗內容”,提高了他對革命的認識,增強了對革命勝利的信念,鼓舞了他的革命斗志之外;還經常接受吳亮平的教誨,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素養,很快就成長為一名意志堅定的革命者,為他后來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33年秋,“英王舉行登基25周年大典,林青在服刑一年半后被大赦出獄”。他“被黨組織派回貴州畢節家鄉”,通過楊玉珍的關系找到也被大赦出獄的繆正元,一起商量回貴州建立蘇維埃、繼續搞革命活動的想法。確定下來后,他們就從上海經武漢到重慶,回到貴陽活動一段時間后才回畢節。(本文寫作中,參考了鐘大亨《獄中二十日見聞—懷念林青烈士》、李臘生《1927年歷史大轉折中的武漢紅色記憶》、劉雪葦《關于三十年代上海地區的共青團》、謝凡生《在監獄中》《貴陽—上海—貴陽》《憶林青同志》、吳黎平《鐵窗里面的學習》《中國共產黨楊浦(滬東)史》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