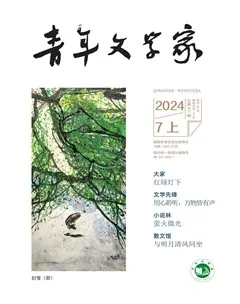用心聆聽,萬物皆有聲

讀《莊子》,其中有一段形容風的聲音,美極了。“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這些千孔萬竅被大風吹動所發出的聲音,有的像急流沖激的聲音,有的像射箭發出的聲音,有的像叱責的聲音,有的像呼吸的聲音,有的像叫喊的聲音,有的像哭號的聲音,有的像深谷發出的聲音,有的像咬牙切齒感嘆的聲音。前面的風吹過,后面的風相應又吹來。小風的聲音小,大風則聲音大。大風吹過后,所有的孔竅都恢復平靜,空寂無聲,然而只見到草木還在搖曳擺動,沒有停止。莊子的文字喚醒了我沉睡的記憶,風真的是有聲音、有形狀的。
風的聲音是如此豐富,我們是否用心聽過呢?記得小時候,這些聲音都存在于我的耳朵里,輕撫過我的每一寸肌理。我喜歡唐寅的《看泉聽風圖》,畫中崇山陡峻,峭壁如削,山崖間老樹虬曲,枝葉蒼茂,清泉瀉于兩峰之間,兩位高士沐風坐于石上,悠然自得,陶醉于山水之間。還有南宋畫家馬麟的《靜聽松風圖》,畫中古松藤蔓搖擺,送風正盛,高士悠然坐臥,衣襟敞開,傾首凝神諦聽。于雅處聽風,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雅事之一。這是生活的另一種意境,生命的另一個空間,脫離日常煩瑣與世俗的紛爭。奔忙一天,內心被全部攪亂后看到這樣一幅圖畫,是撫慰,是療愈。我會試想進入畫中去做一個靜聽松風的散人,那該是多么愜意的事。當我靜下心,畫中的松風颯颯作響,拂去我的焦躁,送來一片清涼。
秋天到了,可以去聽聽秋蟲的聲音。清晨,你可以枕在床頭聽,倚在窗邊聽,扶著欄桿聽,貼著墻角聽,坐在樹下聽,你總能聽到一絲一縷秋蟲的聲音。如若到了鄉野,月色籠著秋風,蟲聲盈耳,豈不妙哉。細聽,那些被樂師精心調教過,或沒有調教過的,各抒靈趣—那些躊躇滿志,聲音洪亮而又高亢,準備來一場生死抉擇;那些哀怨的詩人,低低絮語,在故鄉徘徊流連;婉轉悠揚的聲音,是那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漫步在園林中,聽風在竹林里穿行,發出颯颯之聲,如若下一場大雨。此時,悠然坐于聽雨軒,喝一壺茶,聽雨打芭蕉,聽雨落荷上,便能了悟為何古人為此亭命名“聽雨軒”。
再走進街巷鬧市,上班的人搖鈴的叮叮聲,賣花姑娘清脆的叫喊聲,小攤販扯開嗓子的叫賣聲……這是市井里最普通,也最具煙火氣息的聲音。這聲音最平凡,也最撫人心。
回到當今我們的日常生活。兩點一線的生活模式,我們的眼里是滿屏的數據,是層層疊疊的文案,是聽不完的激勵人心的豪言壯語,是等待實現的長長的愿望清單……這些讓我們春風得意,也讓我們的耳朵變得失靈,對生活變得遲鈍,用心聆聽變得奢侈。
即便在生活中,用心聆聽也是難得的事情。親子之間,朋友之間,情侶之間,夫妻之間,兩個人看似在溝通,一個人心不在焉,看著手機,望著天空,抑或一個人看似在聽,實則內心早已有了論斷。我們早已忘卻聆聽彼此內心的聲音,兩顆心像斷聯的信號,沒有一絲交匯。
我想,我們現代人缺乏如莊子一樣“一心一物”的心境,用心與自然真實觸碰。我們被世俗外物所困,縱使跋涉千里來到大自然的懷抱,也聽不到鳥的啁啾聲,落葉的簌簌聲,流水的淙淙聲,這些最天然的聲音了。但是,若尋回最原始的耳朵,用心聆聽,你一定會聽到很多聲音的。
作者簡介:
邦尼,本名黃柳彬。青年作家、高級閱讀指導師、高級教育規劃師、邦尼少年小作家文學院創始人、回歸文學社上海攬星分社社長,著有暢銷書《孩子愛上寫作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