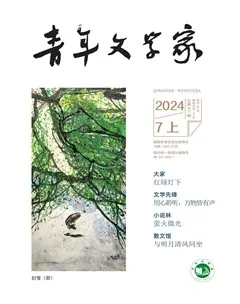近鄉情更怯(外一篇)

唐代宋之問有句詩說:“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年關已過,過年該有的儀式都有了。這日夜晚,我獨自坐在家中,看著窗外煙花璀璨,望著望著,心里油然而生一絲落寞。腦海里浮現的是上班的場景—投身工作時,生活過得更充實;但當接到單位的上班通知時,又有一種矛盾之感。那是對即將遠行的期待,又是對家鄉的戀戀不舍,這種感覺難以言喻。要知道,我出生與成長的故鄉,曾經也是我拼命想逃離的地方,因為可以擺脫父母的束縛,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緊閉的心幕,慢慢地拉開了,交迭出少年時的模樣。身處鄉下,農民身份的父母有著純樸的教育方式。他們常用類似于嘮叨的方式,希冀著未來的一天,他們的子女能洗掉身上的泥巴,走出鄉村,走向美好的未來。殊不知,這樣偏執的方式,讓我煩膩,更是無可奈何。
隨著年歲漸長,我終于辭父別母,走進了大學校園。因大學離家有幾百里的路程,正常情況下,得等到寒暑假才能夠返鄉。每每即將返鄉之時,內心總是興奮不已,回到那個我熟悉的地方與親人團聚,分享彼此的生活。那間小屋,或許低矮逼仄,但我住得無比溫暖。有一個人,她嘮叨個沒完;有一個人,他沉默寡言;有一種幸福,叫回家見到雙親。回家的路,或許顛簸,或許泥濘,但向著那個方向靠近,便無比心安。
走上工作崗位后,我毅然選擇了離家近的工作,每周放假可以返鄉,從此漸漸隱退了“近鄉情怯”之思。返鄉的頻率漸漸多了起來,當我把歸期告知母親,她的言語間總是沁滿了喜悅,又想為我買東買西,準備各種我喜歡的美食。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每次按照與父母約定的日期回家,一開門,總是先迎來等候已久的父母。我放下行李,雙向奔赴,肆無忌憚地享受著溫情。假期終歸是要結束的,啟程離鄉,往往都是父母一方目送。我的雙腳灌滿鉛似的,踏出家門,坐進車里。打火,拉下手剎,踩下離合,載我駛向一個又一個陌生的站點。那樣的時刻,無論眼中還是心里,都是酸酸的。
隨著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親情也隨著距離的拉開逐漸疏離。我像個冷眼旁觀者,看著事態的變化,表面上無動于衷,內心似明鏡,知道這條橫跨在我和家人之間的直線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繼續向兩端拉長、拉遠。內心盡管掙扎,卻要學著放手了,有些離別早晚要來臨的。再一次回家,可能是雙鬢斑白,甚至是生離死別。我想,這應該算是在歲月的沉淀中,完成的一次又一次的鄉愁閉環。
每次回家總會有類似的體驗,盡管前途未卜,我還是不得不奔忙在路上。邁出家門那一刻,竟有些猶豫,不禁笑這“近鄉情更怯”。
豬肉丸子滋味長
豬肉丸子,亦名丸子、水丸,是故鄉常見的美食。它的制作方法和牛肉丸相似,只是用料有所區別。首先精選新鮮豬肉,打成糊狀,加入硼砂,再輔以簡單的調味,不停地用手攪動和摔打,直至肉泥有了韌勁,捏起一大把用手一擠,肉泥便會變成一個個小球。
這種丸子因其獨特的風味,時常綿密地鋪進夢境里。童年,奶奶,鄉愁,時間的經緯,無數次交迭重現。
那是一個盛夏的夜晚,奶奶帶著我和弟弟來到鄰居家的井邊沖涼,鄰居那天剛好煮著豬肉丸子。一出鍋,端出門外,那香氣氤氳,飄進我們的鼻翼里。我們顧不得享受沖涼的快感,手里端著水桶,眼睛直勾勾地看著鄰居碗里的丸子,望著,望著,仿佛眼睛里都綴著光。
奶奶瞥見了我們的反應,第二天早上,奶奶就為我們兄弟倆端來了豬肉丸子。我們拿起湯匙大快朵頤地吃了起來。站在一旁的奶奶欣慰地看著我們享受美食,還不時輕聲說道:“慢點兒吃,別噎著,吃完鍋里還有。”后來,我從母親的嘴里得知,那天,奶奶看著我們可憐兮兮地看著別人吃丸子,她的心里如同千萬只螞蟻噬咬一般,很不是滋味。當晚,她心一狠,等天一亮,就去集市買來豬肉丸子,讓她的孫子吃個心滿意足。
我天生瘦弱、膽小,又從不敢像弟弟那樣無所顧忌地吐露愿望。奶奶擔心我太瘦不健康,便常常讓我多吃。那一次我生日,按照閩南的習俗,生日要吃雞蛋丸子面線湯。在家里的土灶旁,奶奶端出了兩碗面線湯,一碗滿是面線,另一碗是面線上鋪著七八個丸子。按照長輩的教導,哥哥得讓著弟弟,不出意外,弟弟選擇了那一碗有豬肉丸子的。奶奶端著剩下那一碗,把我帶到角落處,在碗內一翻,碗底下埋著一個煎蛋,還有滿滿當當的豬肉丸子。她眼神暗示我趕快吃掉,不要讓弟弟發現。那時候,豬肉丸子剛在市面上出現,售價也不便宜,大人們自是舍不得吃。豬肉丸子滋味長,蘊藏著奶奶濃濃的慈愛,每每憶起,一抹暖意盈滿心田。
時光倏忽而飛,我離開故鄉,去外地求學,心里仍念念不忘故鄉的豬肉丸子,總是期待著早日放假,回到故鄉,滿足那沒出息的口腹之欲。走上工作崗位后,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謀生。其間,在尋尋覓覓中,吃過很多類似的豬肉丸子,但都品嘗不出其中的綿長滋味。
時光被歲月拉長,對于故鄉的豬肉丸子越發想念。后來,每次返鄉,我總會從家里帶出一大包豬肉丸子,工作之余,解解饞,并回憶那溫暖的歲月。那滋味,才下舌尖,又上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