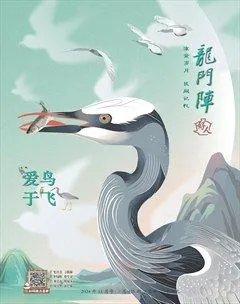那年,父親打了我一巴掌
“你要就要,怎么能讓你娘生病?”
上小學二年級時,我與我們生產隊會計的兒子小峰同桌。那時,我們背上背的、手里拎的都是家里用零碎布頭縫制的書包。有藍色的布也有白色的布,說好看又不好看。書包薄薄的,就像我們瘦弱的身體,背在身上拍著屁股或打著腿,一點兒也不疼,不像現在孩子的書包這么結實。我們書包里除了語文、數學等幾本書和少量的作業本外,就是一支筆和一塊橡皮,沒有儲存筆和橡皮的文具盒。裝的東西雖然少,但書包用久了照樣會壞,不是破了一個洞,就是裂開了一道口子。因此,大家的書包里掉東西是常有的事,當然掉得最多的還是筆和橡皮這些小東西,書本一般是不會丟失的。在那貧窮的年代,筆和橡皮雖然僅要幾分錢,但很多人家都買不起。家人省吃儉用好不容易攢幾個錢甚至借錢幫孩子買文具,幾乎能用一學期,當然那個時候作業也不多。可沒了筆和橡皮,不僅沒法做作業,還會招來家長的一頓打罵。好在我的父母比較寬容,如果丟了文具不會罵我,更不會打我。母親會幫我把書包破損的地方縫補好,父親則會想方設法為我重新買一支筆或一塊橡皮。
其實那時候不是沒有文具盒賣,而是買不起,除了個別家境稍優的人家,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沒有文具盒的。沒有文具盒,有些同學就用藥盒代替。藥盒是那種裝著一支支玻璃針劑的紙盒,一盒基本上是十支藥水,紙盒為長方形,有大有小。無論大小,撕去里面的隔離紙,裝幾支筆和橡皮綽綽有余。然而擁有這種“文具盒”的學生也不多,基本上是醫生家的或是與醫生關系較好的人家的孩子,抑或是家里有人生病去醫院打針,碰巧紙盒里沒有針劑了,央求醫生送給他,帶回來給孩子用的。
可是,我的家人身體都好好的,從來沒生過病;我們也不認識任何一個醫生,父親雖認識大隊的赤腳醫生,然僅僅是點頭之交。自然,我用不上“文具盒”(藥盒)。
有一天清晨,我來到學校,走進教室,看到同桌小峰從書包里拿出了一個嶄新的“文具盒”(藥盒)。這紙盒不僅大,而且盒面上圖案精美。我對小峰說:“哪來的藥盒,借給我看看。”可小峰不給,說:“這是我媽昨天在醫院里打針,向醫生要的。我媽囑咐我要好好愛護它,不能弄壞了。”無論我怎樣請求,小峰就是不讓我拿。我氣沖沖地說:“哼,不給就算了,我回去也叫我娘生病,讓她到醫院拿個更好的,氣死你!”
那天放學回到家,我就纏著母親說:“娘,你為什么不生病?人家都有好看的藥盒,就我沒有。你快點生病,去醫院打針,我才有藥盒。”父親在一旁聽了,大怒道:“混賬小子,你怎么能和你娘說這樣的話?你竟然希望你娘生病?”我不服氣地說:“我的筆和橡皮沒處放,我要藥盒。今天小峰都有了,是他媽在醫院看病要的,我也要。”“你要就要,怎么能讓你娘生病?”“娘不生病哪里來盒子,我就要娘生病!”“啪!”父親忍無可忍,伸手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我捂著臉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喊:“我就要、就要!”母親趕緊把我拉進懷里,責怪父親:“孩子不懂事,你打他干嗎!”父親看看我,嘆了一口氣,轉身走出家門。
第二天早上,我吃過早飯,準備去上學。母親幫我整理好書包,又拿出一個大大的紙盒遞給我。我詫異地問:“娘,哪來的藥盒?你生病了?”母親說:“不是我生病了,是你爹昨晚去赤腳醫生家,走在路上故意摔傷了腿,硬要醫生給他打止痛針,才要了這個盒子。”
這時,父親跛著腳從外面走進屋來。看著他一瘸一拐走路的樣子,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