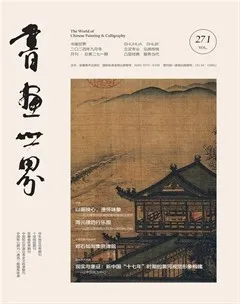現(xiàn)實(shí)與象征:新中國“十七年”時期的黃河視覺形象構(gòu)建




發(fā)端于青藏高原的黃河,一路向東奔騰入海,自古以來被視為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與長江一起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抗戰(zhàn)期間,黃河這一視覺形象作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或中華民族的象征,在美術(shù)作品中反復(fù)出現(xiàn)。這些作品多通過對黃河題材的表現(xiàn),而體現(xiàn)民族與國家認(rèn)同感。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的“十七年”間,隨著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開展,黃河形象逐漸成為新中國文藝作品中的經(jīng)典圖像,并在其象征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增添了體現(xiàn)時代之“新”的“新”意。
這種時代新象, 既包含“ 新形式”,也包括“新內(nèi)容”。在“新形式”方面: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畫領(lǐng)域,面臨著“國畫要不要改造”的時代問題。畫家李可染于1950年2月在《人民美術(shù)》上發(fā)表了《談中國畫的改造》一文。1953年,革命文藝工作者艾青在上海美術(shù)工作者政治講習(xí)班上作了“關(guān)于中國畫改造問題”的講話,并倡議創(chuàng)作“新國畫”。在“新內(nèi)容”方面:“十七年”時期,一大批以“建設(shè)”為主題的美術(shù)作品應(yīng)運(yùn)而生,構(gòu)成此時期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nèi)容。新中國成立后,美術(shù)創(chuàng)作者們開始走向祖國大好河山,扎根祖國各地進(jìn)行寫生,描繪山河新貌,并在此過程中不斷拓展與時代貼近的藝術(shù)語言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十七年”時期的黃河題材美術(shù)作品,即誕生于以上語境之中。橋梁、大壩、機(jī)器、建筑等工業(yè)意象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的美術(shù)作品中,構(gòu)成了新時代的現(xiàn)實(shí)景觀,它們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探索與發(fā)展。當(dāng)傳統(tǒng)筆墨下的黃河形象與這些新意象相融合,所流露出的是對家園建設(shè)的美好愿景與理想,以及一種積極歡騰的樂觀姿態(tài)。
《黃河龍門口》(圖1)創(chuàng)作于20世紀(jì)60年代,畫家方濟(jì)眾為長安畫派的代表畫家。黃河龍門口也稱“禹門口”,位于黃河晉陜峽谷的南端出口,東西兩山夾河,兩側(cè)懸崖陡峭,河道在此處突然收窄,造就出別樣壯麗的景觀。但新時代的畫家顯然并不滿足于對自然景觀的單純描繪。方濟(jì)眾首先在畫面中運(yùn)用了傳統(tǒng)的筆墨手法,對山石進(jìn)行點(diǎn)染、勾勒,墨色有干有濕,筆力老到,使山石整體具有險峻如刀削般的力量感。畫家將紅色與墨色相融,將最為厚重的墨色置于畫面最下方,色彩逐漸向上遞減,到遠(yuǎn)處天邊,化為一抹簡淡蜿蜒的遠(yuǎn)山,為整幅畫面增添了沉穩(wěn)的氣息。中間湍流的河道婉轉(zhuǎn)曲折,其中有船只在行進(jìn),突出一個“險”字。較有新意的是,畫面左上方兩峰之間有一座橋,上面是往來的行人,絡(luò)繹不絕。此作既表現(xiàn)出龍門口壯闊險峻的景觀,又看似不經(jīng)意地點(diǎn)出了“天塹變通途”的主旨,謳歌山河新貌。
何海霞的《黃河禹門口》(圖2)則是以另一視角描繪這一題材的作品,畫面突破了中國畫傳統(tǒng)的“三遠(yuǎn)”構(gòu)圖,以立體傾斜俯瞰的角度來呈現(xiàn)兩山夾河的奇景。何海霞特意著力描繪橫亙于兩山之間的橋梁,橋上的點(diǎn)景人物不再作為點(diǎn)綴性元素,而是作為本畫的“畫眼”而存在,它與橋下的驚濤駭浪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突破傳統(tǒng)的形式為作品增添了雄渾的氣息。
黃河的精神不僅在于黃河本身,而更在于其與人的關(guān)系。黃河流域的生產(chǎn)建設(shè)、生活傳統(tǒng)、衣食住行、風(fēng)俗人情都與中華民族的價值觀緊密相連。長安畫派代表畫家趙望云在新中國成立后,多次深入黃河沿岸地區(qū)進(jìn)行寫生,并在此時期完成了以人物畫為主的寫生到以風(fēng)景為主的新國畫的轉(zhuǎn)變,筆下的作品具有真切的生活氣息和時代感,表現(xiàn)出對底層勞動人民及其生活環(huán)境的觀察與關(guān)注。(圖3)自古以來,黃河水患頻發(fā),黃河沿岸人民深受其害。新中國成立后,黃河治理成為須著力解決的重要課題。1952年10月,毛澤東主席在視察黃河時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號召。1957年4月13日,三門峽水利工程破土動工,1961年黃河三門峽大壩正式建成,是我國在黃河干流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三門峽大壩也因此被譽(yù)為“黃河第一壩”。三門峽處于河南省三門峽市區(qū)東北方,位于豫晉兩省交界處。據(jù)傳古時大禹治水在此疏浚河道,“斧劈三門”,形成了神門、鬼門、人門三島,故稱為“三門峽”。這里景色壯觀奇?zhèn)ィc古代傳說一起賦予了三門峽傳奇色彩。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建設(shè)成就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構(gòu)成了此階段被反復(fù)描繪的重要題材。
畫家謝瑞階是河南鞏義人,筆名黃河老人,黃河是他一生中反復(fù)描繪的藝術(shù)主題。從1955年起,謝瑞階就多次深入三門峽水利建設(shè)工地,考察現(xiàn)場,體驗(yàn)生活,留下了上百幅寫生速寫作品。他于1955年創(chuàng)作完成的中國畫作品《三門峽地質(zhì)勘探》(圖4),是較早描繪三門峽工地建設(shè)題材的作品,即工程早期的勘探活動。畫作為橫向全景式構(gòu)圖,全幅長達(dá)177厘米,前景仔細(xì)描繪了勘探人員、車隊(duì)和物資,與中景洶涌的河水和遠(yuǎn)景連綿的群山遙相呼應(yīng),整個畫面空間被極力擴(kuò)充、拉開。在光影表現(xiàn)上,作品也借鑒了油畫的表現(xiàn)力,如強(qiáng)化黃河水的黃色明度,為整幅畫面營造出一種明快盎然的氛圍。對于水流和浪花的表現(xiàn),也不局限于傳統(tǒng)的繪水之法,而是為其增加了立體空間感,突出此地波濤之險。
1960年,作為“新金陵畫派”的代表,以傅抱石、錢松嵒、宋文治、魏紫熙、亞明等為主體的江蘇國畫寫生團(tuán),前往祖國西北、華南進(jìn)行寫生,先后經(jīng)過豫、陜、川、鄂、湘等省,行程兩萬余里。1960年9月21日,寫生團(tuán)抵達(dá)三門峽市,參觀了建設(shè)中的三門峽大壩工地。這年底,傅抱石便創(chuàng)作了作品《黃河清》(圖見扉頁)。
《黃河清》之畫題出自“圣人出,黃河清”這一典故,畫面中的題跋文字也顯示出傅抱石在創(chuàng)作時所寄托的深厚情感:“一九六○年九月廿一日抵三門峽,至則前三日黃河之水清矣,清明澄澈,一平如鏡,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觀也。水閘工程尚未全竣,而億兆人民將永蒙福祉,豈可無圖頌之。”而當(dāng)真正用畫筆傳達(dá)黃河水“清明澄澈”的景象之時,傅抱石說:“就是這個‘清’字把我們難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筆墨是不會有辦法的,一不小心,還容易畫成長江或是太湖呢!”[1]他采取的辦法是用兩岸的山勢來表現(xiàn)三門峽的流域特點(diǎn)。此外,此作也不似同時期大多作品那樣,直接描繪忙碌熱鬧的工地建設(shè)場景,而是仍以大壩兩岸的山水作為主題表現(xiàn)對象,前景高聳的電線桿和高壓電線,構(gòu)成此畫的“畫眼”,電線一兩筆的飛白彰顯畫家功力,以舉重若輕的方式體現(xiàn)出三門峽正火熱進(jìn)行的工地建設(shè)。
江蘇國畫寫生團(tuán)的同行畫家錢松嵒,同為“新金陵畫派”的主將之一,也留下了多幅與三門峽相關(guān)的創(chuàng)作。他創(chuàng)作于1960年的《三門峽工地》(圖見扉頁)是一幅紙本水墨設(shè)色作品。畫面為豎式構(gòu)圖,上半部呈現(xiàn)三門峽工地的建設(shè)場面,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機(jī)器、鱗次櫛比的建筑,都坐落在斧劈般的大塊山體之上。畫面右下角是近處的禹王廟,在遠(yuǎn)處火熱場景的對比之下倒顯得孤寂清冷。畫上的詩文題跋“禹王血食已千秋,日日廟前滾濁流。不料黃河今降服,笑他空對鬼門愁。六億人民是圣賢,禹王瞠目一龕前。驚看倒轉(zhuǎn)乾坤手,腰斬黃龍利萬年。過三門峽畫禹王廟”也表達(dá)了作者的主旨,即歷朝歷代都難以治理的黃河水患在新中國終于得到了“降服”。這幅畫的色調(diào)十分引人注目,山石黃土大膽運(yùn)用了朱砂和赭石,畫面中紅色與墨色相互呼應(yīng),為畫面注入昂揚(yáng)熱烈的情感,令人想到他的另一作品《紅巖》。繁與簡的對比尤其突出,中間大片留白,為兩岸的古今對話創(chuàng)造出一個引人遐思的空間,書法題跋本身在布局中也起到了增加氣勢的作用。
相對于前者的浪漫主義色彩,錢松嵒創(chuàng)作于1963年的《三門峽》(圖見扉頁)則更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基調(diào)。《三門峽》以墨色為主調(diào),輔以赭石渲染山體,描繪出黃河岸邊的山石、大壩和層層梯田。作品的經(jīng)營位置方面,畫家將筆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景象進(jìn)行了巧妙的融合,三門峽大壩等人工景觀集中于畫面左上方的遠(yuǎn)處,而沿岸的山石、云霧等,以淺絳山水的方式置于畫面近景和中景,傳統(tǒng)山水與建設(shè)場景于畫面中遙相呼應(yīng),構(gòu)建出新的時代美學(xué)。
“新金陵畫派”的宋文治以三門峽為題材先后創(chuàng)作過多幅版本的作品,并都命名為《山川巨變》。其于1959年6月就已前往三門峽寫生,1960年9月隨江蘇國畫寫生團(tuán)已是第二次來到此地。宋文治深受傳統(tǒng)筆墨浸染,初學(xué)清初“四王”,后逐漸在實(shí)踐中探索中國畫的新形式。這幅于1960年創(chuàng)作、收藏于中國美術(shù)館的《山川巨變》(圖見扉頁)是一幅淺絳山水畫,但它在色彩上比傳統(tǒng)淺絳山水畫的設(shè)色更加鮮明。石青色被畫家施染于畫面中景山坡梯田上,成為橫亙于畫面中間的主色調(diào)。前景山川、梯田以墨色為主,遠(yuǎn)景的對岸、大壩則施以淡石綠、淡赭色。畫面采取了與《黃河清》類似的做法,在兩岸之間描繪出電線桿與電線,也使整個畫面元素得以整合在一起。與傅抱石、錢松嵒的巧妙構(gòu)思不同的是,宋文治對同題材的處理相對更為平鋪直敘,畫風(fēng)清秀雋麗,自成一派。從中也可看出,對同一題材的處理,不同畫家在探索中國畫新形式的同時,也保留了自己獨(dú)特的風(fēng)格。
由以上可見,“十七年”時期,藝術(shù)家們秉持著“為祖國山河立傳”的創(chuàng)作思想,讓此時期美術(shù)作品中的黃河形象通過中國畫這一傳統(tǒng)畫種呈現(xiàn)出新時代的現(xiàn)實(shí)。同時,此時期的黃河題材美術(shù)作品,也已經(jīng)突破了其在空間上的地域特性,而成為時代和民族的精神象征。這種視覺象征并非一味借助傳統(tǒng)的方式,而是更多地傳達(dá)出時代新象,在這一傳遞過程中實(shí)現(xiàn)了中國畫筆墨上與時俱進(jìn)的新發(fā)展,以此構(gòu)成了20世紀(jì)中國美術(shù)史上的一個獨(dú)特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