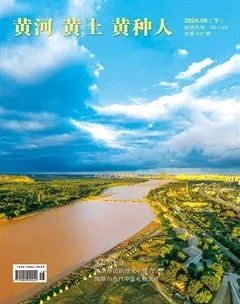陶鬲與古代中國禮制文化






陶鬲的起源
《說文解字》曰:“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漢書·郊祀志上》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其空足曰鬲。”鬲的字形演變為:甲骨文" " (《甲文編》108頁)到金文
(《金文編》171頁)再到小篆" " (《說文》62頁)、楷書" " (《篆隸表》189頁)。甲骨文的鬲字像是一個圓腹器物底部正被火煮燒的樣子,而且這個甲骨文的“鬲”和甲骨文的“鼎”字如出一轍。因此辭書《爾雅》上就說鬲是“款足鼎”,“款足”就是足部中空的意思。
《禮儀·士喪禮》記載:“煮于垼,用重鬲。”《孔子家語·致思》云:“瓦鬲煮食。”可見鬲是飲食的重要用器。《禮記·禮運》記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說明禮與飲食關系之密切。在遠古時代,人類最初的食物來源主要是生食。隨著對自然界認識的加深和生存技能的提高,人類逐漸發現了火的作用,并開始嘗試利用火來加熱食物。火的使用不僅改變了食物的口感和營養價值,更促進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陶鬲作為一種新型的炊具應運而生,成為人類從生食到熟食轉變過程中的重要工具。
陶鬲的出現,不早于龍山文化時期。中原地區早于龍山時期的廟底溝以及同時期其他文化遺存中的袋足器僅有陶斝,不見陶鬲,承接廟底溝文化的陶寺類型早期也不見陶鬲出現,中期初見鬲。最初陶鬲在形制上與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較為相似,目前發現最早的陶鬲是在豫北冀南地區龍山文化早期的側裝雙鋬手陶鬲,龍山文化中期雙鋬減少,出現單耳陶鬲。至二里頭文化和先商時期,帶耳陶鬲逐漸消失,出現尖底實足,且袋足變小,器腹加深。商周時期,尖底實足逐步演變消失。最初的陶鬲通體打磨,表皮光滑,到了中后期,身上才出現拍打或刻畫的繩紋。
陶鬲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當時的人類社會正處于從生食到熟食的轉變過程中。陶鬲作為這一轉變的產物,不僅體現了人類對火的掌控和利用,更展現了古代人民對炊具設計的智慧和創新。早期的陶鬲多為侈口、圓腹、三個袋狀足,腿長襠深的陶鬲年代較早,這種設計使得陶鬲能夠在三個足下直接燃火,可以增大受熱面積,便于烹飪。陶鬲的祖型,一般認為與尖底器、鼎、斝(釜灶)、三足器等有密切的關系。對中國史前考古作出重要貢獻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其著作《甘肅考古記》中認為,鬲由三個尖底器結合而成,“鬲之為物,乃專為尖底器而作。蓋此等尖底器,可以插入鬲之空足”,首次將尖底器與鬲聯系起來。1947年,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在《中國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一文的注釋中認為,鬲是由鼎演變而來。
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于考古材料的日漸豐富,關于鬲的來源問題又有了新的觀點: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提出鬲是由斝演變而來(張忠培、楊晶:《客省莊與三里橋文化單把鬲及其相關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在其著作《單把鬲譜系研究》中推斷單把斝式鬲與釜形斝必有淵源。內蒙古涼城老虎山遺址的陶鬲是由陶斝演變而來稱為斝式鬲(高天麟:《黃河前套及其以南部分地區的龍山文化遺存試析》)。河套地區龍山文化晚期陶鬲有神木石峁遺址出土單把罐型鬲及帶鋬罐型鬲,均由老虎山遺存中的罐型斝及帶鋬罐型鬲發展而來(張忠培、關強:《“河套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的研究》)。早期陶鬲發展演變中單把鬲比較早,主要在渭水流域及河南西部和山西中南部一帶,再往東,河北和河南北部一帶的鬲,主要帶兩個雞冠形鋬手。東北地區的陶鬲始見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另外,內蒙古海拉爾西山發現的大型陶鬲最大口徑達到31厘米,與甘肅沙井文化大型的陶鬲相似,體現了草原居民氏族公社共食的原始習俗。
陶鬲的演變
距今4600—4000年的黃河流域龍山文化陶鬲,釜深占器高的二分之一以上,襠低于器高二分之一,三袋足呈分叉外張之勢,相應襠也較寬。器表呈褐灰色,胎紅褐。沿外泥條上有壓印紋二周。
距今約4300—3800年的陜西神木石峁文化遺址出土的陶鬲,夾砂灰陶,陶色亮灰,直口微侈,厚圓唇,矮領豎直,有雞冠狀器鋬。飾豎向繩紋袋足自領下鼓出,袋狀三足合于襠部,襠部有較為明顯的瘤狀下凸。
距今4300—3900年的山西臨汾陶寺文化陶鬲特點高領雙鋬鬲,器表飾繩紋,領根有凹弦紋一周。隨著陶鬲的演變發展,陶寺中晚期,鬲已逐漸取代釜灶及斝,成為最主要的炊具。而后,單耳鬲、雙鋬鬲傳播到豫陜晉交界地帶和關中地區,同時向北傳至陜北、內蒙古地區和燕山南麓。鄭州洛陽一帶出土的陶鬲從形制上為陶鬲的發展晚期,袋足較小接近消失(王思園:《鄭洛地區東周墓葬出土飲食器具的考古學研究》)。另外,陶寺文化中期時“無領平唇鬲”就已經作為鬲模使用了,但由于工序復雜、操作難度高,最終被淘汰。
距今3800—3500年的二里頭文化時期,不少陶鬲在形制上與鼎較為接近,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中原大地正處于文化傳播交融的鼎盛期,這一時期鼎的興起與鬲的發展均是二里頭文化與周邊文化相互影響、兼容并蓄的結果。湖南寧鄉炭河里古城出土的楚式鬲,形制上是在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基礎上融合南方的鼎而形成的。另外,晚商至周初時期,在江西西北部、湖北東南部、湖南中北部出現的不同于中原地區的陶鬲,也被當成楚式鬲的前身。可見周時期陶鬲的使用范圍極廣,成為先民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劉俊男、易桂花:《湖南寧鄉炭河里古城出土陶鬲研究》)。
商周時期,陶鬲繼續流行,陶鬲在設計和功能上也不斷完善,并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生活器具。其原因在于:商周時期,奴隸制從發展達到鼎盛階段,商業的萌芽及發展加快陶鬲的傳播,頻繁的征戰促進了各族文化的融合及遷徙。商殷時代陶鬲的主要特點是空足與壁厚。同時,陶鬲也開始具備一定的裝飾性和象征性。曾廣泛存在于以黃河中游地區為核心的空間范圍之內,并隨著時代的推移而影響更為廣泛。另外,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發明與使用,在商早期的銅鬲,其形狀、用途與陶鬲基本相同。商朝晚期,鬲的三袋足逐漸退化,到了西周時期陶鬲高領短足,常有附耳。
春秋時期,由于鐵制炊具的普及和灶臺的廣泛使用,陶鬲的實用性逐漸降低,中原地區陶鬲逐漸走向衰落。戰國早期,隨著灶臺的普及,陶鬲的袋足完全退化,最終演變為鍋釜,也就是“破釜沉舟”的“釜”,陶鬲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隨著古人制造工藝的進步,青銅器的逐漸發展,陶鬲在材質和工藝上較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易碎、不耐高溫等缺點,這些都限制了陶鬲的延續,陶鬲逐漸被其他炊具所取代,最終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在陶鬲消亡后,釜形器取代三足器成為主要的炊器之一。
總之,陶鬲的演變充分體現了東、南、西、北等各方文化,既是兼容并蓄、揚棄創新的過程,也是社會凝聚力、組織力匯集的過程,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
陶鬲與中國早期禮制
文化的構建
陶鬲除作為炊具外,也可作為禮器和祭器,一些精心制作的陶鬲被用作祭祀或禮儀活動中的禮器,彰顯了王權政治的中心化、集權化、凝聚力。
《爾雅義疏》釋器說:鼎絕大謂之鼐,圓圜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孫詒讓《周禮正義》云:“鬲,形制與鼎同,但以空足為異。”《夢溪筆談》中提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而《漢書·郊祀志》則說,鬲就是空足鼎。由此可見,陶鬲演化過程中逐漸變成鼎,成為敬之廟堂、象征權力的禮器。鬲和鼎很可能源自同一源頭,但由于用途不同,器形逐漸分化。
鼎與鬲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兩種器物都是人們在祭祀、炊煮場合經常使用的器物,鬲、鼎二者在功用上也有交叉(陳劍:《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青銅鬲有自命為鼎者(《集成》:1981年寶雞紙坊頭M1出土的鬲,自名旅鼎),在青銅器銘文中,鼎鬲二名往往混用,鼎可稱之為鬲,鬲也可稱之為鼎。可見鼎與鬲的關聯十分密切。“古代鼎和鬲實際不很分,其分得清楚的大概在西周后期”(故宮博物院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出土于山西、河南、陜西、甘肅、河北地區的鬲形鼎,是鼎與鬲融合發展的結果,其流行于春秋戰國時期,與鬲的消失時間較為接近。鬲形鼎盛行,或許可以說明鬲在戰國時期數量減少的原因。另外,鬲形鼎最初是較高等級的貴族階級的專屬,逐漸向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蔓延,體現了鬲形鼎的使用范圍逐漸擴大。鬲形鼎主要分布于晉文化區域,鬲形鼎也是晉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焦雪倩:《東周青銅鬲形鼎探析》)。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鬲,雖然尚未形成完整的禮制文化體系,但其作為炊具的實用性和便利性,已經為中國早期禮制的萌芽奠定了基礎。在商周時期,陶鬲不僅作為實用的炊具存在,更成了禮制文化的重要載體。禮制文化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和完善。《周禮》《儀禮》《禮記》儒家經典的出現,標志著禮制文化體系的初步形成。
陶鬲作為禮制文化中的重要名物,其制造和使用也逐漸受到了禮制的規范和影響。在祭祀、喪葬、宴饗等諸項禮儀中,陶鬲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形狀、大小、紋飾等都需要嚴格遵循禮制的規定,彰明君子之德,彰顯尊卑長幼身份,體現貴族君子的威儀。在祭祀活動中,陶鬲的器形和紋飾往往與祭祀對象相關,以表達對祖先或神靈的敬意和祈求。
殷墟大司空村M57出土陶鬲,小型,器高不足10厘米,明顯不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是祭祀時專用的禮器。殷墟文化時期,禮樂制度不斷發展,至殷墟文化第四期,祭祀專用的容器需求增加,加上人口不斷增加,殷墟的制陶作坊要制造生活、禮儀兩方面的大量陶器(黃川田修:《殷墟陶鬲制法考——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陶鬲為中心》)。
龍山時代的陶鬲只作炊器,用作明器、祭器和禮器的還不多見。到了商周時期,陶鬲這種平民階層的實用器物也進入了貴族的視野。陶鬲的地位和作用急劇上升,成為禮器,王者、貴族將其鑄成精美的銅鬲,大小有序,生前享用或賞賜于王室成員、首領和有功部將,死后隨葬。平民百姓則用陶鬲作炊器,死后用以隨葬,并有一定組合,成為商周時期禮制和葬俗。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東周時期(高天麟:《黃河流域龍山時代陶鬲研究》)。在陶鬲的基礎上結合青銅器的特征出現了象征禮樂文化的青銅鬲,這種禮器在西周后期開始大量出現。青銅鬲又反過來影響了陶鬲。春秋以后,仿銅陶鬲這一特殊的器型逐漸取代普通的陶鬲,為陶鬲賦予了政治意義。不過,實用性的陶鬲此時還未完全消失,這一時期兼有實用性和禮儀性兩種特征(紀媛:《隴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至戰國陶鬲調查與研究》)。
夏代中原地區最發達的是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的炊器以陶罐和陶鼎為主。陶鬲雖然不是二里頭文化的主要炊器,卻在二里頭文化的地區繁育成長,鬲文化成為后來相繼崛起的商文化和周文化最強勢的文化因素,并伴隨商文化的擴張和西周的分封制,傳布到了更廣大的地區,與當地文化融合并發展起來(單霽翔:《陶鬲譜系——舌尖上炊器的研究成果》)。
西周時期存在的“列鬲”制度,與“列鼎”和“列簋”制度不同,鬲的數量基本相同。表明鬲在西周時期的禮制文化中地位是與其他禮器并列。“列鬲”制度體現了早期社會禮制文化的演變,不同于“列鼎”和“列簋”的遞減趨勢,“列鬲”是一種獨立對等禮器,在西周時期鬲作為一種獨特的禮器,具備特殊意義。西周時期,“列鬲”制度的形成使得鬲被大量用于墓葬禮儀,體現了鬲的獨立地位及古人逐漸對平等的儀式的追求(魏文闖、萬芬芬:《青銅鬲的婉轉華章——從炊器到禮器、媵器的歷史演變》)。
中國早期社會,禮制被用以維護宗法制度和國家治理的手段,形成禮治模式,同時鬲也被賦予了禮制獨特的含義。目前出土的少數青銅鬲刻有銘文,內容多為受賜或祭祀。鬲作為葬器時常成組出現,每組的鬲形制、大小、紋飾、銘文均相同。出土的西周時期的鬲最多的一組有10個。到春秋戰國以后漸成制度,鬲往往以偶數組合與列鼎同墓隨葬,比如2鬲或4鬲陪5鼎是一個常用的組合。西周后期,周王室衰落,社會秩序動蕩,鬲的禮制功能減弱,開始作為媵器使用。
陶鬲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物質載體,也是連接古今的橋梁和紐帶。其發展歷史軌跡從起源到消失,充滿了變革與創新。鬲與鼎的演變兼容,離不開禮制文化的影響,存在2000余年的鬲,不僅是“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的象征,也是古代中國禮制文化的具體表現。隨著禮制文化的發展,陶鬲的實用功能逐漸弱化,轉而對構建中國早期王權秩序起到獨特的作用。
(作者單位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