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一位經濟學家和一滴水的力量

經濟學家很少像在2024年這樣被需要。
這是備受經濟問題困擾的一年,金錢、房子、股票每天都在被廣泛地談論。
但世人向來沒有那么關注經濟學家。一個原因是,人們認為經濟學家研究的課題“不接地氣”,晦澀難懂—普通人習慣了埋頭賺錢,經濟的大問題就交給那些聰明人吧。
而當勞動的獲得感消失,當日子突然陷入阻塞,人們迫切地希望用某種理性的秩序來理解所處的世界,迫切地希望有確切的答案來消解環境的不確定性:為什么收入不增長了?為什么房價下跌了?就業會好起來嗎?
在這種急迫的期待中,有一群經濟學家出現了。張斌便是其中一位,他低調,不是經常拋頭露面的學者。
過去20多年,張斌做宏觀經濟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朝九晚五地“上班”。他總是關注當下的經濟問題,以至于在系統性的著書立說上顯得有些懶散,很多一同入行的人在他這個年紀已經有了好幾本著作,而張斌直到4年前才出版第一本書。
2024年,有兩件特別的事在張斌的生活里掀起了漣漪。
或許因為研究領域切中當下需求,他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參與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同時,他的第二本書出版了,出版社開始頻繁邀請他與公眾交流。
“經濟學家貢獻的是一滴水的力量。”張斌說。2024年的經驗告訴他,在經濟問題上,人們需要更多的共識,這樣才能推動政策的制定,解救自身于困境。
違背直覺的宏觀經濟
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無法改變現實世界,即便舉世聞名如凱恩斯、李嘉圖,他們也從未指揮過千軍萬馬,從未掌握過生殺大權,也幾乎沒有參與過歷史的決策。
思想才是經濟學家的陣地。思想撼動不了一草一木,卻能建構和改變人類的知識體系:異端可能是常識,而常識可能是迷信。
2024年12月初的北京,我在社科院大樓的辦公室內見到張斌,他現在是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冶研究所的副所長。張斌待人十分平和,和很多經濟學家一樣,他們習慣講述“抽象”,不愛談論自己。
見面沒多久,張斌告訴我,宏觀經濟有許多違背人性直覺的東西。
他打了一個簡單的比方,人們普遍不喜歡通貨膨脹,物價高了,生活壓力便會增大。但在一些時候,適當的通脹是有好處的,物價水平過低,會對企業盈利還有未來預期造成負面影響,社會反而會承受更大的損失。
生活當中固然有智慧,但一些問題的答案僅憑日常經驗永遠也無法抵達,解謎的過程還需依靠數學工具與演繹,更重要的,還有宏觀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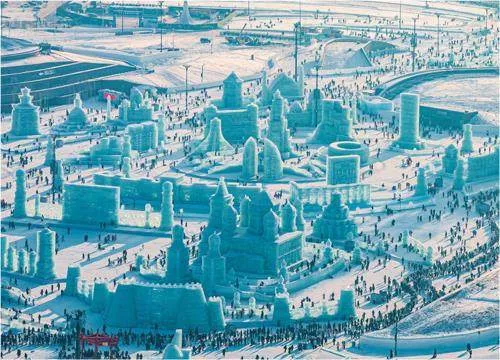
宏觀經濟學者站在系統的角度思考問題,這導致專家的意見時常引發網友爭論,其中不乏大量的負面評價。與此同時,一些迎合社會情緒的觀點廣受歡迎,事實上卻并不可靠。
張斌說,這意味著更多的對話是需要的。
抽去那些復雜的模型與推演,宏觀經濟里仍然存在基本的理念,或者說道理,可以逐漸被公眾觸及、理解。當它們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認知時,就能促進改變的發生。
現代經濟學誕生于一個人人逐利的社會組織,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絕非全知全能,所有人的理性疊加起來,未必會通往理性的結局。
2024年11月,張斌與陸銘共同錄制了一期播客,主題是“需求不足”。張斌關注這一問題已有多年,他在播客中提到,無論誘因為何,需求不足的現象出現后,就會變為一個獨立且棘手的問題。
他用“房間里的三個人”舉例。一個房間里有A、B、C三個人,每個人的支出構成其他兩個人的收入來源,三人相互形成一個經濟循環。當A突然減少支出,即便B和C原本的行為不變,他們的收入也會降低,故而也會減少支出,繼續導致A的收入下降。由此,A、B、C三者的收入和支出陷入了螺旋式下降的困境。
個體的理性行為累加為惡性的結果,市場就失靈了。
當前,總需求不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壓力。就像人們急切地想從經濟學家身上得到關于財富的答案,張斌也急切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需求不足這一現象本身:卷入其中,無法打破僵局,只有當外部力量大于負向螺旋的力量,才能扭轉趨勢。
面對現實,回應關切
就業、收入、企業盈利、膨脹系數,是宏觀經濟主要關注的變量。宏觀經濟學家平常的工作,就是弄明白這些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
“(宏觀經濟)遵循一般的科學范式,先從假設開始,然后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演繹,演繹之后還要證明。整套做完了,結論才能夠成立。”
這個過程聽起來容易,做起來不簡單。
宏觀經濟研究的第一步是,描述事實。但現實的表面總是混亂無序,迷障無處不在。
中國人到底有沒有錢?張斌說,如果從銀行存款來看,中國人很有錢。但“錢”不等于存款,還有股票、債券、養老保險等金融資產,把這些合計起來,中國人的錢在國際上就不顯得多了;用人均家庭金融資產除以人均GDP所得的數字,橫向對比起來也不算高。
張斌看待經濟問題獨立、謹慎,具體表現為,他不是任何經濟學家的擁躉。如果要問受到誰的影響最深,他會答,每位經濟學家都有自己的風格,想理解市場經濟的人,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定有收獲;約翰·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雖然過于抽象,但邏輯演繹精彩絕倫。就像聽歌,好聽就足夠,張斌不為任何歌手停留。
從2003年開始,張斌進入社科院工作,從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人民幣匯率和外匯管理政策等問題的研究。
與高校相比,社科院學者研究的問題更加“實際”,他們要關心現實問題,回應社會與政府的關切。研究宏觀經濟無法幫助個體致富,也左右不了企業的投資決策,如果說,張斌的研究有一個終極的目的,那便是為更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服務。
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在許多時候是隱蔽的,因為它主要解決的問題是減少經濟波動。當正確的經濟政策實施時,生活維持原本的風平浪靜,人們并不能感受到它的影響;不過一旦決策錯誤,就可能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研究大蕭條的經濟學者并不認為經濟要為此付出百業凋敝、1/4勞動者失去工作的代價。資產泡沫破滅、價格下跌、銀行破產、結構矛盾這些問題并不新鮮,出現大蕭條更主要是因為錯誤的政策應對。”張斌在他的書中寫道。
那個時代的管理者對逆周期調控毫無經驗,當時還沒有出現凱恩斯主義,美聯儲憑借舊有的理念,選擇了一系列緊縮政策。錯誤的政策加劇了大蕭條引發的傷害,人們饑腸轆轆、企業倒閉破產,社會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沒有正確思想的指引,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猶如暗夜行走。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大不同,就在于人的行為充滿復雜性與多變性,所有的預測、計算與解釋只是參考,正確的經濟政策通常是不斷試錯后的結果。包括經濟學家本身,也會對同一個問題爭論不休。
分歧、爭辯,經濟學家的動力
張斌最初研究的是人民幣匯率和外匯管理政策。當時有說法認為,人民幣不能升值,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升值后國有企業會破產,中國經濟會遭到重大挑戰。但張斌在研究后得出結論,合理的匯率調整不僅對改善資源配置有所幫助,還可以平衡進出口資本的流動。
分歧與爭辯一直存在,在媒體上喊話,在聊天群辯論,經濟學家免不了口舌之爭。
張斌個性溫和,有人反駁他,他便寫長文章解釋。回應批評,成為了張斌經濟研究的重要動力。“你要去應對批評你的觀點,一條一條給別人做回應。”
匯率問題與國家資源配置息息相關,大約在10年前,隨著研究的深入,張斌的研究方向逐漸過渡到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張斌認為,大約在2012年前后,中國告別了工業化高峰期,此后一直處于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經濟結構轉型進程中。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轉型,往往伴隨著經濟增速的臺階式下降,中國的現實情況確實如此,連續30余年近10%的高速增長后,中國GDP增速在2010年開始下滑。
GDP增速的放緩帶來了一個問題:這是因為潛在經濟增速下跌本身帶來的(意味著經濟不存在過冷或過熱),還是很大程度上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
“中國宏觀經濟在2012年進入從制造到服務的結構轉型期以后,面臨的主要難題是經濟偏冷”,而經濟偏冷的重要原因是需求不足。和張斌的老師余永定一樣,張斌也支持采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速。
總需求不足,主要還得依靠逆周期政策,快速打破負向螺旋循環。經濟學家對自身的定位影響著他們的政策主張。張斌是一位專注于實現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學者,他說:“宏觀經濟學者要做的是在這些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而不是改變約束條件。”結構改革是“遠水”,他要先解決“近渴”,從政策工具入手。
需求不足問題,在2024年吸引了越來越多經濟學家的目光。至于如何破局,學者們觀點紛呈。
2024年9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十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建議。他認為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需求結構直接相關,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不夠,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
滕泰、李稻葵等經濟學家,也圍繞“十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展開了激辯。李稻葵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是兩大周期疊加在一起的結果,中國不需要強刺激,也經受不住強刺激,發行長期國債才是當前問題的解決之道。滕泰在認可刺激計劃的同時,建議擴大內需應集中在擴大居民消費方面,比如以各種方式向居民進行消費補貼。他擔心受到體制慣性的影響,繼續擴大投資會形成新的供給過剩。
相比于拉動消費,擴大投資更接近于張斌的主張。“從歷史經驗看,逆周期政策需要更多投資,”他說,“我現在講的這個觀點,在主流學界是一個小眾觀點。”張斌不贊同效仿發達國家給居民發放現金,相比于投資,消費是一個慢變量,短期內很難改變。
但從生活經驗來看,人有了更多的錢,就會有更多的消費,這是一個頗為直觀的邏輯,為什么不對呢?張斌一邊回答,一邊在白墻上用食指畫著起伏的曲線:“現在之所以消費下降,不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造成,是因為周期性問題,怎么解決周期性問題,就要回到前面三個人的例子里。”
劉世錦對“發錢”這件事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需要厘清需求不足的內因。如今即便是低收入群體也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他們面臨的真正難題,是住房、上學、醫療與養老。在這些問題面前,撒錢無異于杯水車薪。
張斌相信,“爭吵”是有好處的:“我經常對同行朋友說,很多觀點是偏見,朋友也會反駁我說,你講的難道就不是偏見?我有時會辯駁,有時也無言以對……兩種或者多種偏見的打架,可能好過一種偏見的統治。”
在亞當·斯密開啟現代經濟學之前,人類早就開始處理經濟問題了,但幾千年以來,經濟學并沒有出現。人人圍繞著習俗與統治者命令的社會是不會產生經濟學的,經濟學誕生于一個人人以自己利益行事的市場,而這個沒有指令的世界是什么樣的?窮困者和大富翁背后是否存在一套統一的秩序?揭開這個謎團的重擔就落在了經濟學家身上。
而對于研究宏觀經濟的人來說,他們的目的不止于揭示一種哲學,他們密切關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探尋背后貫穿的線索;他們服務于經濟政策的制定,為了更多人的保障與幸福。
若想要改變什么,一滴水、一個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夠的。但如果有更多人的參與、有更多的支持,喧囂總會化為共識,水滴也有穿石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