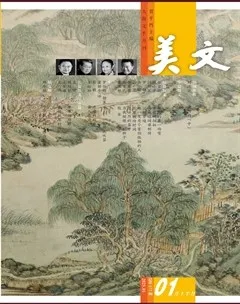江納百瑞
清晨,周老師傅換好工作服,戴上手套,帶著徒弟們從豎井下到平巷,緩緩走進采礦區域,開啟一天的采礦生活。除了工歇,周老師傅和徒弟們要在井下呆上一整天。傍晚,他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居住區,舒舒服服洗個澡,換身衣服,抽袋旱煙,再美美睡上一覺。
日復一日,周老師傅和徒弟們重復著相同的生活。小時候,周老師傅就知道家里周邊都是礦,爺爺和父親、叔叔們起早貪黑出去挖礦,仿佛有取之不竭的礦藏。周老師傅十來歲時,就跟著父親到銅礦當搬運工。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學會了采礦、選礦、冶煉等技術,加上天資聰穎,以至于隨手抓一塊礦石,便可估算出銅的含量,八九不離十。他們先從暴露于地表的礦體入手,再沿礦脈鑿洞,通過特制的方形豎井向下采掘礦石。
前不久,周老師傅飯后散步,無意間瞥見一小排紫色的花。“銅草花!”多年的職業習慣讓周老師傅一個激靈。這個山頭我天天路過,怎么看也不像有銅礦啊。但片片紫紅,穗狀花序,莖干纖細,葉小而圓,確是銅草花無疑。銅草花只生長在含銅的土壤上。周老師傅相信大自然的信號。他馬上喊來徒弟,簡單挖起一塊石頭,放在手中掂了掂。有銅!于是,幾個月后,他的團隊開采完上一個地下采場,就轉移到這片新的區域。
幾年后,周老師傅將技術全部傳給徒弟們,回家頤養天年。偶爾,他也會回到礦山,看看兒子、侄子和徒弟們。實在看不下去,還會自己上手操作幾下,數十年的功夫總讓年輕人嘖嘖贊嘆。
周鑫的父親多次聽自己的祖父說起,家族的祖先曾經在瑞昌挖掘銅礦、冶煉礦石。可是,瑞昌似乎并沒有銅礦的跡象。是在鄰近的湖北銅綠山?還是安徽的銅陵?抑或是代代口口相傳產生了謬誤?周鑫父親的腦海中始終疑惑重重。
這份疑惑一直持續到1988年。因生產需要,九江市銅嶺鋼鐵廠委托瑞昌縣夏畈鄉銅嶺村村民,在銅嶺頭合連山西坡修筑一條公路。在降坡工程中,村民們挖出了大量形狀各異的木頭,有的似木鏟,有的像木棍,還有一些生滿斑斑銹綠,不明何種材料制成的斧、鑿等工具。鋼鐵廠和村委會不敢擅作主張,把部分物件送往縣博物館。經初步鑒定,斧、鑿等工具都是青銅器,與湖北銅綠山出土的青銅生產工具十分相似。隨后,小山村迎來了一批又一批考古學家,貯藏這些器具的遺址逐漸展露真容。
這是一處大型商周采銅遺址。與當時被認為是我國最早采銅遺址的湖北銅綠山相比,還早三百多年。
遺址總面積約三點五平方公里,包含采礦區、選礦區、冶煉區、生活區等功能區域。
始采于商代中期,發展于西周,盛采于春秋,延于戰國,前后連續開采超過一千年。
商代至戰國時期的古豎井一百〇三口,巷道十九條,露采坑七處,工棚六處,選礦場一處,馬頭門、斫木場、圍棚等若干,陶、原始青瓷、銅、木、竹器等生活用具四百六十八件。
冶煉區散布面積十八萬平方米,主要分布在礦山腳下的鄒家、戴家銅石坡、下戴銅石坡、禁地銅石坡等處。發現煉爐六座及大量煉渣,從冶煉區的分布面積及煉渣的堆積厚度估算,古代銅煉渣合計約六七十萬噸。
生活區位于萬家、檀樹咀、銅嶺下,面積合計約三千平方米,發現灰坑、房基、灰溝、木骨泥墻的壓棍印痕燒土等遺跡,出土有商代中期至戰國時期典型陶器等生產生活用具。
遺址中發現的商代木滑車,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早的提升運輸機械,將我國木制機械的歷史提前了一千余年。
銅嶺銅礦遺址發現的西周木溜槽,把有文獻記載的木溜槽選礦技術向前推移了一千多年。
……
銅嶺銅礦遺址的發現,不僅解決了周鑫父親心中的疑惑,他終于可以把家族的傳說講得更加確切。更重要的是,此時妻子恰巧懷孕,他可以底氣十足地把家族的傳說傳承下去。那個古老廣博的礦址,幾乎可以確鑿證明祖先的采礦生涯,證明祖先是領先全球的青銅文化的參與者,證明祖先是這部屬于中國人的青銅文明史詩的見證者。
興許是講得太過投入,周鑫一口氣干了一大杯水。他從記事起,就知道他的祖先把青春和汗水都獻給了銅嶺銅礦。早在三千多年前,銅嶺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采礦、選礦、冶煉、提升、運輸、照明、通風、排水、安全防護及管理系統。其中,巷道支護技術、采礦技術、溜槽選礦技術等,在當時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部分井巷木支護結構在出土后,依然保有良好的抗壓能力。銅嶺銅礦遺址揭示了中國青銅文化的獨立起源,也為中華文明的雙向和多向相互轉播觀念提供了充足的佐證,將中國實證的采銅歷史向前推進了三百余年。當然,同樣也為周鑫先祖采礦的場景提供了鮮活的佐證。
漫步銅嶺銅礦遺址,微風習習,四周草木葳蕤,山坡上隔三差五插著“古井巷口”的牌子。我仿佛看見了三千多年前,周老師傅從方形井筒踩著木支護躬身下礦的過程,看見了一個個技術能手熱火朝天采礦冶煉的場景。山野間點綴的一撮撮銅草花,如同一塊塊胎記,讓銅礦無論隱藏得再深,也一樣無處遁形。走著走著,恰有一塊礦石滾落山腳,拾起,平放手掌上,眾位老師皆驚:“竟然還有銅!”一張張資料圖,講述著挖掘時的盛況。這個中國古礦冶遺址中獲取文物最多的一個地點,與長江對岸的安徽銅陵、湖北銅綠山遺址一道,成為中國工業文明起源于長江流域的最佳佐證。
與古銅礦遺址一同被發現的,還有數量不菲的青銅器皿,上面雕琢的紋飾圖案精美絕倫,鏤空技藝更是高超。實在無法想象,古人如何在條件簡陋的情況下完成這些高水平的創造。但周老師傅和工友們做到了,他們把采礦的技藝、冶煉的技藝和雕刻的技藝緊密結合,把一塊塊質地堅硬、外形不規則的青銅升華為一件件藝術品,讓它們在數千年后重見天日之時,依然熠熠生輝。
第二天的座談會上,來自山西的楊老師說起他們那兒的青銅器特別多,一直不知道是從哪兒來的,直到這兩天到瑞昌,才發現用來鑄造青銅器的礦石有可能源自瑞昌。三千多年前,銅礦石的不斷挖掘,必定遠超瑞昌本地的需求,必定有大量多余的銅礦石被運往全國各地。或許這一段段奇妙的旅程,又是另一大片尚未開啟的秘境。
不知過了多少年,古銅礦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或許是銅的儲量已被采罄,或許是戰亂征伐所迫,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總之,人們不再聚集在銅礦上班,不再以采礦冶煉為生,曾經發生在銅礦的故人舊事也慢慢被歷史遺忘。然而,雕刻的工藝卻頑強留存下來,只是它將對象變成了——紙。無戶不剪紙,無女不繡花,就是瑞昌人民對青銅雕刻工藝的最好紀念。
走進瑞昌剪紙博物館,琳瑯滿目的剪紙作品看得我們眼花繚亂。一會兒是花草樹木,鮮活得仿佛正被微風輕拂。一會兒是鳥獸蟲魚,單首雙身的老虎,滾繡球的獅子,銜花微笑的小狐貍,栩栩如生。兩只戲水的鴛鴦似乎剛剛鬧了別扭。呀!那條魚的魚鱗怎么能如此清爽整潔?一會兒是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平淡,一顰一笑的幸福,任意揮灑在一張薄紙間。一會兒又是童話故事,十只老鼠或高舉“喜”字,或手提燈籠,或吹喇叭,或抬轎子,轎子里的新娘手捧鮮花充滿期待。“老鼠嫁女”的惟妙惟肖,讓人忍俊不禁。粗獷的剪刀,是如何做到在纖細的薄紙上隨心雕琢?一格格細小的鏤空,一條條細密的邊棱,為何能如此工整?“瑞昌剪紙采用陰陽交互、虛實相生的表現手法,并采用‘非鏤空’的反常技法,使作品含蓄而不失典雅,神秘而又深刻。”解說員清脆的嗓音為我們答疑釋惑。
千百年來,剪紙工藝在瑞昌薪火相傳,不斷發揚光大。其構圖之新奇,手法之多樣,藝術之精妙,世所罕見。既有秀麗精巧的陰柔之美,也有豪放堅實的陽剛之美。曾幾何時,南陽鄉每五年舉辦一次“百花帳”活動,選取一百名剪紙手藝高超的未婚女子,用剪紙作為刺繡的紋樣,繡成百花帳,掛在元福主菩薩和鄒氏太婆的生轎上,以紀念剪紙之神。這也是女子的成人禮,巧手善剪的姑娘,很快就有媒婆上門說媒。
2006年,瑞昌剪紙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2008年,瑞昌剪紙被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2018年,瑞昌剪紙被列入國家第一批傳統工藝振興項目名錄。周鑫告訴我,他聽父親說過,剪紙也是他們家族的傳家寶,他的女性長輩們多多少少都會一點剪紙。“有的水平還很高!”他的神情里充滿自豪。
周老師傅沒有什么業余生活,僅有的娛樂,是到不遠的長江邊,瞅瞅廣袤無邊的江水。興致高時,還會釣釣魚,給徒弟們改善伙食。各式各樣的魚,是江水的饋贈。青魚、草魚、鰱魚、鳙魚,沒少出現在他們的餐桌上。吃著吃著,魚與瑞昌人,與瑞昌城融為一體,成了瑞昌最鮮明的符號。
來到長江魚文化館,天降微雨。遠方山巒連綿,厚厚的云層把山壓得低低的,細密的雨滴讓門口的水塘暈開朵朵漣漪。率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根披著地圖的圓柱,長江浩浩湯湯從湖北而來,進入江西的第一站便是瑞昌,在瑞昌留下十九點五公里的美麗岸線。乍一看,位于長江南側的瑞昌像是戴著一頂官帽,帽頂是雄渾的長江干流,下沿象征著十九點五公里的長江岸線,兩旁的“翅膀”一只是洞庭湖,一只是鄱陽湖。瑞昌長江四大家魚原種場的雷明新場長則把這條岸線比作一根挑著兩個筐的扁擔,一筐是洞庭湖,一筐是鄱陽湖。
面對著滿墻鱗次櫛比的珍稀標本,中氣十足的雷場長恨不得把每個標本介紹得淋漓盡致。這只是白豚,智商是長江魚類的冠軍,超過了類人猿,它的聲吶功能連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聲吶技術也無法媲美。就連《聊齋志異》也選擇白豚,化身傾國之貌的美女參與“人魚戀”,被譽為“長江女神”,只可惜2002年已經被宣布功能性滅絕。那只是中華鱘,長江最古老的魚類,一點五億年前與恐龍同處一個時代,它們在海洋里生長,卻非要進入長江產卵。它們從頭年夏天一直游到第二年秋天,兩千四百公里的距離不吃不喝,利用長江水的刺激不斷加速性成熟,消耗掉四百多斤脂肪,方才產卵。后面這條五彩繽紛的魚像涂滿了胭脂,它叫胭脂魚,是一種變色魚,被稱作“亞洲美人魚”,心情好的時候色澤鮮亮,有種“女為悅己者容”的羞澀,心情不好的時候變成渾濁的江水色。還有始終嘴帶微笑的“水中大熊貓”長江江豚,背鰭有如旌旗飄展的旗魚,胸鰭賽過鳥兒翅膀的飛魚,共同訴說著長江的古老歷史。
盡管魚文化館里存有兩百六十六個水生動物活體和模型標本,但這兒的“臺柱子”卻是平凡的青魚、草魚、鰱魚和鳙魚。從唐朝開始,這四種魚類就從周老師傅和兒孫們的餐桌美味,逐漸上升為全國人民的“四大家魚”。
為什么是這四種魚?雷場長用高昂又平緩的語調作出專業詮釋。四大家魚分布于長江、珠江、黃河等水系,其中長江水系最優。它們塊頭比較大,生長周期短,能夠適應不同模式的養殖,產量占全國淡水魚總產量的七成以上。青魚喜食螺蚌類軟體動物,安居于水體底層。游弋于中下層的草魚以水草為食。愛吃浮游動物的鳙魚出沒于中上層。以浮游植物為生的鰱魚則偏愛上層。天然習性的差異,使這四種魚類可以充分利用水體空間和天然餌料,實現和諧共處,因而成為我國水產養殖的“當家魚”。不過,這四大家魚多為洄游式繁殖,需逆水上游刺激性腺產卵,成本不菲。它們的前輩,曾經最早的“當家魚”鯉魚,多為靜置式繁殖,產卵于緩靜多水草處,更適合養殖。只是到李唐時代,“鯉”與“李”同音,人們不敢養鯉、食鯉、賣鯉,鯉魚才不得不讓位于后輩。調皮的四大家魚無法平靜待在狹窄的池塘里,人們只好從長江捕撈魚苗。
我想起剛才進門前見到的弶網。古人把一個小網箱和一個棉麻布制成的漏斗形網系在一起,再綁上一根細長的竹竿支撐網身,稱作“弶”。魚苗從網的大口端游入,順小口端滑進小網箱,人們隔一段時間從小網箱撈舀魚苗,去除雜草,用“篩、擠、撇”等方法初濾野雜魚后,借助碗、桶等工具將魚苗舀入大網箱。肌體強健的四大家魚迅速脫穎而出,充分體現了自然界優勝劣汰的不二法則。試想,密密麻麻的弶網在古瑞昌的長江邊隨風飄蕩,該是何等壯觀。
為什么是瑞昌?長江岸線綿延不絕,為什么由并不起眼的瑞昌,樹起了一座水產養殖的豐碑?雷場長坦言,長江流域每年五至七月進入汛期,水流加速,水溫上升,成熟的四大家魚受水流刺激,完成產卵排精。位于長江干流的產卵場有三十多處,其中宜昌至城陵磯江段的十一個產卵場規模較大,產卵量將近一半。經過五至七天的發育,魚卵隨波逐流到瑞昌江段,恰好破膜出苗。瑞昌段開闊的江面和平緩的水流,以及浮游生物豐富的天然洄水灣,都給這些小精靈們提供了充足的餌料。自然,長江瑞昌段當仁不讓成為四大家魚的主苗場。1958年5月,周恩來總理親臨瑞昌,親眼目睹捕撈魚苗的過程,并對漁民親切說道:“餐桌有魚靠你們!”
原種是人工養殖的芯片。原種是市場供應的源頭。原種事業靠我們。魚卵在長江瑞昌段破膜出苗的動畫展示旁,三排簡短的文字充分說明了瑞昌人民育種護苗的決心。1981年,瑞昌長江親魚原種場成立。1998年,瑞昌長江四大家魚原種場升格為國家級原種場。除四大家魚外,長江瑞昌段還孕育出胭脂魚、大口鯰、鳡魚等上百種特種魚苗。如今,近七億中國人餐桌上的四大家魚魚種,均與瑞昌密切相關。原種調撥遍及全國各地,并遠銷越南、斯里蘭卡等國。
從唐朝起,一代又一代瑞昌人投身水產養殖,不僅僅作為養家糊口的工具,更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呵護魚苗,愛惜魚苗,源源不斷將魚苗輸送到全國各地。因此,分布在長江的四大家魚才能生長速度快,抗病能力強,整體品質好,品質才能遠遠超過黃河、珠江等水系的同類,長江瑞昌段才能成為魚類基因的寶庫和生物多樣性的典型代表,瑞昌人民才能有足夠的自信喊出“世界四大家魚看中國,中國四大家魚看長江,長江四大家魚看瑞昌”。勤奮、堅韌的瑞昌漁民,在長江畔樹起了一座水產養殖的豐碑!
回到披著地圖的圓柱旁,我方覺得雷場長的比喻更加貼切。瑞昌恰似挑著扁擔的漢子,一頭連著魚苗和種質資源,一頭連著老百姓的“菜籃子”,從一千三百多年前昂首闊步向我們走來。
保護種質資源,既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更是從根本上保護長江。長江大保護,自古就印刻在瑞昌人的心里。周老師傅們世代生活在長江邊,水渠、水塘、溪流隨處可見,始終對水充滿敬畏。他們知道人都是逐水而居的,水是生命的源泉。面對一條小河、一泓清泉、一脈小溪、一汪碧潭,他們絕不僅僅把它們看作一個個單純的物,而是一具具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幽遠本源的存在。他們利用卻不過分攫取,享受卻小心呵護。他們投之以真情實感——不能對著江河說臟話,不能在水邊大小便,不能往水里亂扔垃圾,不能向江河吐痰,不能把用過的水傾倒回河里,不能戕害水邊的花草和動物。這些從未形成文字的規則,一直傳承到周鑫和廣大瑞昌市民身上。故而千百年來,春夏秋冬,作為長江入贛門戶的瑞昌,境內的長江干流和支脈們清流蕩漾,淙淙不息。
車行駛到長江邊。江上云霧彌漫,水汽氤氳,有如人間仙境。在江西省新江洲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我們既回味了原國營江州造船廠曾經的輝煌,也見證了新型制船工藝的智能化。碼頭工業城內,一艘艘貨輪靠岸待發,工人們正汗流浹背忙碌作業,各式各樣的產品又將運往江浙地區。如今,實現“多式聯運”的瑞昌港區已經成為江西重要的貨運中轉站,一大批貨物原料在這里完成中轉。來到瑞昌港區的船員們還有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打開微信小程序“船E行”,對著接收設備的屏幕掃碼,確認船上的污水和垃圾成功交付岸上。
曾經有段時間,由于經濟的粗放式發展,導致長江水質受到污染,四大家魚數量一度下降。瑞昌也遍布“小、散、低”碼頭,非法采砂船頻繁進出,造成水質持續惡化,生態功能不斷退化。好在人們及時醒悟,圍繞江中、江岸、江堤、水體、水系、山體、運輸、企業等源頭,開展系列專項整治,十個沿線砂場、四十一條“三無”涉砂船舶全部清理完畢,二十九座碼頭三十三個泊位被拆除。如今,更是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廣船舶水污染物“船上儲存、交岸接收”模式,實現靠港船舶污染物零排放,從根本上解決了船舶污染物問題。
待到雨停,我們下車行至堤岸。云霧漸開,水天一色。江面巨輪林立,穿梭不息。“在長江上隨意切一個斷面,便可捕撈一百七十多種魚。”雷場長鏗鏘的話語依然在耳邊盤桓。我仿佛看見數不清的魚兒正在江水里歡快嬉戲,不時吐出點點水花。突然,水面浮出一個半圓弧形,隨著江水起起伏伏。“江豚!”“江豚!”同行的老師們紛紛叫嚷。得益于長江“十年禁漁”等生態保護措施,長江江豚的種群數量增至一千二百多頭,江豚“攜子進城”的畫面頻頻出現,遇見江豚已經不是一件低概率的事情。我清晰記得,2020年1月1日0時起,江西全省在水生生物保護區和長江干流江西段全面禁止天然漁業資源生產性捕撈。按照國家規定,原本鄱陽湖區域從2021年1月1日0時起全面禁捕,但鑒于該區域七成以上水域屬于保護區,為此江西在時間節點上統一到2020年1月1日全面禁捕,魚類、甲殼類、貝類、藻類等天然水生經濟動植物迎來了休養生息的寶貴機遇。在我們看不見的江水深處,一大批生態系統保護修復的重大工程投入運行,重點物種的產卵場、索餌場、越冬場和洄游通道等關鍵區域的保障持續得到強化。根據中國水科院開展的禁漁效果評估和生物完整性指數評價結果,長江干流和鄱陽湖、洞庭湖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數由禁漁前最差的“無魚”提升了兩個等級。
沿岸線步行,輕風拂面,綠意蔥蘢。走到一個拐角處,紅紅綠綠的指示牌指向不同的方向,上面寫著“江風漁火濱江畫廊”“詩畫長江”“等風也等你”“滿船漁火”等字樣,讓人浮想聯翩。前方,幾名身著白襯衫的人員在堤岸取水。原來,他們是九江生態環境監測中心的工作人員,正在例行取樣,對長江干流水質進行監測,為水環境安全提供支撐。“每月上旬,我們都會開展例行監測,已經堅持了十多年。”一個靦腆的小伙子輕聲向我們介紹,“截至2023年,九江長江干流十個段面已經連續六年穩定保持Ⅱ類水質。”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我們的內心充滿崇敬。
往西幾公里,是位于贛鄂省界的長江一級支流龍港河洋港鎮斷面,這個國控斷面的水質常年可達Ⅱ類標準。今年年初,江西與湖北兩省成功簽訂首期長江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規定近三年兩省每年分別出資一億元,設立長江流域鄂贛段橫向生態保護補償資金,標準就是洋港鎮斷面和長江干流跨省界中官鋪斷面的水質狀況。通過監測月均水質類別,測算全年補償資金,推動保護責任共擔,處置措施共商,跨界執法聯動。洋港鎮斷面上游幾公里,就是湖北省陽新縣。江對岸,則是湖北省武穴市。多年來,兩省人民攜手同行,共同保護近在咫尺的長江水質。這份協議對于兩省人民來說,不啻于一份最好的褒獎。
前方的岸線一眼望不到邊。瑞昌十九點五公里的長江岸線,只是整個九江一百五十二公里長江岸線的一部分。早就聽說“水美、岸美、產業美、環境美”的長江最美岸線已經成為九江的亮麗名片,今日一見,名不虛傳。眺望遠方,矗立在江邊的琵琶亭依稀可見。“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從長安貶謫到江州任司馬的白居易觸景生情,寫下膾炙人口的長詩《琵琶行》。千百年來,琵琶亭歷經廢興,屢毀屢建。1988年,九江市開始在原址下游五公里重建琵琶亭。但受制于周邊混亂不堪的碼頭,琵琶亭占地狹小,重建工作一度進展緩慢。長江岸線整治行動開展后,琵琶亭周邊九座非法碼頭先后被拆除。而今,重建后的琵琶亭景區占地面積擴大了十倍,還進行了聲光電數字技術改造。走進琵琶亭內,視聽演藝燈光秀會迅速把游客包圍。亦可登上潯陽江畔那艘白居易曾經乘過的古船,沉浸在古江州的夢幻夜色之中。坐在船上的木桌前,還能與白居易月下對酌,同作琵琶詩、共賞琵琶曲。若干年后,是否在瑞昌,能夠見到古人制弶網、撈魚苗的火熱場景?是否在銅嶺銅礦遺址,周鑫能與他的祖先周老師傅,也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離開瑞昌時,我想起了長江魚文化館門口懸掛的一張圖片。下半部分是巨浪滾滾,幾條大魚在浪花中嬉戲,上半部分是藍天白云,印有三個大字:魚,水,人。下有一排解釋:水孕萬物,相互交融,和諧共生。這不正是瑞昌的地理特征嗎?這不正是“祥瑞昌盛”的初衷嗎?這不正是瑞昌千百年來的發展脈絡嗎?這不正是瑞昌當下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生動寫照嗎?水是萬物之源,有了長江的滋養,采礦冶煉、青銅器皿、剪紙工藝、種質資源保護的文明之光才能持續閃耀,經久不衰。
長江歡,百瑞興。
(責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