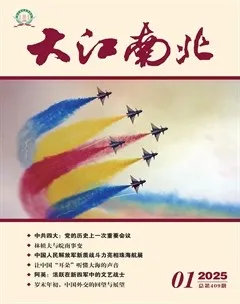中共四大:黨的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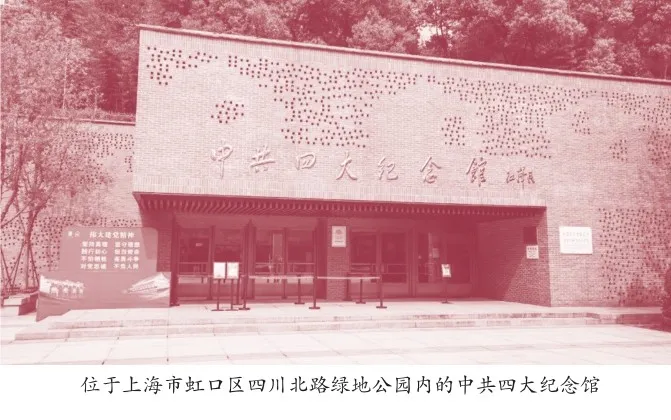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市虹口區東寶興路廣吉里254弄28支弄8號召開(會址已毀于戰火)。作為黨的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黨的四大就革命理論、組織建設以及群眾性政黨建設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在黨的理論探索史、革命奮斗史和自身建設史上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在紀念黨的四大召開百年之際,我們謹以此文嘗試作一番回顧和探討。
黨的四大召開前的形勢和會議召開情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決議。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但是,國共合作并非一帆風順,在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國民黨內的右派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于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在這場日益高漲的大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中國工人、農民以及青年,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組織群眾?
中共四大正是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而召開的。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王荷波、項英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彭述之作了關于共產國際五大的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報告;維經斯基作了關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各地代表分別報告了本地區情況。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并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黨的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第一次明確了工農聯盟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對于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掀起革命高潮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
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基本問題。盡管黨自誕生以來對革命的認識不斷提升,但對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與工農聯盟等問題的認識仍不夠深入。國共合作形成后,隨著黨獨立領導革命意識的增長,必然會引發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沖突。因此,如何在紛繁復雜的革命形勢中保持黨在思想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進而實現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對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的挑戰,也為中共四大解決革命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增加了緊迫性。
中共四大在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的闡釋與實現途徑,集中體現在下列幾點:第一,明確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中心和領導地位。大會指出:中國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既“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因此對于這場革命,無產階級“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會議提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明確無產階級應該參加革命并獲得領導權,這是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的重要闡述和明確論斷。第二,在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上作了初步回答:工人階級自身必須有穩固的組織和工作保障,并且不斷參加革命活動;黨必須盡可能地引導農民不斷參與革命斗爭,保障農民的核心利益;必須爭取與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此外,大會還提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表明黨對反封建的內涵有了進一步認識。
中共四大就工農聯盟問題也進行了深入探索。大會肯定農民是工人的同盟者,首次明確提出建立工農聯盟問題。《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指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階級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尤其是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農民問題特別重要。大會強調: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其中農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大會指出,在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中,更需要工農階級的共同努力,才能夠保障革命的勝利。會議對于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與無產階級的親密關系的認識,無疑比較以往更進一大步。
中共四大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問題與工農聯盟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深化了黨對自身和革命的認識,是黨在革命理論探索上的重大突破和重要創新。
推動國民革命向前發展
黨的四大的召開,提升了黨對革命性質的認識,強化了黨對各階層的了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共四大會議相關議決案及其精神的指引下,迎來了以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為主要內容的革命實踐。這些革命實踐使得革命漸成燎原之勢,也深化了黨對革命的認識。
從中共一大黨綱指出采用階級專政的手段,到中共二大的最高、最低綱領的制定,再到中共三大進一步提出“國民革命”的口號,彰顯了黨在革命性質認識上的進步。盡管這些探討和思考仍有局限性,但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對革命規律的深刻把握和理解,為中共四大深刻地分析和探討中國革命澆筑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會議通過對中國革命特征、革命前途等方面在內的革命性質進行詳細闡釋和探討,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進步與發展,乃至革命浪潮的興起具有突破性作用。會議認為,當前各國革命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歐美國家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在十月革命發生后都是世界性的,這兩種革命的匯合才能夠推動世界革命前進。會議鮮明指出,中國的革命屬于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四大對中國革命特征的描述,肯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具有革命性、階級性和世界性的重要特征。
在革命的內容上,會議指出,中國民族革命是繼續或完成辛亥革命,是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的革命;在中國革命的前途上,會議指出:“民族革命勝利后,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必得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定之,那時的世界政治狀況也有很大的影響。”這些認識,為黨在會后進一步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論基礎,使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漸趨深化。
會議還決定加強《向導》 《新青年》 《中國工人》等刊物的工作,以及設立黨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等,使其成為運用馬列主義理論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重要宣傳陣地。
指導黨逐漸發展成為真正的群眾性政黨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共四大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完善黨的組織結構,壯大黨的隊伍的同時,也推動黨從一個宣傳性政治小團體轉變成為真正的群眾性政黨。
中共四大立足革命形勢的發展,就組織建設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設性舉措。一是提出設立黨支部,強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為了增強黨的基礎,便于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中共四大將黨的基層組織由“小組”改為“支部”。在對支部建設進行總體闡釋時,會議還就支部的設置標準與形式、設置原則、職能等重要方面予以闡述。二是強化中央機關建設,明確中央權威,增強黨中央的領導能力。中共四大修改黨章,改“委員長”為“總書記”,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互推總書記一人總理全國黨務”,各級執行委員會及干事會互推書記一人總理各級黨務,其余委員協同總書記或各級書記分掌黨務。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將“總書記”確立為中央委員會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并明確其職責。三是嚴肅組織紀律,加強黨員教育。在波譎云詭的形勢下,嚴明的組織紀律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保障。會議指出:“各黨員對外發表之一切政治言論,尤其是在國民黨中發表之一切政治言論,完全應受黨的各級執行機關之指揮和檢查。”在四大會議精神的影響下,1926年8月4日,中央擴大會議發出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旗幟鮮明的反腐敗的制度性文件,也是首個對貪污腐敗分子明確進行懲處的文件,對于加強黨務工作,嚴明組織紀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四大對群眾路線問題也作出了有益探索。群眾路線對于中國共產黨建設群眾性大黨極其重要,是把黨逐步群眾化的關鍵。中共四大所頒行的一系列議決案,是黨對組織建設的深入探索,深刻闡發了黨的群眾路線。一是強化黨對群眾來源的認識,拓展黨的群眾空間。會議指出,要糾正那種主張不與黃色工會的群眾發生關系的弊病,才能將無黨派的大多數工人群眾集合到共產主義旗幟之下來。二是有效搭建實踐平臺,為實行群眾路線創造有利條件。隨著國共合作的逐漸穩固,黨借助國共合作所搭建的實踐平臺,積極投身群眾工作,使得群眾工作有所改觀。四大會議召開后,以毛澤東、澎湃、羅綺園、阮嘯仙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先后主持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為革命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干。
綜上所述,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會議總結了黨成立以來特別是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重新審定國共合作以來的政策和策略,表明黨在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為隨后出現的革命新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雖然大會對于怎樣取得領導權、怎樣實現工農聯盟的問題,尚沒有具體、明確的主張,也沒有認識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革命武裝和革命政權的重要性。但四大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提升了黨對革命的認識,開創了黨的組織建設和群眾路線探索的新階段,對于如何加強自身建設,鞏固工農聯盟,從而奪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以及最終奪取革命的偉大勝利等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作者王佩軍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區委黨史辦原主任,徐雪琛系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韋博系西華師大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編輯 易化 韋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