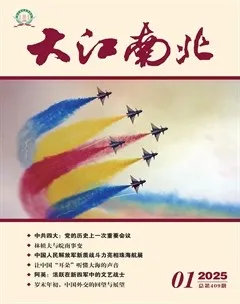我在和含被服廠的戰斗歲月
1943年2月,隨著和(縣)含(山)抗日根據地的鞏固,軍工生產也得到發展,對保障部隊和地方的軍需民用發揮了重大作用。
我是1943年春日軍對巢(南)無(為)地區大“掃蕩”時,隨師部教導隊邊戰斗邊轉移到含和支隊的。6月,日軍對和含再次大“掃蕩”。反“掃蕩”勝利后,經一段時間學習,我被分配到支隊供給處被服廠擔任廠長。
和含被服廠規模不大,除請來的裁縫師傅外,初期干部和職工也就十幾人。工人多是當地人,還有六七個女同志,有的是從家里跑出來的“童養媳”,有的是地委和支隊的干部家屬。工人們進廠后即等于參加革命,都有軍籍,享受供給制,是不穿軍裝的戰士,還有極少的津貼費。請來的師傅是定期合同工,拿計件工資。
工廠的條件很差,廠房設在駝塘黃村一所破祠堂里,設備也很簡陋,僅有兩臺圓梭、一臺長梭的舊縫紉機,以及幾臺從南京、蕪湖買來的手工織布機。縫紉工具一般都較輕便,適于肩挑、船裝,以便隨時轉移。
被服廠生產的產品有棉衣、夏衣、雨衣、布襪、綁腿、被單、蚊帳、便衣(老百姓穿的衣服)等,每年的單、棉衣任務為1000多套。女工們主要負責打孔、鎖扣眼、釘扣子、干雜活,以及必要的運輸等任務。每年的生產任務完成后,裁剪師傅與縫衣工人都回家,到需要時再請來。隨著部隊不斷發展、壯大,被服廠的任務也不斷增加,生產方式也隨之轉變,由夏天做單衣改為做冬衣,請來的裁剪、縫衣工人也由定期合同工改為長年合同工,除春節回家過年外,長期在廠做工。
廠里生產所需的細布、蚊帳布、縫衣針、紐扣、染料等材料,均由軍需通過當地“跑單幫”的商人到蕪湖、南京、上海等敵占區采購而來,家織布、土紗、棉花、青麻、毛巾等物資,則多數是向當地商人或巢北的布商購得。如無特殊情況,被服廠不直接購買生產資料(原料)。
由于當時干部和工人都是自愿參加革命的,都有熾熱的愛國熱情和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因此紀律性很強,自覺性和積極性都很高。為進一步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被服廠實行了賞罰分明、超產有獎的制度。干部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任務緊迫時,夜里一起突擊加班,在汽油燈下一直干到深夜。干部還經常與工人在一起做游戲(如畫蘭草),開展文娛活動。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促進了干部與工人、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團結。
關心和改善工人的生活,也是調動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有效方法之一。有時,我們帶領工人到野外、山崗去打野兔野雞等,改善伙食。有時,我們也到地主家的塘里搞魚。廠黨支書記焦恭貞知道后,就告誡我們說,這是違反紀律的,以后不能這樣干。過年時,大家喜氣洋洋,一起動手,弄了幾個菜、一個湯,有說有笑,歡度春節。當時物質條件雖然相當困難,生活也十分艱苦,但干群之間互相關心、親如一家。大家思想樂觀、積極向上,工人在生產中都能吃大苦、耐大勞,每年都能按時或提前完成生產任務,即使在戰斗頻繁的情況下,也能千方百計保證部隊服裝裝備、軍需物資的及時供給。
此外,和含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的無私支援,不僅是被服廠能按質按量完成任務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工廠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當時,被服廠一旦接到日偽軍企圖“掃蕩”我根據地的消息,就立即處于緊急備戰狀態,除動員全廠力量外,還需要當地民伕的協助。只要我們一聲呼喚,不論是白天、夜晚,民伕們召之即來,為工廠包裝設備和物資,并迅速轉移到可靠的群眾家里藏起來。日偽軍離開后,他們又把這些物資設備如數搬出,讓我們馬上恢復生產。
1945年7月,被服廠遷到了無為東鄉湯溝,直到新四軍北撤時才停止生產。這時,工人們根據情況,一部分回家,一部分隨部隊撤走,笨重的機器(如縫紉機等)埋在黑沙洲等地方。
1943年至1945年,兩年多時間,和含支隊供給處被服廠在斗爭十分殘酷、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積極生產,保證了支隊各部隊、各機關軍需服裝及裝備的需要,改善了人民子弟兵的生活條件,為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馬紅南 供稿)(編輯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