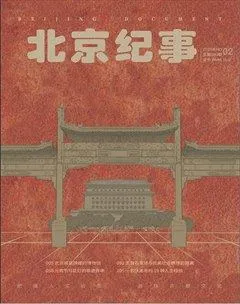臘庫胡同中的貢蠟往事
北京的胡同是最具特色的一景,叫什么名字的都有,在這些獨特的名字背后,都有著其精彩的故事。
臘庫胡同,就是北京眾多的胡同中的一條,它位于北京市東城區景山公園東北側,南北走向,全長426米,寬約4米,北端胡同口僅寬1.5米左右。最初臘庫胡同還是叫蠟庫胡同,明清時期內務府曾在這里設過“蠟庫衙門”,得名就由此而來。
貢蠟照亮皇室的奢華生活
臘庫胡同由來還是很久遠的,最早要追溯到明代。自明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建成了氣勢恢宏、金碧輝煌的紫禁城,這紫禁城皇宮內各色人等的衣食住行都交由內務府各衙門負責。內務府下轄包括磁器庫、緞庫、蠟庫等供應庫衙門。
而蠟庫衙門所在的蠟庫胡同分為南北兩條胡同,習慣上稱為蠟庫南岔北岔。南岔用來收蠟,同時負責制作宮蠟,制成的宮蠟就存放在北岔的庫房,每天按時供應皇城內使用,蠟庫胡同對面的鐵匠營胡同則專門負責制作制蠟的模具。
這個蠟庫衙門聽起來不是多么高大上,其主要是負責宮內的宮蠟供應,沒有這個蠟庫,皇宮內將一片漆黑,所以還是很重要的。鑒于蠟庫的重要性,蠟庫衙門也是二十四衙門之一,共設有總管1人,司書2人,正式工人16人,接蠟兵役及雜役數十人,也成了一些人升遷謀生的好去處。
蠟庫供應皇宮所用的宮蠟,都是由四川和廣東進貢的白蠟以及黃蠟煉制而成。宮蠟,顧名思義是專供宮廷里點燃照明用的蠟燭,所用的原料與香蠟鋪里賣的和寺廟里用的蠟燭不同。一般的蠟燭是用蠟樹籽即烏桕樹籽軋成的蠟油制成的;而宮蠟就不同了,其中白蠟則是用四川省特產的蟲蠟煉制而成的。由于這些蠟產地都在南方,所以每年都需要向朝廷進貢。
地方向朝廷進貢宮蠟制度,從明朝就開始了,清朝沿襲了明代舊制。貢蠟是由四川和廣東兩省向朝廷進貢的,被稱之為“蠟貢”,四川進貢的叫川蠟,即白蠟;廣東進貢的叫粵蠟,俗稱黃蠟。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發生庚子事件后,粵蠟停止生產,貢蠟則全部由四川進貢。
在沒有電的時代,明清皇宮紫禁城內就是靠這些宮蠟照耀著其輝煌奢靡的生活。
貢蠟源自大自然的恩賜
人們只知道使用蠟燭,卻不知道,蠟燭制作步驟繁瑣,源頭要取自蟲蠟所產。當時,制作宮蠟的貢蠟叫蟲蠟,是四川當地的特產,是由一種名叫蠟蟲的昆蟲吐出的液體積累形成的,由此取名蟲蠟。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蠟蟲誕生在四川建昌,蟲卵卻要送到幾百里外四川嘉定的蠟樹上去繁殖養育。所以,在四川蠟蟲與蠟樹是分開的,蠟蟲只有吃了建昌的蠟樹葉子,然后吐出液體,就像春蠶吐絲一樣,才能生成這種優質的蟲蠟。
因為建昌和嘉定兩地相距很遠,為了把蠟蟲運輸過去,就在四川出現了專門販運蠟蟲的販子。每年清明節后,這些蠟蟲販子運載著大批食鹽、紙張、布匹和煙草等建昌地區缺少的物資,到那里換取蠟蟲卵,然后將蟲卵運至嘉定,賣給種植蠟樹的蠟戶,由他們進行繁育養殖。
這種蠟蟲卵嬌貴得很,運輸途中是不能讓蟲卵曬到太陽的,如經太陽一曬,蠟蟲就會破卵而出,途中又沒有蠟樹葉子,沒有蠟樹葉子給幼蟲吃,就會面臨餓死,蠟蟲販子就賒大發了。所以,蟲販子們換得蟲卵后,立即連夜運至嘉定,這樣就不會見到太陽了,比較保險。買到蟲卵后,蠟戶會將其先放置于陰暗處,等到陽光充足了,才將蟲卵分散放在蠟樹葉上。很快蠟蟲就破卵而出,和蠶寶寶出生很相似,蠟蟲出生后長到兩三個月就可以吐蠟了。
蠟蟲吐的蠟會被積累起來,然后蠟戶將其加工提煉成純凈的白蠟,并做成蠟坨,每坨10余斤,裝在特制的木桶內,加上木蓋;也有不用蠟桶包裝的,而是用稻草把五六個蠟坨疊放在一起來包裹,外用木板夾上,再用草繩捆扎,這種包裝被叫做蠟鞘。
這些蠟桶和蠟鞘就是送往北京城的貢蠟,運到碼頭裝船后,再輾轉運到北京。既然是送往京城的貢蠟,地方官員絲毫不敢馬虎,省署衙門派官員隨船押運,以確保萬無一失。當然,也有少數蠟戶自己用手推車運蠟,叫蠟車子,經旱路運至京城。
千里迢迢,一路奔波,貢蠟終于運到了北京。四川省署衙門押運官要先到內務府報到,并呈交所運貢蠟的清冊。然后,內務府通知蠟庫胡同的蠟庫衙門,派兵役接蠟,貢蠟即被裝車運進城里。
貢蠟成為官匪謀私利的工具
即便是派了兵役人員前來接應運蠟,但是運蠟車輛仍不敢單獨進城。要知道,當時北京城內有一伙地痞流氓不簡單,他們被稱為“蠟匪”。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些蠟匪深知貢蠟的價值,也要靠此發財。他們往往提前探聽消息,一旦得知貢蠟運到了京城,他們就派匪徒暗中尾隨,這叫綴車子,又叫跟盤子。
蠟匪搶劫運蠟車輛卻不在郊區動手,偏要等蠟車進城后走到僻靜小巷時,才包圍哄搶。更為奇怪的是,他們搶貢蠟卻不是為了出售,換取錢財,那為啥呢?
原來,蠟庫衙門也是個肥差,蠟庫頭目和匠役們都是靠此發財的。他們知道這個差事油水大,最后都弄成了子孫世襲,俗稱“窩子差使”。
蠟庫頭目和匠役們把此差使當成自己的產業看待,他們靠蠟吃蠟、監守自盜。他們的做法是:經常故意將蠟庫存放的蠟坨打碎,藏在身上帶出賣給藥鋪、顏料店、香蠟鋪和油漆店,中飽私囊,因此個個都富得流油。由于當時庫存蠟坨一向沒有準確數字,入庫時又按對折過秤入賬,即100斤入賬50斤,于是給這伙盜賣者以可乘之機。他們瘋狂盜竊,每天每個人偷蠟不下10余斤。
看到蠟庫頭目和匠役們肥得流油,蠟匪們還能不眼熱,于是他們就成了蠟匪死磕的目標。一旦蠟匪劫到貢蠟,既不出售,也不毀掉,而是向蠟庫頭目等索要贖金;這些蠟庫官役們為了向蠟庫衙門交差,會找到雙方都認識的地痞流氓從中說和,這種事叫“說票”,雙方互提條件,談妥后,由蠟庫官兵和頭目們將贖款交給說票人,說票人再將錢交給蠟匪后,就可以將貢蠟拉回來入庫了事。
既然蠟匪們要搶蠟庫頭目們的油水,蠟庫頭目自然要嚴加防范。為防止貢蠟被搶,蠟庫頭目往往會出大價錢請鏢局的鏢師或武術行家協助接蠟。蠟匪們也不示弱,同樣也請這些人幫忙搶劫,雙方經常發生械斗。當時,廣東貢蠟是經運河運至大通橋進東便門,經前門、西長安街、府右街,進西安門,再入庫;四川貢蠟是進廣安門,經宣武門、西單、西四,進西安門,再入庫。
所以,西安門的皇城根和西四丁字街比較僻靜的那一帶,成了蠟庫官兵和蠟匪爭奪械斗的戰場。可笑的是,在雙方混戰時,即使是附近衙門站崗的官兵眼看事發,不但不前去制止,要么閉門不出,要么退縮不前;路上行人也站在一旁看熱鬧,似乎與這些人毫無關系。等戰斗結束了,官兵們才一個個出來,看看有無傷亡,如果有傷亡,就會報告有關衙門,例行其敷衍之公事。好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清朝廷設立了巡警部以后就很少發生了。
宮蠟的制作堪稱完美
貢蠟入庫后,宮廷就可以制作宮蠟了。明清宮廷所用的宮蠟,其實由來已久。在古代蠟燭是油燈之外另一種重要的照明工具,據《禮記·內則》載,“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可見蠟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
關于蠟燭的起源,據《漂粟手牘》載:“娥皇夜寢,夢升于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驚覺,仍燭也。于是孿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顯然這個記載更早,上溯到了三皇五帝時代。
到了唐宋時期,蠟燭的使用達到高潮。
唐代的宮廷用蠟在制作材料和工藝上就已經十分講究,燃著能飄散出陣陣異香,沁人心脾。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寧王好聲色,有人獻燭百枚……每至夜,延賓妓坐,酒醋作狂,其物則昏昏如所掩,罷則復明矣。”從這段描述來看,蠟燭的使用達到了極致,就像今天的霓虹彩燈一般,有復明復暗、迷離人眼之效果,著實讓人難以想象。
在沒有電燈的唐代,蠟燭照亮了黑夜,許多詩人吟詩作賦稱贊蠟燭的貢獻。詩人杜牧感慨:“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看看,都把蠟燭擬人化了。而詩人李商隱則寫出“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千古名句。
到了清代,制作皇宮所使用的“宮蠟”,工序更是復雜,技術也更加成熟。他們共分為四道工序:第一為熬煉,用直徑為七八尺的大鍋,將蠟坨放入熔化,把蠟中的雜質剔除,達到提純的目的;第二為擺盤,用二三尺見方的木盤,盤上豎立著若干筒形蠟模子,模子中央為空洞,是安裝蠟芯的地方,蠟芯有棉花芯和燈草芯兩種;第三為上模子,將熔化之蠟油,倒在模子內,放在木盤上,待蠟油凝結后,撤去模子,就成為蠟燭;第四為罩紅,用配制好的紅顏色,將蠟燭染成紅色、黃色和五彩色等四種顏色。
宮蠟從造型和花紋上又分有“花蠟”,上面刻有金龍抱柱、富貴滿堂、吉慶有余等花紋,專門供皇帝批閱奏折等使用;白色蠟燭則供帝后大喪時使用;洞房中用的蠟燭還要刻上五彩花紋稱喜蠟,其余各色均在日常生活中點用。宮蠟按大小來分,則有10余種,其中有小雙包、大雙、三燭、四燭、通宵大蠟等。隨著清王朝的結束,真正的宮蠟已經很罕見了,有心人將其收藏,現已成為古董。
說起蠟庫胡同也是赫赫有名,早期青年革命家高君宇曾經住在蠟庫胡同,而且他曾在這里有過一次脫險的經歷,還有他與石評梅的愛情故事;作家楊沫在其小說《青春之歌》中多次寫到蠟庫胡同;解放戰爭平津戰役期間地下黨的電臺就曾設在蠟庫胡同49號。建國后蠟庫胡同才改稱臘庫胡同,現在都成了民居。其實,北京還有與之相近的胡同命名,有一個蠟燭胡同,虎坊橋附近還有一個臘竹胡同。
一切都如過眼煙云,曾幾何時皇宮里明亮如晝的貢蠟悄然消失,僅僅留下了一個臘庫胡同,似乎在提醒人們那段曾經有過的貢蠟造蠟的輝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