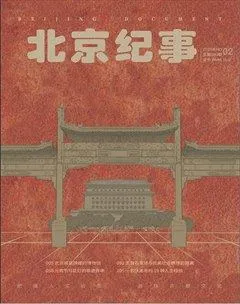變法怪圈:抑兼并與不抑兼并
劉子健先生認為,王安石政策的重點不在于法律的頒布與執行,他也并不將“富國強兵”作為頭等大事。他的最終目的在于改善社會風俗,期盼實現一種完美的社會秩序(“至治之世”)。在我看來,在評判王安石變法時,不僅要看其政策動機,重要的是觀察其政策后果。此外,富國強兵既是宋神宗趙頊既定的變法目標,顯然也是王安石變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而王安石變法,也部分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
變法扭轉了國庫空虛的局面,從中央到地方的府庫都非常充盈。1078年,宋神宗將山海坑冶、榷貸和常平、免役等項獲利都收歸中央,建了32座倉庫儲存。1082年,又將青苗、免役法所獲之利直隸朝廷,又有20庫。此外,地方財政也得到極大充實。
在軍事上,王安石采取了很多措施來增強軍隊戰斗力。宋哲宗親政后,基本掌握了橫山一線的控制權。自此,宋夏之間的戰略態勢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西夏一再上表請罪,愿向北宋俯首稱臣,而宋朝則一舉結束了屈辱、被動的狀態。宋哲宗對此興奮異常,連呼“西人未嘗如此遜順”。游彪認為,宋哲宗時期所取得的勝利,其實來源于宋神宗時期奠定的基礎。
只是,古代君主制的困局,通過宋代及王安石變法也顯露無遺。北宋前期的一百多年在政治上重文抑武,在經濟上“不抑兼并”,到宋神宗趙頊登基之前,三冗二積嚴重。王安石變法部分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后果,卻打破了北宋初期維系一百多年的寬容政治局面,由此拉開了朋黨之爭的序幕。游彪在《問宋》一書強調,對王安石來說,權力只是實現“治天下”理想的手段,而不是滿足個人野心和私利的工具,因此他絕無“權相”嫌疑。但王安石擴張相權的種種策略,卻為以后的權相開啟了方便之門。
在經濟上,王安石的抑兼并,用官營經濟部分取代了商業壟斷,但并未減輕底層民眾的負擔。《傳統十論》中認為,“不抑兼并”的結果是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抑兼并”的結果是“國富民窮”。而“兼并”在本質上并非經濟行為而是權力行為,有權者兼并無權者(包括無權的富民)、權貴兼并平民、統治者兼并所有者。抑兼并則是朝廷用權力限制所有人,官府用國有經濟取代部分民營經濟。而兩難選擇的原因在于,無論朝廷的“公權力”,還是貴家勢要的“私權力”,都不讓規則公平,更不讓起點公平,“與民爭利”。如今回看王安石變法意識到,要想跳出歷史怪圈,維系健康的市場經濟,就必須嚴格限制強勢者的權力,以法治來保證規則的公平、起點的公平和過程的公正。
如果以劉子健先生所說,王安石企圖通過變法改善社會風俗,期盼實現一種完美的社會秩序,這一目標并未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