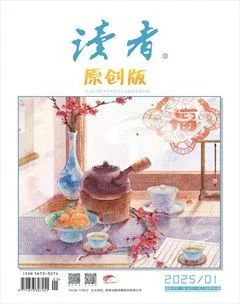和媽媽一起遠游
一
剛見面就出了狀況,在人頭攢動的米蘭大廣場上,我居然找不到我媽了!如果說還有什么比這更糟的,那就是她不會說外語,永遠聽不見來電鈴聲,并且今天還穿了白色的衣服,簡直是隱身在了四周的白色建筑群里!六月的陽光早早地攻陷了波河平原,此刻,站在人群中的我感到頭腦無比昏沉,卻不得不努力伸長脖子,盡力用目光撥開人群尋找她。
這是我們分別一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在此之前我們當然也會打電話、視頻聊天,但時差不容分說地模糊掉了彼此生活中的細節。除了偶爾在網上幫她買買應季蔬果,團購幾張代金券,我不知道她的每一天究竟是如何展開的,心情怎么樣,除了每天轉發給我的那些公眾號文章,她還會讀什么、聽什么、關注什么,我甚至還自以為是地想:如果我不再是她生活的錨點,那她還能忙什么?
無數個應急方案如彈幕般從腦海中快速劃過:找警察?我不會意大利語,他們顯然也不擅長英語。等人潮散去?一隊隊游客不斷地在我面前來來往往。廣播找人?我已經想象到自己被分享在社交平臺上的樣子了:一個中國留學生在和媽媽見面不到一個半小時之后就把她弄丟了!唯一讓我感到安心的是我知道我們之間還有默契—如果她找不到我了,一定會站在原地。
厘清思路以后,我開始小范圍搜索,突然發現,原來她就在我身后不遠處自拍!這也太沒有團隊精神了吧!兩個人結伴出游,一個人卻在忙著自拍!而且我剛才趁著人流松動的間隙,占據了一個絕佳的取景位置!剛才的心情明明還沮喪得像化掉了的意大利冰激凌,正順著手腕滴滴答答地掉落,此刻,怒氣瞬間如咖啡機攪拌起的泡沫,伴隨著刺耳的噪聲不斷地升高。
近乎本能般地,我表現出所有孩子都會有的行為,不容分說地沖著她大喊了一聲:“媽—”千言萬語都在這一聲之中了。
我有什么好指責的呢?我不是總看著她發來的自拍照不由自主地微笑嗎?我不是鼓勵她沒事多下載點兒手機應用程序好好學習學習,多追求進步嗎?現在,她早已對各種自拍角度熟稔于心,能夠輕而易舉地創作視頻,還經常把我隨手分享給她的照片“擦除背景”或者“一鍵美顏”一番。她早已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了新的秩序,并且自得其樂。換句話說,我們都已經習慣了彼此不在身邊陪伴的生活了。
二
當向導說我們要協同合作,劃獨木舟到對岸的時候,我是真的有點兒打怵。盡管是極晝時節,北極圈的風云仍酷酷地際會于斯瓦爾巴群島的上空,風獵獵作響,望著不斷開合涌動的波濤,我把讀過的所有關于波塞冬的神話,一股腦兒全想起來了。
“你,坐在后面。”向導一開腔,就帶著挪威人特有的寒冷氣息。
可是我想坐在前面,因為前面視野好,而且媽媽會主動幫我拍出很多好看的背影照。我甚至不需要跟她商量,直接坐在我想坐的位置上就行了,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可是現在,我被安排到了后面。
“現在我來教你怎么控制方向。”向導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耐心地逐一介紹細節,沉穩、果斷、踏實,這也是此刻他希望我具備的品質。原來,從外部視角來看,我早都是那個需要承擔起全部責任的人了。
一陣手忙腳亂之后,我們總算把獨木舟劃到了中央,我忽然感到這個地理坐標對我來說意義非凡。父母以“北溟”喚我,此刻,59歲的母親陪我來到了真正的“北海”,仿佛某種隱喻一般,這里也正是我精神氣質的原鄉。
眼前,壯闊的景象讓人如此胸襟遼闊,我提議一起背詩。
“行啊,背什么?”我媽問。
“背你喜歡的蘇軾的怎么樣,小舟從此逝,滄海寄余生?”
“不背,真不吉利。”
“從流飄蕩,任意東西?”
“不好。”
“那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顯然這句也不理想,我連忙識趣地閉嘴。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搜腸刮肚了一番,腦海中再能想起來的有關吉祥的意象就只剩《春節序曲》的旋律了。“哎呀,那就背《逍遙游》吧,怎么把這茬兒給忘了!”
于是兩個人總算默契了一回,完全不用排練,聲音一唱一和,順序一來一往,船槳一左一右,蕩舟,蕩舟,讓聲音如飛鳥般迅捷地掠過水面。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
“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我拍了很多張媽媽的背影,襯著我們一起見證的最純凈的天空。拍她和山與水、和花與木、和云靄與煙霞、和鯨與麋鹿、和天地萬物,也拍正在自拍的她。我不知道“看世界”是否也是她的夢想,但我知道,我正在把自己認為最美好的東西一一呈現給她。
三
這一路我們爭吵不斷。
我讓她加一件衣服,她高聲說“不要”。拜托,這里的溫差真的很大啊!她讓我幫她在魯冰花叢中拍張照,卻對成片很不滿意,說我完全沒有審美。開玩笑,好像我對她拍的沒有同樣的感受似的。我讓她幫我錄一段視頻,她說再折騰下去自己就要暈車了。她趁我不注意時偷偷打起了瞌睡,可是租車自駕不就是為了帶她看風景嗎?兩個意志獨立、各有主見的成年人同游,即使血脈相連,也有矛盾調和不了的時候。
吵了一路的嘴,置了一路的氣,離別將至,兩個人的心情卻忽然都像返了潮的調味罐,酸、甜、苦、辣都不再劇烈,無論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差點兒興致。辦好登機牌,退了稅單,托運好行李,站在候機樓巨大的落地窗前,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對時間的無能為力。

每次都要大哭一回,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五官原來真是相連的:剛開始只是鼻酸,然后連忙吞咽,忽然咽也咽不下了,于是所有明明剛才已經被偷偷壓抑下的淚水突然“嘩”一下涌了上來。兩個人哭得耳廓通紅、抽抽搭搭。
雖然我們現在只隔著一道安檢門,我卻急得坐立難安。她倒好,用一條條語音沒完沒了地給我講剛認識的土耳其小妹妹—善良的土耳其小妹妹接受了我的拜托,帶領媽媽一路通關,出了申根區。本以為此行圓滿結束,誰承想飛機竟然晚點了。這意味著不會外語的她很可能會錯過中轉航班,被延誤在碩大而繁亂的伊斯坦布爾機場,獨自度過沒有入境簽證、沒有網絡、沒有現金、不知道接續航班什么時候出發的滯留時光。
我一邊在手機上瘋狂地刷新航班動態,關注著前序航班的進展,一邊查看航空公司細則,研究滯留后幾種可能的轉機方案;同時還拼命地用翻譯軟件打字,把可能遇到的情形,問路時可能用到的英文句子等一一翻譯出來并截圖發給她。
本來全程我都在自鳴得意,什么“父母在,不遠游”,咱們明明可以“家人在,一同游”嘛。現在看來,古人還是對的,“游必有方”—帶著家人走在語言不通、文化迥異、生活習慣差異巨大的異國他鄉,面對這一路上頻發的各種突發狀況,是很有挑戰的。小到沒有圖片的菜單、各種需要填寫的手續和資料,大到向導講解的注意事項、航站樓的飛行信息板,所有能預見的和會遇見的情形,隨時隨地都會讓人陷入手忙腳亂的巨大無力感之中。
其實自始至終我都不覺得是在“帶”媽媽一起旅行,而是全程都在“和”她一起遠游。我們一起坐在街邊喝橙色的阿佩羅雞尾酒,驚奇地發現當地人用腌漬過的羽扇豆種子下酒;我們把車開到殘雪未消的冰島東部峽灣,探尋海鸚的蹤跡,捕捉涂抹人間的第一抹熹微晨光;我們在一個又一個民宿間漫游,在溪邊汲水,為忽然發現的滾筒洗衣機雀躍,又為只有一粒洗衣凝珠嘆息;我帶她走遍我走過的城市,告訴她我彼時與此刻的心緒;我們一起蹙眉品嘗甘草風味的冰激凌,窩在房間里一部接一部地看電影,在宛如地下美術館的斯德哥爾摩地鐵站里飛速“打卡”,又在晃動的船屋酒店里各自做著深深淺淺的夢。
這一路我能感受到巨大的成長,有關于母女關系的,但更多仍是關于自己的。我學著規劃,學著妥帖辦事,學著平心靜氣,學著承擔錯誤,學著凡事都要另有計劃。以前,媽媽只知道我進屋的第一件事是播放喜歡的樂隊的歌曲;現在,她見證我用支離破碎的外語和她一路“通關”,蹭陌生人的手機熱點、與民宿房東暢快交談、發郵件憤怒但不失理性地向航空公司維權……
但是,在每一次我們爭吵不休,又哭得撕心裂肺時,其實早已約好了下一次的遠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