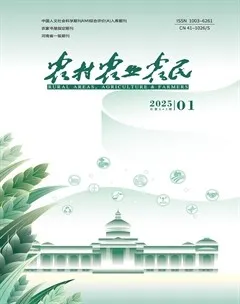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邏輯與思路
摘 要:建立糧食產銷區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是當前更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及共同富裕的戰略性舉措,更是踐行區域公平發展和共享發展新理念的內在要求。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核心在于回答依據什么補償、補償多少、如何補償等問題。可以以凈調出(入)數量的糧食生產成本及市場價值作為補償依據,根據補償依據計算產銷區各省補(受)償額,明確以資金為主、產業與智力為輔的多擇補償方式。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需要建立“糧交易”試點和產銷固定合作伙伴試點,加強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增加主產區利益訴求權的強制性要求,建立糧食產供銷監測系統和信息共享平臺。
關鍵詞:橫向利益補償;補償機制;糧食主產區;糧食主銷區
中圖分類號:F320.1" " "文獻標志碼:A
“糧食大縣、經濟弱縣、財政窮縣”的客觀現狀,不僅凸顯區域發展不均衡不充分問題,遲滯共同富裕進程,而且影響主產區抓糧種糧積極性,危及國家糧食安全。在現行主產區①耕地利用制度鎖定以及當前中央財政補貼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加大對主產區的利益補償,迫切需要探索新的補償機制,實行主銷區對主產區的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是其中的可行選擇。202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均提出“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202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和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的指導意見》再次指出,要在建立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上邁出實質性步伐,推動糧食主產區、主銷區、產銷平衡區落實好保障糧食安全的共同責任。
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是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推動以省為行政單位的主銷區以人、財、物、技術等資源作為補償物按照約定的標準補償給主產區,讓主產區糧食生產得到合理的利益補償,讓產銷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更為均衡[1]。當前,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既是持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現實考量,又是體現區域公平發展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論邏輯。其中的核心在于解決好依據什么補償、補償多少、如何補償3個問題,重點在于試點先行、統籌設計、制度保障與系統監測。
一、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基本邏輯
構建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既是解決當前區域發展不均衡和種糧積極性不足的現實邏輯,也是貫徹“誰受益、誰付費”公平理論和“先富帶后富”共享理念的理論邏輯。
(一)現實邏輯
第一,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在全國主體功能區及農業區域分工明確并不斷深化的背景下,糧食主產區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穩定器”,是實現糧食穩產保供的關鍵。從自然資源稟賦看,糧食主產區擁有較為豐富的耕地資源和水土氣候條件,糧食生產規模較大且經營水平相對較高,但區域經濟發展基礎較弱,經濟總量、人均財稅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核心經濟指標遠低于糧食主銷區,存在“糧財倒掛”矛盾。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迫切需要加大對主產區的利益補償,激發主產區糧食生產積極性。但是,一方面,現有對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主要來自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在中央財政支出增長趨緩的現狀下,補償標準難以持續提高,主產區糧食生產能力和糧食生產積極性的提升受到抑制[2]。另一方面,目前各種糧食獎補政策,尚未按照糧食調出量和自用量進行區別獎補,也未考慮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等指標進行獎補,難以給主產區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增收效應,影響了主產區政府抓糧積極性。雖然我國已經規定糧食生產產銷區同責,但主產區責任過大、主銷區責任不足且主銷區沒有對主產區進行利益補償的現實狀況,必將影響國家糧食安全的持久性。因此,探索建立主銷區對主產區的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是持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有效手段。
第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需要。糧食生產屬于弱質產業,產業收益相對較低。主產區生產糧食,但糧食產業經濟效益較低,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較小;主銷區對糧食進行精深加工,產業經濟效益較高,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較大。近年來,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的經濟發展差距在拉大[3]。主產區為了發展糧食生產,不得不投入較多的資源、犧牲更多自然資源環境;主銷區卻將更多的資源投入經濟效益更好的二三產業或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質量越來越高;如此逐漸形成“產量越多負擔越重”“弱縣補貼強縣”的奇特現象,造成了產銷區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協調”。2023年,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占全國的77. 9%,而人均財政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分別落后于主銷區7 000元和41 780元以上[4],區域經濟差距明顯。產銷區之間經濟不協調必然對區域間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協調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迫切需要主銷區拿出發展的紅利對主產區進行橫向利益補償。
第三,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主體與非糧食生產主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影響共同富裕目標實現進程。不論是與非農部門相比,還是與農業內部經濟作物生產相比,糧食生產主體的收入均處低位。2023年,我國稻谷、小麥和玉米3種糧食生產的平均畝均凈利潤為75. 14元,利潤率為5. 85%;遠低于經濟作物生產的畝均凈利潤342. 51元和利潤率16. 10%。同時,主產區農戶經營收入大多來源于農業經營性收入,如河南省和黑龍江省的農戶經營性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1. 84%和49. 99%,這一占比遠高于主銷區,如廣東省的24. 27%。特別是近年來,受勞動力成本提升、地租顯性化、農資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影響,糧食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種糧收益空間不斷被擠壓,與其他就業者的收入差距持續保持較高水平[5]。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健全農民種糧掙錢得利的機制保障”。顯然,從促進共同富裕角度,需要加大對主產區糧食生產的橫向利益補償,促進種糧農戶生產經營性收入增加,縮小主產區農戶與主銷區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
(二)理論邏輯
第一,基于公平理論的糧責共擔需要。糧食是事關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基礎性戰略物資,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糧食生產責任區域之間應該公平承擔。當前,主產區承擔大部分糧食生產責任但沒有得到相應的收入或利益補償,主銷區承擔與其常住人口不相對等的糧食責任,但卻得到較高的財政收入。也就是說,糧食主產區財政收入與區內土地面積之比遠低于主銷區。按照公平理論,這對糧食主產區是不公平的。事實上,橫向利益補償本質上是市場機制發揮重要作用的補償機制,糧食主銷區作為利益流入主體理應向作為利益流出主體的主產區提供合理的利益補償,這不僅體現公共產品“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而且體現區域之間共同承擔糧食生產責任的公平理念。因而,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具有學理上的合理性。
第二,基于共享理念的均衡發展需要。糧食產銷區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源在于土地資源利用的制度鎖定而形成的“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核心——邊緣型產業空間結構。主產區土地被制度固定用在生產率較低的糧食生產上,承擔了過多的責任而經濟發展落后,主銷區土地多用于發展生產率較高的二三產業,經濟發展先進卻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造成產銷區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不均衡。盡管主銷區上交國家更多的財政資金并以財政轉移支付形式補償主產區,但這種補償力度不足以彌補耕地被用來發展二三產業的機會損失,主銷區經濟發展紅利并沒有更多被主產區共享。顯然,打破這種區域間不協調狀態,必須要堅決貫徹執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區域發展“公平、協調、共享”的重要論述,通過共享主銷區的經濟發展紅利,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共富理念。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就是要在制度上促進主銷區經濟發展紅利能夠為主產區共享,進而推進共同富裕進程。
二、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核心思路
構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核心是確定補償依據、明確補償標準和選擇補償方式。
(一)確立補償依據:凈調出(入)量糧食成本及價值
補償依據重在回答“憑什么補償”這一問題。現有研究者認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主要依據是基于耕地等投入的生產要素、跨省凈調出的糧食數量、糧食生產生態損耗量等。將耕地等生產要素作為補償依據,主要是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6]、耕地用于發展二三產業的機會成本[7],當然耕地數量是指糧食凈調出(入)數量①折合的虛擬耕地資源②數量。將耕地、水資源等生產要素作為補償,主要是計算糧食凈調出(入)數量折合的生產要素消耗量[8]。將糧食凈調出(入)量作為補償依據,主要是依據跨省糧食凈調出(入)數量確定橫向補償系數[9]。將生態作為補償依據,主要是跨省糧食凈調出(入)數量折合的碳源產生量。
本研究團隊認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的依據只能是凈調出(入)“糧食”,包含凈調出(入)量“糧食”的生產成本、機會成本、碳成本、市場價值等。凈調出(入)量糧食的生產成本包括土地、勞動力、肥藥、機械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實際成本,機會成本是以上述生產要素用來生產糧食而沒有用于發展二三產業的機會損失成本(以本區域一產與二三產業的生產率之差乘以要素投入數量計算),碳成本為生產凈調出(入)量糧食的全過程碳產生量乘以碳市場交易價格。
(二)明確補償標準:雙方協商的標準及動態調整
補償標準回答“補償多少”這一問題。利益補償標準的核算需要與依據相結合,包括3類核算。一是依據投入生產要素的成本核算,如耕地生態價值的核算[10-11],虛擬耕地的核算[12],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核算,生產要素消耗量的核算。二是依據糧食或等量產出的市場價值進行的核算,如依據糧價按比例提成[13],以GDP按比例提成[14],參考碳交易方法以糧食安全指標核算[15]。三是綜合核算,如結合糧食凈調出(入)數量,以固定金額或固定比例確定補貼額度,或者中央收取主銷區一定的補償金額并根據主產區糧食調出量給予合適的補償額度。
實際上,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是一個討價還價的交易過程,成交價格(即補償標準)的計算尤為關鍵。一是糧食主產區的“報價”,以凈調出數量糧食生產的總成本(要素投入成本、機會成本)與總價值(產品市場價值、碳匯價值)來計算的金額數。二是糧食主銷區的“還價”,以補償系數法測算或“反事實”法測算的金額數。其中,補償系數法測算是以主產區計算的補償總額減去主銷區當年上交中央用于農業的財政轉移支付額再除以當年本地財政收入,以此數的近3年平均值作為橫向利益補償系數,用該系數乘以主銷區本地財政收入作為補償標準;“反事實”法測算,假定主銷區土地沒有用來發展二三產業而用來生產凈調入量糧食的總成本,以此作為補償標準。三是補償標準調整。補受償雙方在“報價”和“還價”中達成交易價格,確定補償標準。補償標準并非一成不變,需要考慮主銷區經濟實力、發展潛力、主產區自我發展能力以及糧食進口配額等因素,形成動態調整機制。
(三)選擇補償方式:資金+產業+智力的多樣補償
補償方式解決的是“如何補償”問題。現有研究認為補償方式主要包括資金及非資金兩種方式。其中,資金方式主要包括財政轉移支付[2]、建立補償基金[13]或糧食發展基金[16]等;非資金補償主要是實物、技術及智力補償[17]、投資主產區農業基礎設施[18]。從補償目的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的目標是更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促進區域間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方面,補償資金可以用于高標準農田建設、糧食倉儲設施建設、農業生態修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也可以用于獎勵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項目建設。在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產業補償主要是激發主產區糧食及相關產業發展活力;智力補償主要是主銷區為主產區提供糧食產業高質量發展及鄉村振興的技術、管理人才培訓和咨詢服務。
需要說明的是,具體補償方式的選擇還需要解決“誰補償誰”這一問題,但這一問題的確定并不容易,因為糧食流通的方向并不是固定的,某一省份流入的糧食可能源于多個省份,但在補償上不太可能對多個省份分別進行利益補償。對于資金補償,可以在中央財政部成立糧食省際橫向利益補償資金專戶,主銷區依據應該承擔的“糧責”(糧食凈調入量),按照一定的補償計算方法計算出應補償額度,并上交到財政部資金專戶;主產區依據額外承擔的“糧責”(糧食凈調出量),按照一定的補償計算方法計算出應受償額度,從財政部資金專戶中獲得相應的補償金額。對于非資金補償,建議主要的糧食凈調出區(黑龍江、河南、吉林、內蒙古、安徽)與主要的糧食凈調入區(廣東、福建、浙江、北京、上海、天津、海南)①開展結對幫扶,建設產銷區產業共同體,不斷深化糧食購銷合作和產業鏈合作;或者由主銷區承擔培訓主產區農業農村業務干部的責任,為其提供智力支持。
三、實施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對策建議
我國尚未實施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推進實施需要從試點中總結經驗,需要在國家層面做好頂層設計、搭建好制度框架,需要有方便監管和調控的完善的流通數據信息系統。
(一)探索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試點
盡管在國際國內利益流出區和流入區之間的橫向補償已有較多的成功案例,如美國水土保持補償、德國州際財政平衡補償、我國浙皖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態補償和江蘇南北合作幫扶等[19],但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實踐尚無前例,國內外均缺乏可資借鑒的成熟模式。為此,亟須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試點,嘗試建立“糧交易”試點、產銷區固定伙伴深度融合試點。
借鑒碳交易市場的設計和運作機制,建立“糧交易”試點。綜合考慮各省產銷區經濟和財政狀況,按照“誰缺糧、誰出錢”原則,由國家統一確定糧食生產責任配額,通過市場化交易機制調節各省之間的利益,促進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區域資源共享和協同發展,確保全國糧食安全。一是以糧食生產責任配額為補償標的,結合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口數量、糧食需求、資源承載能力、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設定糧食生產責任配額。二是建立配額交易機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實際糧食生產和需求狀況,可以購買或出售糧食生產配額,確保國家糧食供給安全性和穩定性。三是確定配額定價機制,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供求調節的價格機制,根據市場需求、生態保護成本、資源消耗和生產效率等因素動態調整配額價格。四是建立第三方審計平臺,由第三方對配額分配、交易價格、資金流向等進行審計,確保市場公平和透明。
借鑒江蘇南北合作幫扶經驗,建立產銷區固定伙伴深度融合試點。一是中央政府在初步核算主要糧食凈調出區和凈調入區的基礎上,引導產銷區兩兩建立固定合作伙伴,如豫粵糧食購銷合作伙伴。二是中央政府引導產銷區加強產業鏈協作,特別是在種業開發、糧食加工、物流倉儲、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建立產業鏈共同體。三是推動糧食產業生態認證,主銷區與主產區協同推進糧食產業生態認證,推動糧食優質優價,發揮生態認證品牌效應,提升糧食價值鏈和農民收益。四是深化產銷區產業協調發展,主產區承接主銷區產業,優化區域產業布局,推動優勢互補,形成以糧食安全為牽引的協同保障機制。
(二)強化中央政府在其中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作用
國家對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實行的是“以縱為主、以橫為輔、縱橫結合”的機制體系,橫向利益補償機制是對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的重要補充。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目的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國家戰略性舉措,中央政府必須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這一關鍵作用體現在:一是做好頂層設計。由中央政府對橫向利益補償的依據、標準、方式、效果評估等進行全局性、戰略性的部署規劃,明確補償的總體目標、政策導向和實施的原則、程序及關鍵舉措。既要激勵與支持糧食主產區種糧抓糧積極性,又要確保主銷區財政收入能夠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在省際區域之間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既要為各省橫向利益補償實際操作提供方向指引,確保全國一盤棋,又要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多樣化補償方式提供靈活空間,形成上下聯動、左右協同的良好局面。二是統籌協調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效落實。橫向利益補償不僅涉及產銷區政府,而且涉及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等相關部門,建議由中央財經委牽頭,明確各部門在橫向利益補償中的責任分工,建立跨部門協作機制和監督考評機制,確保橫向利益補償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三)完善權責劃分明確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體系
明確對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訴求權的強制性要求。我國201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法》提出,國家建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支持和鼓勵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建立穩定的產銷合作關系;2016年修訂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也指出,國家鼓勵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以多種形式建立穩定的產銷關系;2018年出臺的《關于深化糧食產銷合作提高安全保障能力的指導意見》也提出建設多種形式的產銷區之間合作關系。盡管現有法規政策中提到了對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但由于沒有強制性要求,主銷區實際上并沒有直接對主產區進行利益補償。由此可見,推進橫向利益補償必須有法律上的強制性要求。而這種要求就是明確將主銷區界定為利益補償主體,賦予其一定的糧食生產利益補償法律責任;明確主產區為受償主體,賦予其一定的利益補償訴求權。主產區憑借這一補償訴求權可以向主銷區申請合理的利益補償。在法律制度上還必須作出明確界定的包括補償范圍、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方式和補償標準等。這方面的法律法規界定可以參考我國生態保護功能區與受益區之間建立的橫向利益補償法律制度。
當前,我國亟須制定專門法律法規。一是出臺《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法》,在法律層面界定糧食主產區、產銷平衡區和主銷區的責任、義務和權利,明確補償范圍、主體、方式及標準,確保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安全保障法》的基礎上,指導主產區、主銷區出臺橫向利益補償的地方性法規。三是規范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流程,建議構建標準化補償流程,包括補償申請、審核、分配、反饋等環節,確保補償機制的程序化和公平性。
(四)建立全國糧食產供銷系統監測體系和信息共享平臺
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的主要依據是“糧食”,即凈調出(入)的糧食數量,但當前我國對糧食流通關注不夠,導致對糧食流通的數據,尤其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類糧食流入流出的數據掌握不足,缺乏糧食產銷區之間的調入調出精確數據。
一是建立全國統一的糧食生產和流通運輸數據采集和監測信息平臺,收集主產區、產銷平衡區、主銷區糧食生產、流通、庫存、消費和進出口數據,強化平臺的兼容性和擴展性,確保各地糧食數據搜集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二是強化數據采集的標準化流程,確保省際糧食調入量和調出量等關鍵指標記錄的準確性和更新的及時性,通過實施定期的數據校驗和審計機制,提高數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三是建立全國糧食安全預警系統,用于實時監控糧食生產、庫存、市場供需、災害情況等關鍵指標,提前預測糧食供應風險,并為橫向利益補償的測算及補償決策提供支持。四是建立糧食產銷區橫向利益補償機制信息共享平臺,確保補償金額、資金來源、使用情況、實施效果等信息在政府部門之間、研究機構和市場主體之間的共享,定期發布補償資金使用報告,接受公眾和社會監督。
參考文獻:
[1]孫珊,李邦勤. 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研究[J]. 中國經貿導刊,2024(9):25-28.
[2]鄭兆峰,宋洪遠. 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現實基礎、困難挑戰與政策優化[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23,44(2):214-221.
[3]魏后凱,賈小玲. 中國糧食主產區萎縮態勢及其福利損失[J].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3,27(5):65-79.
[4]孫中葉,楊傳宇,李治. 健全我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的新思路[J]. 農業經濟與管理,2024(1):1-11.
[5]胡凌嘯,劉余,華中昱. 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狀況及機制創新[J]. 農村經濟,2024(5):77-88.
[6]周小平,柴鐸,宋麗潔. “雙縱雙橫”:耕地保護補償模式創新研究[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3):50-56.
[7]陳璐,馮廣京. 糧食主產區耕地機會成本分析[J]. 東北農業大學學報,2019,50(7):68-75.
[8]王越,孔令宇,高丹桂,等. 生產要素視角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研究:以東北糧食主產區為例[J]. 中國農村經濟,2024(6):117-135.
[9]劉慧,崔亞妮,鐘鈺. 高水平開放下保障飼料糧供給的新舉措與展望[J]. 世界農業,2023(6):25-36.
[10]梁流濤,祝孔超. 區際農業生態補償:區域劃分與補償標準核算:基于虛擬耕地流動視角的考察[J]. 地理研究,2019,38(8):1932-1948.
[11]阮熹晟,李坦,張藕香,等. 基于生態服務價值的長江經濟帶耕地生態補償量化研究[J].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1,42(1):68-76.
[12]賈晉,丁華. 基于馬克思主義級差地租理論的糧食產銷區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理論分析、補償設計與路徑選擇[J]. 農業經濟與管理,2024(5):1-14.
[13]魏后凱,王業強. 中央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的理論基礎與政策導向[J]. 經濟學動態,2012(11):49-55.
[14]朱新華,曲福田. 不同糧食分區間的耕地保護外部性補償機制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5):148-153.
[15]李明建. 完善我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研究:基于財政分權視角[J]. 中國糧食經濟,2022(4):41-45.
[16]郭雅媛,張青. 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創新研究:基于糧食安全問題的戰略思考[J]. 開放導報,2023(3):88-95.
[17]楊建利,靳文學. 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研究[J]. 農村經濟,2015(5):9-13.
[18]趙光遠. 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的現實需求與落地方式[J]. 新長征,2024(4):53-55.
[19]王怡婷,魏廣成,巴雪真,等. 區際補償對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的啟示借鑒[J]. 農業經濟與管理,2024(5):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