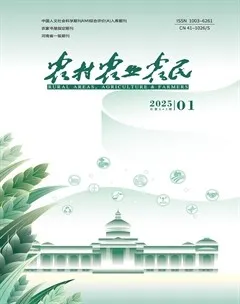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視角的糧食安全保障研究
摘 要:夯實糧食安全根基是建設農業強國與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離不開農機社會化服務的強力支持。通過2022年實地調研廣東省水稻種植大戶發現,農機社會化服務面臨再服務體系落后、烘干服務發展緩慢及倉儲服務尚未成型等現實困境。提出加大扶持和培訓力度、健全農機維修服務體系、提升糧食烘干服務能力以及重構糧食倉儲服務體系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機社會化服務;糧食安全根基;農機再服務;烘干服務;糧食倉儲服務
中圖分類號:F316. 11" " "文獻標志碼:A
現代化的農機裝備是保障糧食生產與糧食供給安全的重要技術基礎。新時期的中國正經歷由小農戶分散作業向適度規模經營轉型[1]。構建完善的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是轉型時期加速農業生產機械化、現代化,實現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舉措。“深入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是新時期的主要戰略方向之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要做到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同時要創新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當前,種糧大戶逐漸成為保障糧食生產供給的重要經營主體,如何加快完善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建成與種糧大戶需求相匹配的服務體系,是新時期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的重要舉措。
一、構建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現實意義
農機社會化服務是有效促進農業經營主體和現代農業有效銜接,解決糧食生產“誰來種地、怎么種地”重大問題的現實途徑。作為落實國家重大戰略“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有效舉措,構建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能通過農機載體功能,實現糧食生產過程的標準化、集約化、專業化,推動我國糧食生產提質增效。
(一)連接經營主體與現代農業的重要橋梁
《農業農村部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以現代化的服務過程實現農業現代化。一方面,傳統聚焦于耕種收等產中環節的農機社會化服務,有助于小規模糧農以低成本采用現代機械生產技術,將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2]。另一方面,不斷完善的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能夠覆蓋產前產中產后全環節、提供全程機械化服務,為種糧農戶解決產前產后糧食生產缺人力、難烘干、無市場等問題,助推種糧農戶深度融入現代農業。綜上,健全的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既是連接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橋梁,也有助于種糧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深度融合。
(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有效載體
要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智能化,給農業現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在大國小農的現實背景下,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中國小農引入現代生產方式、采納機械技術的有效途徑[3],是中國農業機械化和農業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的重要支撐[4]。并且,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可通過服務外包聯合分散農戶、提升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進而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為鄉村產業振興和組織振興提供保障。可見,構建完善的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有助于提升農業機械化程度、強化農業生產科技水平、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5],進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三)保障糧食產品供給安全的核心措施
長期以來,小農生產存在分散作業、生產成本偏高、經營效率低下等問題[6],是制約中國糧食生產的主要瓶頸。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糧食生產一大軟肋是生產成本偏高,解決辦法還是要創新經營方式,要培育好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健全專業化社會化服務體系,把一家一戶辦不了、辦起來不劃算的事交給社會化服務組織來辦。換言之,在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健全糧食生產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有助于提升糧食生產效率與效益、激勵糧農生產積極性,保障糧食供給安全[7]。
二、農機社會化服務的發展歷程
2013年,農業部(現為農業農村部)發布《關于大力推進農機社會化服務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提出“農機社會化服務的市場主體進一步壯大、服務領域進一步拓展、服務質量進一步提升、服務效益進一步提高,推動農業機械化‘全面、全程、高質、高效’發展。力爭到2020年,全國擁有農機原值50萬元以上的農機大戶及農機服務組織的數量、全國農機化經營總收入均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與要求。經過多年的培育與建設,中國農機社會化服務市場不斷完善,基本完成《意見》提出的目標,為糧食安全保障提供了堅實支撐。
(一)農機社會化服務市場不斷發育
一是服務機構與人員數量快速增長。全國農機化作業服務組織的機構數和人員數,從2010年的17. 1萬個和101. 9萬人增長至2022年的19. 6萬個和210. 6萬人,年均增速分別為1. 14%和6. 24%。二是擁有農機原值50萬元以上的服務機構以及大戶數量大幅提升。全國擁有農業機械原值50萬元以上(含50萬元)的農機化作業服務組織機構數和人員數,從2010年的1. 6萬個和26. 6萬人,增長至2021年6. 1萬個和102. 7萬人,年均增速分別高達12. 9%和13. 1%;截至2022年,擁有農業機械原值100萬元以上(含100萬元)的農機化作業服務組織機構數和人員數分別為3. 3萬個和60. 5萬人,較上年增長了6%和3. 1%。三是農業機械作業服務收入實現翻番。2022年全國農機作業服務收入達3 678. 95億元,為2010年農業機械化田間作業收入1 447. 39億元的2. 5倍①。
(二)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穩步提高
一是農業機械總動力呈逐年增長態勢,2010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為9. 28億千瓦,2022年上升至11. 06億千瓦,年均增速為1. 47%。二是農機作業面積逐步擴大,2010年全國農機作業面積共計3. 36億公頃,2022年擴大至4. 91億公頃,年均增速高達3. 21%。三是大型農用機械保有量快速增長,全國大型拖拉機(功率為58. 8千瓦及以上)保有量從2010年的33. 6萬臺增長至2022年的83. 97萬臺,年均增速為7. 93%;耕整機保有量從2010年的420. 78萬臺上升到2022年的519. 28萬臺,年均增速為1. 77%;聯合收割機保有量從2010年的99. 21萬臺上升到2022年的173. 11萬臺,年均增速為4. 75%②。
(三)糧食機械化作業水平全面提升
一是水稻耕種收等作業環節的機械化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2010年水稻耕種收3個環節機械化比例為85. 99%、20. 70%和64. 02%,2022年分別上升至98. 75%、61. 59%和95. 55%。二是小麥種植基本實現作業環節全程機械化。2022年小麥耕種收3個環節機械化程度都在90%以上,分別為93. 71%、94. 17%和97. 77%。三是玉米耕種收等作業環節的機械化水平都有一定程度提升。2010年玉米耕種收3個環節機械化水平為57. 53%、71. 06%和23. 96%,2022年分別上升至60. 65%、82. 04%和75. 06%③。
三、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現實困境
近年來,隨著農地流轉市場快速發展與新型經營主體不斷培育,種糧大戶日益成為糧食生產的主要經營主體。因此,過去以種糧小農戶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漸露缺陷,生產“末端”服務嚴重缺失,成為糧食規模化生產和農業現代化經營的制約瓶頸,不利于糧食供給安全目標的實現。以本團隊2022年上半年于廣東省11個縣(區)所進行的217個水稻種植大戶調研素材為例,進行論證說明。
(一)再服務體系落后,機械作業缺乏保障
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部分種糧大戶會購置作業環節(耕整、播種或者插秧、收割等)的相關機械,通過服務利潤內部化來降低作業成本,提高種糧效益。調研數據表明,217個種糧大戶中擁有拖拉機或者耕整機的大戶占比35. 02%;擁有插秧機或者直播機的農戶占比33. 64%;擁有(聯合)收割機的大戶占比30. 41%①。盡管機械化作業大大提升了糧食種植效率,但種糧大戶經營規模大、作業量多,同樣也面臨著“農忙”“雙搶”等傳統農業經營問題。調研數據顯示,種糧大戶在“農忙”時期平均每天使用機械作業14~18個小時,部分種糧大戶甚至出現農機白晝不停工作的現象。為了保證作業效果,農機作業不僅需要足夠的動力,更需要及時的養護、維修服務來保障機械能夠長時間密集作業。
然而,當前農機再服務體系(養護、維修等)卻不盡完善,種糧大戶的機械作業缺乏后續保障。宏觀統計數據表明,2010年農業機械維修廠及維修點的機構數和人員數為21.70萬個和47.95萬人,2022年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至14.58萬個和36.14萬人。面對繁重而又緊急的作業量,如果農業機械在作業過程中出現故障而未能及時得到維修等服務,將會中斷或者擱置農業生產過程,糧食作業的不確定性增加,將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反之,如能迅速得到農機維修等服務,就能及時止損。對此,本團隊與全國勞動模范羅新輝及其合作的23個種糧大戶進行座談②,種糧大戶普遍反映作業過程中出現農機故障較難及時獲得維修服務是當前面臨的主要困難。可見,農機再服務體系發展滯后,是制約糧食機械化生產的主要問題之一。
(二)烘干服務發展緩慢,種糧大戶利益受損
相較于干谷,濕谷一方面不利于儲存,另一方面銷售價格也相差甚遠。種糧大戶如能將濕谷加工成干谷,將獲得規模化報酬,進而提高種糧效益。濕谷加工成干谷的主要途徑有:傳統晾曬和機械烘干。一般而言,即使水稻品種不同,同季水稻的成熟期也相差無幾,規模化種植大戶的產量高,如通過傳統晾曬的途徑來加工濕谷,將會對晾曬場地的面積、位置以及應對突發狀況時的人力有著極為苛刻的要求。因此,大部分種糧大戶會選擇機械烘干來加工濕谷。但是,烘干設備的購置成本較高,且對場地有一定的要求,大部分種糧大戶較難實現自購烘干機械,只好購買烘干服務。
然而,當前烘干服務的發展趕不上種糧大戶的發展速度,大部分種糧大戶缺乏糧食烘干途徑而只能低價售賣濕谷,致使豐產難以豐收,利益極大受損。調研數據顯示,水稻種植大戶中直接售賣濕谷(轉化成干谷重量)的平均售價為:早稻2.354元/公斤、中稻2.406元/公斤、晚稻2.828元/公斤。相較之下,種糧大戶如果以0. 22元/公斤購買烘干服務,再售賣干谷,平均售價為早稻3.098元/公斤、中稻4.138元/公斤、晚稻3.572元/公斤。可見,相較于售賣濕谷,種糧大戶若能獲得烘干服務再售賣干谷,早稻、中稻和晚稻的平均利潤率分別可實現26. 51%、62. 84%和18. 53%的提升③。
(三)倉儲服務尚未成型,規模生產穩定性低
種糧大戶批量生產糧食將催生倉儲需求。由于糧食收獲與市場需求時間錯配、糧食價格波動等原因,大部分種糧大戶都有糧食倉儲的意愿,但現代化、智能化的糧倉建設不僅經濟成本高,還須獲批相應的設施用地,一般的種糧大戶較難實現,因此大部分種糧大戶只能選擇在收割期以低價售賣糧食。調研數據表明,直接在收割期售賣糧食的種糧大戶比例較高:早稻為98. 21%、中稻為97. 67%、晚稻為92. 23%。如能通過社會化服務解決種糧大戶倉儲問題,將有助于大戶對糧食加工、銷售等產后環節進行合理規劃,進而規避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一方面,糧食倉儲可在一定程度上為糧食加工環節降低作業密度和提升作業環境穩定性,減少因時間和環境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技術風險;另一方面,當糧食售價不穩定時,種糧大戶可通過倉儲服務將部分糧食進行儲存,待糧價穩定后再行銷售,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面臨的市場風險。
然而,當前市場“末端”現代化、智能化的倉儲服務嚴重欠缺,種糧大戶缺乏通過倉儲服務規避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途徑,由此也導致部分種糧大戶初成規模后不得不縮小種植面積以降低風險,糧食規模生產缺乏穩定性。調研數據表明,217個種糧大戶中,2022年因為風險問題而選擇縮減規模的比例分別為早稻8. 93%、中稻11. 63%、晚稻6. 22%。
四、完善糧食生產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健全農機維修服務網絡
當前,農機維修服務市場的需求呈時間集中、緊迫性強的特點,供給卻表現為分散不均、不成體系,供需失衡比較嚴重[8]。對此,需要通過政策引導來健全農機維修服務網絡。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對大型農機維修設備進行財政補貼,降低服務成本;建立農機維修人員培訓專項財政資金,提升維修人員的技能與素質。二是摸清農機維修服務的實際情況。無論是政策補貼還是布局規劃,應先了解實際的維修服務供應能力以及覆蓋范圍。各市縣應對管轄范圍內具有農機維修服務的網點進行統計,并進行能力鑒定以及資格審查。三是布局縣鎮二級維修網絡。以縣級農業農村部門為核心,組建每縣一個大型維修中心,維修能力覆蓋全縣范圍;通過“鎮政府+合作社”或者“鎮政府+農機企業”的協同模式,每鎮建一個維修網點,確保能夠在鎮域范圍內提供及時的維修服務。四是實現服務數字化智能化。以縣維修中心為依托,開發農機維修服務智能App,及時匹配農機維修供需信息,確保種糧大戶維修服務需求能夠及時被維修服務團隊獲取。
(二)提升糧食烘干服務能力
隨著糧食種植規模化程度不斷提升,糧食烘干服務需求愈發強烈,但是各地糧食烘干設備保有量參差不齊、整體服務能力有限[9]。對此,需要調動社會各界力量提升糧食烘干服務能力。一是加大烘干機械購置補貼力度。降低烘干機購置成本,支持有能力的種糧大戶、合作社、糧食企業購置烘干設備,提升各地糧食烘干設備的保有量,并鼓勵持有烘干設備的主體提供糧食烘干服務。二是建立縣級糧食烘干服務中心與信息平臺。依托縣政府建設糧食烘干服務信息平臺,及時發布縣域范圍內的糧食烘干服務點及服務信息;每個產糧大縣一個大型糧食烘干服務中心,為縣內糧農提供糧食烘干服務。三是補貼鼓勵農機企業研發生產中小型烘干設備。適度規模化是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趨勢,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糧食可能是由中等規模的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生產與經營,中小型烘干設備有助于他們實現烘干服務由外包向自我服務轉變,一定程度上提升種糧效益。
(三)重構糧食倉儲服務體系
過去,倉儲更多的是糧食加工企業思考的問題,糧農一般都能通過簡易包裝和分散存放等方式儲存糧食。然而,當前農業規模化經營趨勢使得越來越多的種糧大戶不得不面臨和思考如何安全、有效存儲批量糧食[10]。對此,需要重構縣鎮糧站,提供省、市、縣、鎮多層級全方位、現代化的糧食倉儲服務。一是充分利用現有儲糧倉庫。依托現有糧倉糧庫,在條件允許、質量把控的前提下,放開部分倉儲容量用于提供糧食倉儲服務。二是重建升級縣、鎮糧站。將過去縣、鎮二級糧站進行重建升級,轉為糧食倉儲服務中心,向縣域范圍內的糧農提供倉儲服務。三是加快建設產糧大縣糧食產后服務中心。設立專項財政資金,為每個產糧大縣建立糧食產后服務中心,遵照《糧食產后服務中心運營指南》,優先發展烘干、倉儲等服務主業,在中心運營成熟后再拓展增值服務業。
參考文獻:
[1]佟澤鑫,劉帥.農地流轉期限與農戶耕地質量保護行為:兼論不同流轉行為的影響差異[J/OL].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 https://link. cnki. net/urlid/11. 3513. S. 20240716. 1114. 016
[2]薛信陽,韓一軍,高穎. 農機社會化服務對糧食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基于四省小麥和玉米種植戶的調查[J]. 農村經濟,2024(1):10-19.
[3]鄒寶玲,洪煒杰,耿鵬鵬. 誰在養活中國:基于農戶種糧行為決定機理的分析[J]. 農業技術經濟,2024(5):4-24.
[4]金文成,王歐,楊夢穎,等. 農業強國建設目標下的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戰略與路徑[J]. 農業經濟問題,2023(10):13-21.
[5]馬九杰,趙將,吳本健,等. 提供社會化服務還是流轉土地自營:對農機合作社發展轉型的案例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9(7):35-46.
[6]張紅宇. 大國小農:邁向現代化的歷史抉擇[J]. 求索,2019(1):68-75.
[7]唐文蘇,翁貞林,鄢朝輝. 信息獲取、風險偏好與技術密集型農機社會化服務:基于江西省水稻規模經營戶的調研[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2,27(4):270-280.
[8]阮冬燕,周晶,王娟. “創造性毀滅”:農機裝備升級引發的維修服務體系重構[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4,29(1):240-257.
[9]黃景瑤,郭芷岍,許健釩. 烘干服務市場發育對種糧大戶經營規模選擇的影響研究[J]. 山西農經,2023(21):29-32.
[10]亢霞,鐘昱,張慶. 我國糧食倉容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J]. 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36(5):72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