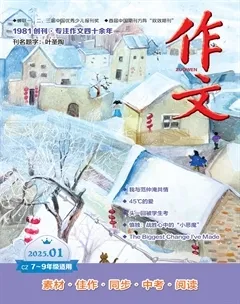青白蘿卜,清白人生
母親來(lái)家里小住,買(mǎi)了排骨和幾個(gè)白蘿卜。不一會(huì)兒,熱氣騰騰的蘿卜燉排骨就上桌了。
屋里香氣四溢,蘿卜清甜爽口,排骨肉香撲鼻,兩者完美結(jié)合,讓人大快朵頤。喝一碗鮮美的蘿卜湯,渾身暖融融的。
兒時(shí)在老家,幾乎家家戶戶都會(huì)種蘿卜。山坡上、田間地頭,都有蘿卜的影子。放眼望去,一畦畦,一片片,鮮嫩嫩的,整個(gè)村莊生機(jī)蓬勃,綠意盎然。屋后的菜地里,母親春天也會(huì)撒下蘿卜種子,施肥、澆水,要不了多久,幼嫩的蘿卜苗破土而出,拔節(jié)生長(zhǎng)。秋冬,蘿卜“噌噌”往外冒出頭,一半裸露在泥土外,一半埋在大地深處。
秋冬時(shí)節(jié),收蘿卜了,在我們那里稱(chēng)為扯蘿卜,是孩子們最樂(lè)于干的事。抓住蘿卜葉使勁一拽,蘿卜鉆出泥土,胖乎乎的,沉甸甸的,帶著泥土的清香,鮮嫩接地氣。
“瞧!這大蘿卜真喜人呢。”母親喜上眉梢,將蘿卜撿起,整齊地碼在籃子里。
蘿卜是冬日鄉(xiāng)親們飯桌上的常客,涼拌、紅燒、燉煮,蘿卜丸子、蘿卜湯、蘿卜肉餡餃子、酸辣蘿卜等五花八門(mén),風(fēng)味各異。村子里常常飄蕩著蘿卜的清香,綿長(zhǎng)悠遠(yuǎn)。
“冬吃蘿卜夏吃姜,醫(yī)生不用開(kāi)藥方。”蘿卜全身都是寶,有“土人參”的美譽(yù),營(yíng)養(yǎng)豐富,生津開(kāi)胃,蘿卜葉、根莖都可食用,蘿卜葉剁碎后拌到飼料中喂養(yǎng)雞鴨,一個(gè)個(gè)吃得歡快。
母親總是變著花樣做各種蘿卜佳肴給我們吃,用豬油炒蘿卜絲,就著紅薯稀飯,蘿卜的清香,紅薯的甜,讓我回味無(wú)窮。寒冷的冬天,母親時(shí)不時(shí)會(huì)做一鍋蘿卜燉排骨,為一家人驅(qū)寒送暖,雖然只有很少的排骨,但沾了油腥的蘿卜湯,美味可口,百吃不厭。屋外,雪花紛飛,屋內(nèi),盈滿了蘿卜的香味,有家的味道,有愛(ài)的味道,尋常的日子踏實(shí)又溫暖。
吃不完的蘿卜,母親會(huì)腌制成蘿卜干,用來(lái)燉臘肉,風(fēng)味獨(dú)特,越嚼越香。蘿卜還可做成泡菜,咬一口,嘎嘣脆,是調(diào)節(jié)口味的下飯菜。偶爾生病沒(méi)胃口,蘿卜絲拌點(diǎn)油辣子,特別爽口解膩,吃后胃口大增,病也好了很多。
有一年,地里的蘿卜遭了蟲(chóng)害,收成寥寥無(wú)幾,蘿卜瘦不拉幾的,母親一臉失落,我們也沒(méi)了往年扯蘿卜時(shí)的快樂(lè)。蘿卜沒(méi)吃兩頓就吃光了。
放學(xué)路上,我和小妹路過(guò)廖爺爺家的菜地,蘿卜從地里冒出了胖胖的頭,一個(gè)挨一個(gè),一個(gè)比一個(gè)大,我看得心癢癢的。看著四周沒(méi)人,腦子里冒出一個(gè)念頭:何不順手牽羊扯幾個(gè)蘿卜呢?
我瞄準(zhǔn)后迅疾下手,扯出一個(gè)雪白的蘿卜,圓溜溜的。速戰(zhàn)速?zèng)Q扯了三四個(gè),小妹開(kāi)心得直蹦:“哦,有蘿卜吃啰!”
我屁顛屁顛地把蘿卜抱回家,母親問(wèn):“哪里來(lái)的蘿卜?”“我在廖爺爺家的菜地里扯的。”我沾沾自喜,等著母親夸我。
“廖爺爺同意了嗎?”“沒(méi),沒(méi)有……”我吞吞吐吐地說(shuō)。
“沒(méi)同意你為啥偷別人的蘿卜呢?”母親嚴(yán)厲訓(xùn)斥道。
“媽?zhuān)摇义e(cuò)了。”
母親領(lǐng)著我和小妹,將蘿卜還給廖爺爺并讓我們認(rèn)了錯(cuò)。從那以后,我沒(méi)有再犯類(lèi)似的錯(cuò)。母親的話,我謹(jǐn)記一生。
青白的蘿卜深受天南地北的人的喜愛(ài),只要扎根大地,就能發(fā)芽結(jié)果,一生樸實(shí)無(wú)華,清清白白。人亦當(dāng)如此,始終恪守本色,清白做人,人生之路才會(huì)越走越光明。
(徐光惠,重慶市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出版有散文集《夢(mèng)回故鄉(xiāng)》)
賞析:蘿卜是一種普通而又不平凡的食材,它在鄉(xiāng)親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從種子到破土而出,再到拔節(jié)生長(zhǎng),最終成為飯桌上的美味佳肴,蘿卜的生長(zhǎng)過(guò)程充滿了生命力和希望。然而,文章并未止步于對(duì)蘿卜的贊美,而是通過(guò)一次“偷蘿卜”的經(jīng)歷,引出對(duì)人生的思考,以蘿卜的樸實(shí)無(wú)華為喻,倡導(dǎo)一種恪守本色、清白做人的人生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