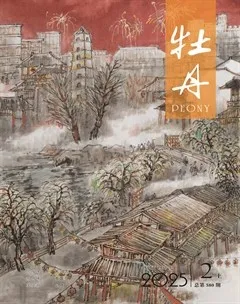創作談:河流和我們
歷史縱向的視域里,河流發祥了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文明;地理經緯的尺度里,古老華夏大地之上有三條巨流即長江、淮河、黃河等距離地并行自西向東奔赴,淮河居其中,而淮河-秦嶺一線斷然成為南北的分界,這是怎樣的神奇!
江淮熟,天下足。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謠歌和古諺所云,可見淮河于“天下”于我們的重要地位。康拉德說,河流承載著人們的夢想、國家的種子和帝國的萌芽。
我老家河南固始,在淮河上游南岸,生于斯長于斯,我是淮河的兒女。放眼河南,淮河流域面積近十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一半以上。因此我帶有故鄉標識的淮河敘事,并非某種意義上的私人化寫作,我們共擁流水的豐沛,流域的豐饒,文明的豐美。事實上,對生養我們的河流,及至每日飲用、享有、觸手可掬的淮河,此前沒有關注,更沒有關切,關于它的始啟、走向、沖越、演化,它的利,它的害,它和我們命運的糾纏和維系。我們也沒有“淮河兒女”的自覺身份認定。我兩次走淮河,第一次是和作家墨白,沿著淮河走并不是為淮河文化的考察和書寫,而是尋找中原人歷史南遷的印記和足跡。第二次是在2019年,仍得于墨白先生所倡,信陽的幾位作家動心了,說好吧,我們“走淮河”吧?初定人選加我三位,也是巧了,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我寫散文。事兒說在那,未見動靜,進入初夏,熱了起來,某個上午,詩人突然發來短信,說準備一下,下午1:30,接你,“走淮河”。路上,詩人給走淮河找到了一個主題,說2020年是毛澤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題詞和新中國治淮70周年紀念,計劃我們三人每人寫一本關于淮河的回望之書、現實之書、河流之書、獻禮之書。
千里淮河,我們分時段和河段,“走”了一年。
進入創作,宏大敘事的構想里,我們都認為,在淮河歷史、流域現實、河流特性、戰略地位、國家治理、人類行為的層面上,及其所呈現的壯闊和恢宏,確實需要有一部全景再現的公共的淮河大書,而在河流文化、生態文化、災難文化、故鄉文化、生存文化、社會生活、現代性的辨析和考察上,更需要屬于我們方式書寫的淮河私人文學志書。淮河需要有這個時代的不同景象和氣象的文學傳記和志書。我轉身回到了上游,我的故鄉,回到我熟稔的土地、村莊、河壩、閘口、樹木、莊稼、家禽、牲畜、民歌、方言、家族、親人中間,尋找書寫的基點和精神的支撐。發現,天大地大,放置你情感的不過故鄉一隅,千川百瀑,流經你生命的乃是故鄉一汪水的血脈。
之后便有了我的二十余萬字的長篇散文《淮上故鄉》。《大河志》是其中的部分。我從故鄉出發,努力通過對一條河流尤其是新中國治淮歷程的回顧,來展示一條大河與國家的關系、與民族的關系、與人的關系,重現河流原始偉力、自然稟賦,當年治淮場景,激情燃燒歲月,未來美麗憧憬。同時對人與水、人與自然、治理和生態、區域與整體、地方和國家、上游和下游、河流和我們等等,進行文學的考量和反思。
新年了,春天就要回到淮河兩岸,想象里已是種子拱土,大地驚蟄,草長鶯飛,桃紅柳綠,長空一注鳥鳴,有如泉水,有如春水,有如美酒,日子就醉了,我在淮上故鄉送給你們流水的滋潤和祝福。
評論:
墨白,河南淮陽人,當代先鋒小說家,劇作家。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開始在《收獲》《鐘山》《花城》《大家》《山花》《人民文學》等刊發表先鋒作品,至今已出版長篇小說《夢游癥患者》《映在鏡子里時光》《來訪的陌生人》《欲望》三部曲等多部;發表中篇小說《光榮院》《討債者》《風車》《局部麻醉》《隔壁的聲音》等四十余部;短篇小說《失蹤》《街道》百余篇;散文、隨筆《lt;洛麗塔gt;的靈與肉》《博爾赫斯的宮殿》等百余篇;出版有小說、散文集《愛情的面孔》《重訪錦城》《事實真相》《霍亂》《墨白作品精選》《夢境、幻想與記憶》《癲狂藝術家》《告密者》《鳥與夢飛行》、訪談錄《小說的多棱鏡像》等多種。有作品譯成英文、俄文、日文或收入多種選本。有電影、電視劇作品《船家現代情仇錄》《當家人》《家園》《天河之戀》等十余部,曾獲“飛天獎”優秀編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