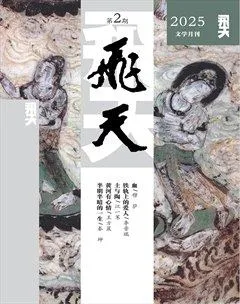血
那天早晨的天空呈現異樣的紫紅色。我驅車四十五公里,來到半山腰黃大友的那套小別墅。路邊橫七豎八停滿了車,我找了一處縫隙把車塞進去,也顧不上會不會擋住別人,跳下車直奔他家大廳。山上的風已經有了初秋的涼意。那棟三層樓房靜立在一片深綠色的高大喬木之中,顯得森嚴不可觸犯。我很少來這里做客,是因為我受不了他女人看我的那種眼神。但我很熟悉這套居室的布局,畢竟三年前他結婚時,以及后來他女人出國旅游時,我都來他家住過的。我跨入大門,穿過一段鵝卵石小徑,走上通往大廳的臺階。
對于黃大友是個好人這一點,在場賓客不論親疏遠近,沒有人不會這么認為。在今天這種場合,假若他還能動,他一定是最不知疲倦地忙前忙后的那一個。即便此刻躺在棺材里,那張臉還對每一位來看他的人含笑致意,仿佛在表示:“不好意思,讓你受累了。”賓客實在太多,以致于想看看死者遺容還需要排隊。這樣一來,他陳列在大廳中央好像一件藝術品。我跟在一位卷發老太太后面。我不知道她是黃大友的什么人,她一看到他就搖頭嘆息,揩著眼淚。離開之前還俯下身子悄悄對他說了句什么。由于現場嘈雜,我沒聽清她說話的內容。黃大友自然也不能告訴我。我猜想她大概是要他安息。可是當我來到他橫著的身體旁邊,看到他那副似笑非笑的模樣,我總覺得他在裝死。就像曾經許多次我和他在約好的地點見面,他都會事先躲起來,在我四下找他時忽然跳出來嚇唬我。會不會這次也是一樣,他正等著我難過落淚,然后睜開眼睛看我笑話?
正當我凝視著亡友的面孔久久不肯離去之時,我感覺到身后有雙眼睛在看我。我沒有立馬轉身和它們對視,而是挪開腳步,和正好站在周圍的兩三個熟人寒暄一番,接著雙手叉腰,假裝四下張望,尋找剛才在我身后的那雙眼睛。果然,黃大友的妻子站在人群之中,面朝我。我們的目光接觸了,出于禮貌我向她點頭致意,她則對我微微一笑。她體態比結婚時更加豐腴,膚色泛紅,跟外面的天空一樣。這使我又想起躺在棺材里的黃大友,他的臉比大廳的地磚還要白。這時我心想,黃大友確確實實是死了。
前來吊唁的賓客越來越多,椅子坐不下,大部分人便站著和熟人聊天。我也加入了他們。大家談論與死者相關的話題無非以下三種:一是黃大友是個少見的好人,他死得太早了;二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三是黃大友的死因。許多人接到消息匆忙趕來,還并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于是知道的便告訴不知道的,來得早的便告訴來得晚的。傳來傳去,竟出現不同說法。有的說是心臟問題,有的說和兩月前的一次酗酒有關,有的又說他身體健康得很,只是長期壓力過大,最近又連續加班,導致猝死。真正的緣由,想必只有他妻子是最清楚的。我想去問她,可又對她心存忌憚。于是我去門外的院子里抽了支煙。
站在院中可以看到這棟樓房的墻壁和窗戶。二層正中間是黃大友和他妻子的臥室。由于位于陰面,窗戶又小,房間幾乎終年曬不到太陽。我曾問他為什么不選擇陽面,他說這里朝向公路,視野較好。我第一次見他妻子,也就是在這間臥室的門檻上。那是他們婚禮當天,人比今天還要多。聽說黃大友和一幫兄弟們都在臥室,我徑直去往二樓,在進屋的瞬間,他妻子不知何故匆忙跑出,我和她撞了個滿懷。在我向她道歉之際,她就站在我面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我。我當時就覺得,黃大友的這個老婆是一匹餓狼。
“我妻子,蔣依。”坐在床上的黃大友向我介紹,并把我介紹給她。實際上不用他說,我自然知道她就是蔣依。全場數百人,只有她穿著婚紗。“你好。”她伸出手要跟我握,我雖覺得這樣不妥,卻也沒有拒絕。于是我們一個站在門檻內,一個站在門檻外,輕輕地握了手,我感到她的手很涼。隨后她便出門而去,等她走了我才忽然意識到,她長得是真漂亮。
婚禮全程,我和她還有過多次眼神上的接觸。盡管我一直在回避,她的目光卻總能夠在人群之中找上我。后來,我竟然也開始不自覺地尋找她。她好像一枚釘子,從見面的一刻起就牢牢地釘在我的意識里。我想告訴大友,這個女人不簡單。可是即便我和他關系極好,又怎么能在他的婚禮上說這種話。我頂多發出疑問:“你們才認識兩個月就結婚,會不會太快了?”“不會。”他篤定地說,“兩個月對我們來說已經很長了。”
我能做的唯有日后盡可能不和她見面。婚禮這樣眾目睽睽的場合她都能像獵人一般時時盯著我,我難以想象假如只身來他們家作客,她會對我做出什么事來。因此,婚后他們邀請我來這套山間別墅,我都以路遠為借口推辭了。我和大友只在我家或是我家附近的一些餐館相見。他是個身強體壯的男人,毛發旺盛,新陳代謝快,平時還有健身的習慣。他死于心臟驟停,我和他的一位共同好友今天早晨在電話里這樣告訴我。這是大友的表弟告訴他的。大友的表弟則是聽蔣依所說。
“好端端的,為什么會心臟驟停?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連抽四支煙后,我把最后一支煙的煙頭踩滅,毫不猶豫地返回大廳,找到蔣依,雙臂交抱在胸前,問她。大廳擁擠,我們距離有點近,我能看到她眉心有一顆小小的痣,她揉了揉鼻子,深深吸了口氣,像是要打噴嚏,卻又沒打。這一次她沒有盯著我看,而是像個小女孩似的,背著雙手,目視一旁,說:“每個人都來質問我,我怎么知道?睡前還好好的,半夜忽然開始抽搐。我也很害怕呀。在這大山里面,前后都沒有人,救護車兩個小時才到,他早就咽氣了。我能怎么辦?都來問他是怎么死的,誰問過這個晚上我是怎么度過的?”她再說下去就要哭了,我連忙轉變態度,語氣溫和地安慰她,告訴她不要想太多,一切都會過去。
她這番話倒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她說得沒錯,人們只知道關心死者,忽視了作為生者的她的感受。這個夜晚她一定很絕望。忽然之間,我對這個女人心生憐意,以致曾經的她給我留下的印象也開始轉變。婚禮那天她的確不合常理地盯著我看,可是那又怎樣,她并沒有做出越軌的事。我對她的判斷僅僅是基于我的想象而已。至于黃大友和她的感情,一直以來都是很好的。每當他在我面前提起她,都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欠揍神態。我雖沒有結婚也沒有戀愛,但據我所知,婚后三年還保持他們這樣熱情的夫妻并不多見。于是,我想我大概對蔣依有所誤解。我回過神來,正感到對眼前的女人有些歉疚,發現她那雙熾熱的眼睛又注視著我。我本能地想要躲開。在這樣的場合和她長時間對視可不太好,可是拔腿欲走之際她忽然問我:“你是B型血吧?”
我在原地愣住。首先,我不明白她為什么問起我的血型。其次,我一時竟想不起我的血型是什么。“你是B型血。”她肯定地說,“我能聞到。”“你能聞到?”我重復了一遍。她點了點頭,說:“第一次見到你,我撞在你身上,那時候就聞到了。”我知道蔣依是學醫出身的,曾經在醫院工作過,或許她真能通過氣味判斷人體血型。此外,我已想起我的血型的確是B型,她沒有說錯。“我也是B型。”她接著說。就好像相同血型是多么了不起的共同點。
由于和蔣依關于血型的簡短交談,接下來我有意無意地將注意力放在我的嗅覺上。與他人擦身而過時,我會輕輕吸氣,讓他們身體散發的氣味進入我的鼻腔。抽煙男人的煙味掩蓋一切。大部分女人身上都有香味,有些甚至因為所用的洗發水相同而散發著一樣的香氣。少數人用了香水。有個男人眼神直愣愣的,不用聞就知道昨夜的酒氣還殘留在身上。后來我又去黃大友的遺體旁邊駐足。由于入殮時做過氣味上的處理,再加上有一層玻璃棺蓋,我聞不到死人的氣息。但是可以想象他的身體已漸漸開始散發尸臭。黃昏時分,有人提前離場,而我的車擋住了別人的車,于是我被叫出去挪車。來到路邊,山谷吹來的晚風裹挾著大量由新鮮植物和腐爛植物混雜而成的氣味源源不斷地流經我的身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種空氣,像是要打噴嚏,卻又沒打。
我的鼻子能捕捉到的所有氣味都是人體或物體表面散發出來的,任何擁有正常嗅覺的人都能聞到它們。而她是如何捕捉到流動于身體內部的血液,并分辨出它的類型?管她說的是真是假,這件行為本身就讓我感到有趣。她究竟是個什么樣的女人?我的眼睛又像當初在婚禮上一樣,忍不住地尋找她的身影。不同的是,聊完血型后的她再也不對我投來目光,她開始無視我的存在。釘入意識的那枚釘子固然造成不適,拔掉它卻更讓我感到痛苦。我在葬禮上對她的關注已經遠勝于對躺在大廳中央的亡友的懷念。許多次當我站在人群中看她,我下意識地想到血。并不是想到B型血——B型血沒什么稀奇,頂多意味著假如她遭遇意外失血過多,我的血能夠救她——而是想到血本身。把一個漂亮女人和血聯系起來,這在我生平中是頭一回。
這天夜晚,一小部分人留下來給大友守夜,作為他生前的好友,我自然也在其中。山里的夜晚本就有些陰森,在這樣的夜晚坐對一個死者,氛圍不用說更讓人害怕。盡管整棟建筑燈火通明,盡管守夜的人為數不少,盡管死者是我們熟悉之人,我依然能感受到恐懼隨著夜深而在眾人心里滋長。外面的黑夜讓我們不敢走出大廳,大廳的遺體又讓我們不敢靠得太近。我們就集中坐在靠墻的一些椅子上,要么低聲交談,要么玩著手里的手機。“哪怕住在郊區也好啊,偏要住在這么偏遠的山上。”一個人說。事實上,我知道他們夫婦選擇來這里住完全是蔣依的意思。黃大友是沒有主見的,他一切都會聽老婆的話。何況這棟建筑雖然名為小別墅,其實并不昂貴,只是在裝修上比一些山村住宅更奢華罷了。我沒有加入他們的交談,靜靜地靠在椅背上打盹,心里則不時地想著樓上的女人。經過幾乎一天一夜的折騰,她太疲倦了,因此沒有參加守夜。我在想,往后她敢一個人住在這么大一棟山間別墅里嗎?
天亮的時候,椅子上、沙發上,甚至墻角的地面上以各種姿勢歪歪扭扭地躺著我們這些守夜人。我們的身體變得無比僵硬,我想這大概是房子里有死人的緣故。女主人下樓時,我們一個個扶著腰,按著脖子,僵尸一般艱難地站起身來。我去屋外吹著山風抽了幾支煙,精神才漸漸恢復。日出后,逐漸又有人開車到來,大廳很快變得如昨日一樣熱鬧。蔣依雖然在床上睡的覺,卻也比前一天更憔悴。分發早餐時她的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片刻,眼神既沒有從前那般熾熱,也不再冷漠。她的臉頰比昨天更白,不知道是不是用了化妝品。接過早餐,我輕輕地吸氣,分辨她身上的氣味。這時我發現她胸脯微微鼓起,正做著同樣的吸氣動作。
正午時分,裹挾大量水汽的云肉眼可見地從西天漫過來,給這片剛才還陽光普照的山區帶來一場秋雨。我和許多賓客身上的衣服無法抵御驟降的氣溫,蔣依便來到我身邊,低聲對我說:“你跟我上樓,拿一些大友的衣服給需要的人穿吧。”我并不想穿大友的衣服,盡管我們是好友,但畢竟它們已經成為他的遺物。想必大廳里那些凍得瑟瑟發抖的人也和我有著一樣的想法。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蔣依說話時的那雙眼睛,忽然預感到接下來的事不僅僅是拿衣服那么簡單。我需要做個決定,到底是跟她上去拿,還是不拿。我的腦子還在考慮,我的雙腿已經老老實實跟著她走了。
一上樓,大廳的嘈雜被瞬間隔絕。世界只剩下雨聲和我們的腳步聲。大友的衣服在他們的臥室。她先進門,再放我進去,隨后關上了門。她把門關上了,這個女人。我心想,我落入她的圈套了,在長時間的潛伏之后,獵人終于要對獵物下手。“我先找一件給你穿。”她說。她從衣柜翻出一件藍色無領外套,這是大友生前常穿的,我乖乖地把它套在身上,切實聞到一股大友的氣味。我和他體格相似,衣服倒也合身。蔣依上下打量著我說:“真像他。”我望著衣柜鏡子里的我,也覺得真像他。衣柜鏡子里的蔣依忽然開始抽泣。我想這應該是看到了和大友相似的我的身影的緣故。我說:“如果你受不了,我也可以不穿。”她搖頭。我別無辦法,站在原地等她的哭泣漸漸過去。
等到我的體味和大友衣服的氣味融為一體,我開口問她:“大友是什么血型?”“和我們一樣。”她說。我接著問:“血型真能聞出來?”她沒有回答,而是從衣柜底部拿出一只口袋,讓我幫忙張開袋口,她再把衣柜里大友的衣服一件件取出來放入袋中。她躬身放衣服時,脖子上一枚紅色吊墜隨著身體動作左右搖晃。“早上拿早餐的時候你不是聞過我了嗎,能聞出來嗎?”她抬起頭看我,手里的動作則沒有停。我坦言我只能聞到洗發水之類的香味。她沖我笑了笑,“這就跟調酒師聞酒一樣,不僅要對酒敏感,還需要后天的練習。你再聞聞看。”說著她把右手伸過來,手心對著我,讓我聞。我吞了一口口水,鼻尖湊近她的手心,在大約一厘米的距離停住,吸氣。“不是讓你聞手,聞我的手腕。”她說。我聽從吩咐,又將鼻尖移到腕部。一股輕微的年輕女人肉體的香。
“血的氣味是掩蓋在體香之下的,要仔細辨別。”她緩緩地說。我聞過暴露于空氣中的血液,有鐵腥味,但我未曾聽說直接從人體皮膚上就能聞到血味。“酒就算密封在壇子里,酒香還是會溢出來。血管里的血也是一樣。聞到不同了嗎?”她將手腕湊近了些,搭在我的鼻尖和嘴唇之間。除了感覺到她皮膚的涼意,我笨拙的鼻子此時連原有的體香也聞不到了。她的手臂已經舉累,便放了下來,繼續耐心地說:“不同部位,聞到血味的程度也不一樣。手腕就比手心更強烈,因為這里有動脈。比手腕更強烈的地方,一個是脖子,一個是大腿內側。也就是頸動脈和股動脈。”她再次抬起右手,用中指和無名指摩挲著她脖子右側的動脈部位。“就是這里,聞聞看。”我猶豫了一下,把鼻子湊了上去。身高原因,我需要低下頭才能夠到她的脖子。她則將腦袋微微抬起,她的脖子完全暴露給了我,我的脖子也交給了她。我們沒有擁抱,身體其他部位也沒有接觸,只是像天鵝繞頸似地嗅著彼此的氣息。我沉醉于那股女人香,哪還有心思去分辨什么血液氣味。而她的鼻息噴在我頸部皮膚上,像注入致幻劑一般,使我一時間忘了身在何處。
是衣柜的鏡子提醒了我。當我側眼看到里面那個酷似黃大友的身影和他老婆曖昧地站著,我的肩膀微微后撤了一下。她察覺到了,于是我們的脖子彼此分開。我心想,沒有分辨出血液味道,她該不會又讓我聞第三處動脈吧。她看我一眼,目光漸漸下落,繼續收拾起大友的衣物。“你聞不到也正常,”她說,“我對血的敏感是天生的。這有遺傳因素,我媽媽就是這樣。我和大友沒有小孩,如果有,很可能也這樣。”她聲音有些虛弱。我不知道她所說的“這樣”僅僅是指對血液氣味的敏感,還是指別的什么。“能聞出人的血型,這也沒什么用吧?”冷靜下來的我故作嚴肅地說。的確,我不覺得這是什么了不起的技能。“你不明白,這是很痛苦的。血液好像是我的另一種感官。體內的河流。有時候我能感覺到它們的流向和流速,也能感覺到哪里流動得不通暢。另外,它們對同類型的血常常會有渴望。這可比性欲什么的強烈多了。好了,我們把衣服給他們拿下去吧。”她收完衣服便不再說下去,使正聽得津津有味的我一時還不能回過神來。我像她的傀儡似的拎著那包衣服,跟著她緩緩下樓。
穿著那件藍色無領外套,他們都覺得我像極了黃大友。“我以為大友復活了。”“真好像他們兩夫妻從樓上走下來。”有人開玩笑說。大廳里的氣氛竟變得歡快起來。由于我已經給他們打了樣,大家就不覺得穿死者的衣服有什么忌諱。再加上天氣的確很冷,他們紛紛排隊拿衣。于是大廳里出現許多個黃大友。站著的、坐著的、走來走去的。其實他們都并不像他,只是我把他們想象成他了。至于真正的黃大友,依然靜靜地躺在那層透明棺蓋下,毫無知覺地等待著自己的下葬時間。
除了黃大友,所有人的血都在體內流動。那些血類型不一,健康程度也有所不同。在這群人當中,她只對我產生興趣,還是對其他同為B型血的人也有著一樣的興趣?這種據她所說比性欲還強烈的血液對血液的渴望,到底是一種什么感覺?這種渴望要如何滿足?她只渴望男人的血,還是對女人也如此?當我再度站在角落偷偷觀察她時,我并沒有發現她對別人有著那種盯住不放的眼神。不知什么緣故,這讓我的內心好受一些。此外,我注意到她在與人交談時喜歡用手摸自己的脖子,這和她的血液渴望有關嗎?還是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習慣性動作?
由于昨夜沒有睡好,而今晚還要繼續給大友守夜,我在她的提議下去三樓的客房睡了一覺,并舒舒服服地洗了個熱水澡。我睡了近兩小時,醒來后發現自己是勃起狀態。這沒什么稀奇,但我想今天的勃起可能跟我和她天鵝交頸的姿勢有關。我靜靜地躺著,什么也沒有做,等待我的器官恢復正常。勃起是血液的涌入,我想,這么說來,性欲倒也是一種血的渴望。血這種平時不會被想起,對生命而言不可或缺,流出體外則會讓人產生生理不適的物質,此刻讓我感到它不再簡單地作為一種人體組織而存在,它有它自身的性格、感覺,甚至思想。
我懷著這些念頭起身洗澡,隨后穿好衣服走出客房。走廊盡頭有一段通往樓頂天臺的樓梯和一扇紅漆門。我推門而出,才發現雨已經停了,太陽出現在西山。仿佛一個人大哭了一場,臉上重又恢復平靜。天臺和樓下房間一樣沒有植物,住在這種方圓數十里全是植物的地方,根本不需要再養什么花花草草。地面濕漉漉的,在夕陽照射下略有些刺眼。我想起曾經蔣依出國游玩時我來這里小住了一星期,某天夜晚正是在這天臺上和大友喝啤酒到深夜。妻子離開幾日,對已婚男人而言通常是一件快樂的事,大友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大友尤其如此。我能看出來那個星期他極其放松,他大吃大喝,大肆娛樂,放縱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可是沒過幾天,他又開始想她,像個男孩似的受不了沒有她的日子。現在她沒有他了。大多時候她倒顯得很平靜,除了我剛換上那件藍外套時她低聲哭泣,我沒有再看到她流過眼淚。這幾天她的反應,一點也不像丈夫剛剛離世,倒像是他已經死了多年。
晚飯后,天色很快暗了下來。大部分賓客散去,留下一定數量的守夜人。有了昨晚的過夜經歷,我們對這山間夜晚的黑暗和孤寂沒有那么害怕了。這次有人準備了撲克牌,他們在大廳墻角支起一張桌子,興致勃勃地開始打牌。我對此沒有興趣,便又獨自來到天臺抽煙。正值陰歷月中,月亮渾圓巨大,用肉眼就隱隱可以望見表面的斑紋。在它的光照下,附近黑森森的山巒顯得格外分明。盡管天地之間一片寂然,我卻總覺得那些樹影當中有許多雙未眠的眼睛。
紅漆門被推開,蔣依抱著一籃衣服來到天臺。“你怎么一個人在這里?”她首先看我一眼,接著抬頭望向月亮。我沒有回答她,而是說:“山里的月亮就是和市區不一樣啊。”她笑了一下,開始晾衣。那些是白天客人們穿過的大友的衣服,她把他們全都洗了,好像大友還會再穿似的。“明天忙起來就沒空了,這些事情只能晚上做。”她說。我上前幫她,她將衣服套在衣架上,再由我掛上晾衣繩。我們之間彌漫著洗衣液的氣味,從中也偶爾能分辨出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體香。晾完衣服后她對我說:“你的煙能不能給我一支?”她不是吸煙之人,這我能判斷。我問她要煙干什么,她說她想試一試。我明白不會吸煙又對煙懷有好奇的人的那種感覺,于是給她點上一支。打火機火苗發出的光把她的臉短暫地映紅了,緊接著那張臉又被月光霸占。我告訴她不要過肺,吸到口中再噴出就可以了。隨后我給自己也點上一支,我們一起抽著煙,默契地走向天臺另一端,那里有一塊可供坐下來聊天的水泥臺面。
我告訴她,去年夏天我和大友曾在這里喝啤酒到深夜。她說她知道。“我從來都不讓他喝酒。我回來后他本來想隱瞞的,但我從他的血液里面感覺出來了。”我首先微微一愣,轉而又覺得不足為怪。既然她連血型都聞得出來,聞出血液中的酒精應該也不難。“不是通過聞的,”她卻說,“是我的血感覺到的。他的血進入我的血,我的血覺得難受,有刺激感。那天我還罵他了。其實他沒做錯什么,但他還是只顧著道歉,也不知道還嘴,這個人。”
我并不關心大友做沒做錯、還不還嘴,我只想知道他的血進入她的血是怎么回事。我當然也清楚她故意不說明這件事,就是等著我問她。我也如她所愿地問了。于是她在說“你真的想聽嗎”并得到我肯定的答復后,對我講了一件她十九歲的遭遇。那時她父母開餐館,有天晚上兩撥顧客醉酒后在店里斗毆,她被無辜傷及。“送到醫院的時候已經休克了,但我還有意識。我以為我要死了。這時候他們給我輸血。我說了,血是我的另一種感官。那是生平第一次我這種感官被滿足,它一滿足,連傷口都不覺得疼了。我當時渾身發抖,他們以為我冷,其實那只是興奮。我能感覺到他們給我輸的是一個男人的血,而且是中年男人,但他是誰我就不知道了。那是血庫里的血。”
講完十九歲經歷,她又向我要了一支煙,這次我沒有陪她抽,只是看著她抽。“后來我學醫,就是這個原因。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讓我體內的血再得到滿足了。有好幾年的時間我懷念那種滋味,但再也沒有機會讓人給我輸血。我甚至想過割腕,但我不能保證在死之前能被送到醫院。這樣風險太大了。直到我進醫院工作,那段時間真是在天堂一樣。頻繁的時候我每天都會。我給自己注射了太多人的血,什么樣的人都有。但偷血庫里的血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我最后還是被發現了。”這時候,我已明白大友的血進入她的血是怎么回事。我感到一陣惡心。想起此刻仍躺在樓下大廳的大友,他煞白的皮膚仿佛不是由于死亡,而是由于被她一針一針吸干了血液。可當我略微轉頭看到她的臉,我又被她冷冰冰的美懾住。不管是周遭黑森森的山巒,還是藏匿于樹叢中未眠的眼睛,還是她所講述的嗜血經歷,都使那種美不同凡響。
既然血液的滿足比性滿足還重要,血型便成了她首要的擇偶標準。她繼續講,在大友之前她還曾談過三任男友,他們很愛她,她也愛他們。可他們都無法接受為她提供血液。“人血又不是不能再生,何況我每次需要的血比獻血站抽血還少很多。但是他們,他們三個,沒有哪個不是臨到我說要抽點血的時候就落荒而逃。只有大友,只有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的血分享給我。一開始他也抗拒,但我告訴他,如果我們的血不在我體內交融,我就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他權衡之后,說可以試試。其實,血的交融不光能滿足我,供血之人也能得到滿足,所以,后來他也上癮了。他的血有很強的嫉妒心,這我能感覺到。可能是嫉妒在他之前進入我體內的那些血吧。因為嫉妒,他給我的血比我實際需要的更多。有時候我都沒有欲望,他還是每天抽一小管給我。他想霸占我,我也需要他。只可惜啊,只可惜,我好不容易找到可以跟我交融的人,命運又把他帶走了。”
她在說這番話時,原本注視著我們正前方的圍墻,而當她說完大友被命運帶走,她轉過頭來,目光移向我。我們短暫對視了一下,這一刻我渾身血液似乎加快了流速。它們感應到了身旁這個女人體內仿佛具有至高無上地位的血液的存在。如月球引發潮汐一般,我的血不可阻擋地想要向她的血奔涌而去。她當然也感覺到了,只是我和她一時都難于開口。我給自己點了支煙,問她還要不要,她搖頭。她雙臂抱著膝蓋,又望著遠處的樹影,說:“大友從兩周前開始,就說他胸口不舒服。雖然去醫院檢查后沒發現什么毛病,但我還是讓他不要再抽血了。所以,已經有兩周,我的血沒有被滿足過。這兩天家里又來了那么多人。那么多B型血,聞到它們的氣味,對我來說確實是一種煎熬。”
“你如果需要,我可以給你。”在我的嘴巴說出這話后,我的腦袋才開始思考。盡管沒有證據表明黃大友的死與長期的抽血行為有關,但同樣沒有證據表明二者無關。何況根據蔣依的描述,向她供血也會成癮。貿然答應她,是一件危險的,甚至最終可能致命的事。但轉念又想,不就是抽一次血,沒什么好怕的。借此才能夠看清她所說的血的交融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才能夠知道我的亡友這三年和她過著什么樣的日子。在我思索之際,她已經從樓下拿來一只銀色醫藥箱。箱子不重,里面簡單地放著未拆封的針管,針頭、棉簽、碘酒、止血帶、創可貼,以及一些看不清名字的藥物。
整個過程,她的左手都抓著我的手腕,生怕我跑掉似的。至于那只右手,其嫻熟和迅速程度令我驚訝。綁止血帶,擰開碘酒瓶蓋,用棉簽在我臂彎靜脈處消毒,拆開針管包裝,彈掉針頭上的塑料保護套,精準地扎入我的血管,抽取她認為適量的血,這些全由那五根靈活手指一氣呵成地完成,中間沒有絲毫停頓。我甚至還未反應過來,我的血已經到了她的針管里。她又遞給我一根棉簽,讓我自己按著針孔處。十毫升左右,我的血,在月下呈半透明的深紅色。她沒有給我時間多看幾眼,快速更換針頭,將她的戰利品注射到自己的血管。
隨后,她開始深深地吸氣,并且大口呼出,像是某種病癥發作的前兆。在她的影響下,我也不由得做起深呼吸。我們面對面坐著,醫藥箱礙事地放在我們中間。現在,我身體的一部分進入了她的身體。哪怕僅僅是十毫升,可那十毫升不是無關緊要之物,而是從我心臟流出的,象征著生命的血液。用她的話來說,那是五官之外的另一種感官。于是,我摒絕其他感官,僅僅用我的血去感受。那十毫升血液猶如壁虎截斷的尾巴,雖脫離身體,卻依然短暫地活躍著。它們進入她的血管,并向我傳來那里的訊息。她體內奔涌不息的血液之河,微涼、詭譎、暗無天日,很快就將我的血吞噬。這時候,她一屁股將醫藥箱擠開,挨我而坐,并像瞎子一樣摸索著握住了我的手。像她描述的自己第一次被輸血時的狀態一樣,她開始渾身發抖。于是我不僅緊緊回握住她的手,還用另一只手臂抱住她。她的抖動不規律,時而輕微時而劇烈,偶爾還像性高潮時的痙攣一樣。我抱著她,一時分不清進入她身體的究竟是我的血液還是精液。她額頭有些濕潤,手上皮膚也不像先前那樣冰涼。我能夠明白為什么供血者也能得到滿足。我想,有三年時間在這遠離人群的山腰居所享受深入血液的滿足感,縱然暴斃,大友倒也不虧。
自始至終,她一句話也沒有說。直到身體恢復平靜,她疲倦地睜開眼睛,對我淺淺一笑。我們的手繼續牽著,彼此都沒有松開的意思。“尼古丁的氣息很重,你抽煙很多年了吧?”她如此評價我的血。我原以為她有嫌棄之意,她卻說她喜歡這種氣息。接下來,我問她一些關于血液的醫學問題。比如長期抽血是否對身體有害,長期被輸血又會怎樣。她告訴我,只要適量,兩者都沒有問題。人的身體會自己調節。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事實,還是想把我作為她今后的抽血對象才這么說。“大友是先天體質問題,你別以為他是被抽血抽死的。”她說。提到黃大友,我心中生起一股小小的羞愧之情,但這羞愧旋即又被我對他遺孀的占有欲取代。我嫉妒已經死去的他,我想把她占為己有,這對我而言并不困難。她需要我的血,我也享受以血供養她的感覺。我們可以依然生活在這套山間別墅,大友死后,所有資產都是她的了。至于旁人的閑言碎語,我是不在乎的。假如她在乎,我們大不了晚幾年結婚。這些想法我并未向她表露。但我知道此刻她心里所想和我想的一模一樣。
夜越來越深,為保證她睡眠充足,我們起身離開天臺。到二樓時我們撒開手,她回臥室,我前往大廳。專心打牌的人們沒有注意到下樓的我,只有一個站在旁邊看牌的人扭頭問我:“你去哪了?”我回說:“我在樓頂看月亮。今晚月色是真不錯。”他敷衍地笑了一下,注意力又回到牌局。我走向大廳另一頭的沙發,經過大友的棺木時低頭看了一眼。他在笑,被我得知生前秘密的笑。我也在笑,在他的葬禮上和他老婆曖昧不清而產生愧意的笑。
我倒在沙發上開始睡覺。一整夜,我時而做著不安的夢,時而又感到極致的愉悅。由于他們徹夜打牌,我睡得很不安穩。在某個醒來的時刻,我迷迷糊糊地看到大友也站在看牌的人群中。他左手搭在另一人的肩上,右手對著牌局指指點點。被他搭著的那人專心看牌,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我坐起身來想看個清楚,這時他發現我醒了,便朝我走過來。“真有意思,比前幾年打得還爛。”他說。我說:“你不好好躺著,干嗎起來?”“還不是為了你?我得跟你說一聲,自己身上的東西自己用就好了。她其實根本不需要。你懂嗎?給她給慣了,你倆都會被害死。”我茫然地聽著這番話,心想,這是大友嗎?生前的他可不會用這樣叮嚀的語氣跟我說話。我仔細打量他,他說:“我就這么一說,聽不聽由你啊。我看打牌去了。”他走后,我又倒在沙發上,一覺睡到天亮。
天剛亮起,鳥就不止不休地開始鳴叫。她下樓時,目光在眾人之間穿梭。我知道她是在找我。我繼續坐在沙發上,故意低下頭,裝作沒有看見她。隨后她來到我身邊,問我早餐想吃什么。我抬頭望她一眼,告訴她我想回家吃。我不敢看她接下來對我投來的關切眼神。她問我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上樓休息。我說我一切安好,只是想回家了。她賭氣說:“那你回去吧。”這樣一來,我越發感到不忍。有半分鐘的時間我動搖了。我想,只要我們兩廂情愿,死又有什么好怕。但是半分鐘后,我就無恥地對她說:“有些事情我還需要考慮一下。”事實上,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只是對她的說辭還是我真的會考慮。她說:“我站在你面前你都無法決定,更何況你走了以后呢。”我覺得這話沒錯。
大廳的人多起來了,我們不能這樣對峙下去,會被人看出來的,何況她還要給一部分守夜人準備早餐。沒過多久,我點了一支煙,假裝去院子里抽,在鵝卵石小路上停頓片刻,回頭望一眼大廳,接著像個心虛的逃兵故作從容地走向公路。進入駕駛室,一種深入血液的安全感將我包裹。我把車從路邊開到路面,輕踩油門,一路向山下駛去。
責任編輯 晨 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