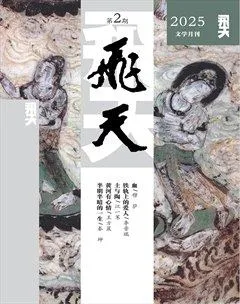黃河有心情
1
黃河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自古以來,這條聞名于世的大河,哺育了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寫道:“千流萬派,同歸黃河之源;玉振金聲,盡入黃鐘之管。”黃河之于中華民族,意義之重大,毋庸贅言。
日常生活中,會有很多司空見慣的事情。恐怕很多人都沒有認真、深入地想過“黃河”二字,對我們每個人,究竟意味著什么。一個“黃”,一個“河”,簡單組合,看上去顯得那么普通。有時我會不禁對自己發問,這條黃色的渾濁不堪的滔滔大河,究竟跟我們有什么非常密切的關系?
我敢肯定,相當長的時間,我并未感覺到黃河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有多么重要。它甚至不如我家鄉門口,名不見經傳的萊河和大沙河。至少我曾站在這兩條小河的岸邊,看見過有人在河里游泳,撈取河里的苲草。偶爾下到河里,會止不住捉到大魚的想象,并為之激動。而過了那條大沙河,我會走到一個叫李雙樓的村落。那是我的外祖家。
我切身接近黃河,是在1990年,因為我從一座小縣城,調到了黃河入海口的東營。也就是說,我來到了黃河尾閭。腳下的土地,是由黃河攜帶的巨量泥沙沉積而來。
宋代詞人李之儀《卜算子》寫道:“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從這一年起,我則在黃河尾,生活了十九年,而在萬里之遙的黃河頭,則不知其為誰。這就成了“誰住黃河頭,我住黃河尾”。
從黃河尾,來到濟南,依然與黃河相伴。
在這十九年間,我多次跨越黃河,目睹了黃河的浩浩蕩蕩和靜水流深,見證過大旱之年的黃河斷流。大水泛濫的時節,我還參加過黃河岸的抗洪救災,坐著飛馳的汽艇,穿行在黃河灘上被洪水淹沒的村莊。
對我觸動最大的,是有一天,我站在了干涸裸露的黃河底,頭上長天遼闊,萬里無云,像是個倒懸的大海,而又藍得像灌滿了濃濃的藍墨水。
此情此景,令我不禁想到古往今來、民間廟堂所發出的那些錚錚誓言,實實的就是“海枯石爛終有時,黃河見底亦尋常”。
2
自然而然,黃河的形象也出現在了我的小說中。
據記載,1935年7月,黃河在魯西鄄城決口,讓菏澤、巨野、濟寧、金鄉、定陶等十幾個縣的良田和村舍一夜之間化為汪洋。成千上萬的災民,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統一調遣下,紛紛向黃河尾閭遷移。
我的小說《地嘯》中的主人公羅得寶、宋蘭香、老蕭、老黑,都是魯西南無數災民中的一員。這些災民散布在黃河尾閭大片無主的土地上,開墾田地,創建村落,繁衍子孫。日本人來了,他們不屈不撓,奮勇抗日,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動人詩篇,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民族精神。
在東營工作期間,我還創作了小說《貓樣年華》,講述山東大學一位老教授的坎坷遭遇。小說取材于真實人物。因遭受不公正待遇,公石蘭教授在黃河尾閭的黃河農場,度過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艱難歲月,與一只叫“花兒”的母貓,結下了超越現實的不了情。多年后,海晏河清,白發蒼蒼的老教授返回山大,但仍對往昔的歲月難以忘懷。忠于感情的“老義貓”,帶領自己的無數兒孫長途跋涉,趕來與老教授在濟南相會,死后被老教授埋葬在黃河灘上。
小說中寫道:“公石蘭在黃河灘上葬掉了老花兒。他覺得老花兒的靈魂不會孤獨。這湯湯的黃河水,日夜不息地流動,很能夠解除她的寂寞。”
如果老花兒愿意,她的靈魂也可以沿著黃河,順流而下,回歸故地,而永不迷路。
近現代涉及黃河的小說作品,我特別注意到了《老殘游記》。在小說第十三回,通過小說人物翠花講黃河,“三天兩頭的倒口子”。有南方才子對撫臺大人指出黃河水患的原因就是河道“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堤。”此計一出,撫臺大人便起意,讓堤里的百姓“搬開才好”。
隨后,依作者劉鶚的話講,在場的“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旦大人們”便出餿主意:“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堤埝中間五六里寬,六百里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那還廢得掉嗎?”
從這段描寫,我們看出黃河給沿岸民眾帶來災難,常常就是小說中通俗的“倒口子”,就是決堤,同時也會發現當時清政府對黃河治理的方略,莫衷一是。
劉鶚是一位清末的小說家,但在水利方面也卓有建樹。他結合自己治理黃河的實踐經驗,著有《治河五說》《三省黃河全圖》等水利專著。顯然他不贊同小說中政府官員在黃河治理中不顧百姓死活的做法,并給予猛烈抨擊,憤怒地稱那些人云亦云的“總辦候補道”為“王八旦人們”。
接下來,小說敘述,“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堤,在濟陽縣南岸,又打了一道隔堤。”感嘆“可憐俺們這小百姓哪里知道呢!”六月里,汛期一到,百姓果然遭殃。這兩道隔堤,就是“殺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小說中寫道:“只聽人說,‘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埝上的隊伍不斷地兩頭跑。那河里的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埝頂低不很遠了,比著那埝里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
劉鶚借助人物之口,給我們生動描寫了百年前黃河泛濫時官民搶險救災的真實場景:“到了十三四里,只見那埝上的報馬,來來往往,一會一匹,一會一匹。到了第二天晌午時候,各營盤里,掌號齊人,把隊伍都開到大堤上去。”而堤內百姓察覺災難到來,倉皇搬家。“誰知道那一夜里,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嘩啦,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里,呼的一聲,水就進去,驚醒過來,連忙是跑,水已經過了屋檐。”
當時的情景是“天又黑,風又大,雨又急,水又猛”,多少百姓陷于澤國,死于非命。劉鶚以小說之筆,將這人間慘劇帶到讀者面前,令讀者讀后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現當代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描述黃河所流經的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直接書寫黃河的作品,也有一些代表性作品,比如李凖的《黃河東流去》、馮金堂的《黃水傳》等。這兩部作品均以黃河為題材,表現黃泛區人民的生活。
1935年的那場大水之后,僅僅過去三年,黃河沿岸就又發生了一次大水:1938年,日本侵略軍進入中原,國民黨軍隊為阻滯日軍南下,炸開河南境內黃河花園口大壩,淹沒了豫、皖、蘇三省四十多個縣。
除了這兩部作品,另有魏世祥的《水上吉卜賽》,則對黃河具體的形態,展開描寫,把黃河塑造成為一條“文化之河”“道德之河”。在這部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各種灘,嫩灘、硬灘、暗灘,可以看到不同季節的河。三部作品中的《黃河東流去》,曾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相對另外兩部,傳播范圍更為廣泛。
黃河本身是一部說不完、道不盡的“活”歷史,是小說家挖掘不盡的文學寶藏,因此也就有了小說家筆下層出不窮的“黃河故事”。河南作家邵麗的《黃河故事》,直接以“黃河故事”命名。小說敘述了黃河岸邊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故事在南方和北方、深圳和鄭州之間來回跳躍。
這幾部作品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的作者,都屬于河南作家。由此可見,黃河在流經中原地區時,給中原地區留下的印跡之深。濃厚的黃河情結,一次次讓他們的目光,深情地投向了這條氣勢雄渾的母親河。
而在山東,也有這類直書黃河的作品。比如從黃河灘區走出的作家羅珠,90年代曾寫過長篇《大水》。這部作品敘述了黃河入海口地區150年間驚心動魄的水患史、生生不息的家族發展史和多災多難的民族生存史。
另外,我曾經閱讀過一部更是少為人知的長篇《黃河咒》,出自山東作家王樹理。這部作品敘述了黃河入海口地區,艱苦卓絕的黃河安瀾史。我在小說評論《安瀾戲里的生死場》頭一句話就是:“歷來寫到黃河的小說,一定會是沉重的小說。”并認為這簡直是一個令人無比憤恨的邏輯。
但事實上,小說里的黃河常常跟災難聯系在一起。我曾這樣寫道:“黃河無知無識,卻仿佛一道不可破解的咒語,將黃河沿岸的生靈,掌控于自己無常的喜惡之間。”
在這篇評論中,我將生活比喻為一條氣勢雄渾的大河。這條大河“狂暴兇悍,不容任何人跟它講道理。它完全地服從于自身的欲望,摧枯拉朽,一瀉千里”,也正是黃河的客觀寫照。
3
河流常被視為文明與文化的源頭。在世界上每條重要的大江大河的流域,都誕生過成就輝煌的文學名著,諸如《靜靜的頓河》之于頓河,《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之于密西西比河。
大約在1987年,我從《文藝報》上看到了一幅改編自《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舞臺劇劇照,兩個小伙子手持船槳,站在船上引吭高歌,而舞臺劇的名字就叫做《大河》。那時候,我才對這部名著與河流的關系,似有所悟。
不得不說,能與黃河相匹配的優秀小說作品,數量還不夠多。與古往今來黃河在詩歌里的華章相比,反映黃河題材的小說作品,藝術光彩也要暗淡得多。
從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與黃河有關的詩篇。我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有人注釋,說是在講黃河水清澈見底。古籍有載:“黃河斗水,泥居其七”。我好像對這個“清澈見底”有點懷疑。難道兩千年前《詩經》吟誦的,跟我們現在所認識的不是同一條河流?
同樣對漢樂府詩《相和歌辭·公無渡河》,它短短的十六個字,“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也有類似的一點疑問。這首詩明白簡潔,但既有悲劇精神,也有悲壯色彩。渡河。不要渡河。竟渡河。人死了。奈何。回環往復、纏綿凄惻、沉痛莫名。它被稱為歷史上最悲壯的古詩,還是有其道理的。
在樂府中,我們可以清晰聽到黃河的水流聲:“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漢樂府《公無渡河》之后,李白又寫出《公無渡河》“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之句,可以讓我們再次感受這支狂放而怫郁的悲歌。他的《公無渡河》,音韻氣勢磅礴,甫一下筆就寫出了萬里黃河的無限聲威,用詞激切,活畫出黃河奔突的雄奇之境,又揭示出它的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帶有了更強烈的悲劇色彩。
在唐代詩人中,李白寫黃河的詩句品質之高,令人驚嘆。在《行路難》中,他寫道:“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唐代詩歌,提到李白,更少不了詩圣杜甫,他在《故武衛將軍挽歌三首》中寫:“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白居易《新沐浴》寫黃河:“是月歲陰暮,慘冽天地愁。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還有他的《雜曲歌辭生別離》:“回看骨肉哭一聲,梅酸蘗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云秋,行人河邊相對愁。”
更有李賀《北中寒》:“一方黑照三方紫,黃河冰合魚龍死。”全詩寫一方灰暗,三方天色皆成紫。黃河冰凍,魚龍皆死。百石大車上路,能在冰面行駛。霜花降落衰草,揮刀舞劍向天,難割破灰蒙蒙天色。海上波濤回旋激蕩,積冰嘩嘩作響。山谷瀑布凝結失聲,如白虹懸半空。北方的寒冷之情狀,撲面而來,令人不寒而栗。
其他諸如“黃河直北千馀里,冤氣蒼茫成黑云”“塵沙落黃河,濁波如地翻”“黃河九曲今歸漢,塞外縱橫戰血流”“百戰無功身老去,羨他年少渡黃河”“黃河晚凍雪風急, 野火遠燒山木枯”“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三春白雪歸青冢,萬里黃河繞黑山”,不勝枚舉。
縱觀這些詩作,無不與愁苦、蒼涼、蕭瑟、艱困有關,有一種悲寒的基調。但是,我們還可以欣賞到許多豪放、雄渾、壯麗的詩篇。魏晉阮籍在《詠懷》中寫黃河“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隨后有“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的發問,峭拔高昂,一掃陰郁萎靡之氣,抒發了詩人的豪情壯志,認為人要以自己的積極作為,擺脫人生的榮枯,而忠義和氣節,也足可以根本上超越生命之短暫。阮籍為三國時期的“竹林七賢”之一,這種建功立名、兼濟天下的人生志向,著實可貴。
到了李白那里,對黃河書寫的浪漫主義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像“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可謂婦孺皆知。
在《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中,他寫道:“西岳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你不是說黃河洶涌澎湃摧枯拉朽嗎?但在李白眼里,此刻則是“黃河如絲”的表現。可接下來,卻是黃河觸動了巍峨山岳。這首詩以大地山河與神話的巧妙結合,將華山和黃河描繪得氣象萬千,運筆收放自如,創作出了奇幻飄逸的境界。
《贈裴十四》是李白贈別一位超凡脫俗之人裴十四。此人據說儀容俊偉,光彩照人,人稱“玉人”。“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黃河之水天上來,一瀉萬里,流入東海。寫奔騰的黃河水,也是寫裴十四寬廣宏大的胸懷。本是一首憂傷的送別詩,被李白寫得氣吞山河,豪邁奔放,灑脫不羈。李白如此寫裴十四,直令人不禁暗生親目瞻顧之意。
同是唐朝大詩人的王維,多詠山水田園,詩作風格清新淡遠,自然脫俗,“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在描繪自然美景時,又流露出閑逸蕭散的情趣,但他在寫到黃河時,也有飄灑自由之情思。在《送魏郡李太守赴任》,他寫道:“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天外。”即便賈島這樣的苦吟詩人,有時也會豪放一把:“幾歲阻干戈,今朝勸酒歌。羨君無白發,走馬過黃河。”(《逢舊識》)身是龍鐘白發人,猶羨走馬過黃河,人老心火不滅。
像“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曾向黃河望沖激,大鵬飛起雪風吹”這樣的詩句,都包含了詩人掩抑不住的壯志豪情。詩人的胸懷有多大,整個世界都不夠充滿,所以我們一再看到“天外”這個表述,從李白,到王維這樣的大詩人,再到叫不出名字的小詩人。后兩句潛臺詞好像是說,老子也曾闊過。這個“闊”應該是類似“英雄闊大寬宏量”。
既是討論寫黃河的詩作,不能不提到煥之《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這是寫黃昏時的景象,以樸素淺顯的文字,縮萬里于咫尺,大寫地描繪出了北國河山的磅礴氣勢和壯麗景象,意境深遠,結合后兩句,鮮明表達積極探索和無限進取的人生態度,千百年來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其家喻戶曉的普及程度,好像一首兒童詩。
要論壯闊雄奇,我覺得應該首推這兩句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讀此詩,有胸襟浩蕩之感。一個詩人的世界,既能容納天,也能容納地。其境界闊大,氣象雄渾,直如李白講“萬里寫入胸懷間”。這就是詩人的胸懷。此詩出自王維之手,出自這位思接天外的絕世天才。
民間諺語,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黃河信有澄清日,后代應難繼此才。”詩歌里的黃河,也常和誓言、信念、宇宙的終點有關。
五代佚名《菩薩蠻》中寫:“枕前發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把鮮活的生命與永恒的天地日月做對比,表意潑辣直露,熱情奔放,激動人心,體現了一種堅定忠誠的人性品格。
為什么當年我站在干涸的黃河底,心靈會受到強烈震動?就是因為干涸的黃河讓我有了一種走到時間盡頭的感覺。
如此看來,所謂永恒,也沒有絕對。我們的世界在發生驚人巨變,現實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但這并不妨礙詩人們繼續以各自的詩句和想象,表達他們不同的生活觀、世界觀、宇宙觀。
王昌齡的兩首《橫吹曲辭·出塞》,其一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首詩互文見義,給了不可捉摸的時間,以具體可感的形象。明代詩人李攀龍,贊它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前人也多言“秦時明月漢時關”,從千年以前、萬里之外下筆,“發興高遠”,最耐人尋味,我卻最喜其二中的“黃河水流無盡時”之句。
多少男兒戰死沙場,人間悲劇頻繁發生,和平安定的生活,只存在于人民的想象。我們嘗試著將兩首出塞詩連在一起,就像電影里的鏡頭一轉,“白花垣上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
于是,我們看到黃河東流,滔滔依舊,既可做思念的象征,也可做時間的寫照。在時間的永恒面前,征戰殺戮,成敗功名,都付與了土。詩人的情感和思想,或可藉此得到超然于世的表達。
“古來黃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道變通津,滄海化為塵。”這幾行元代的詩句,也借黃河,道盡世事滄桑之感。而在“黃河日日水東流,斷送卻、英雄多少”的感喟中,又隱含了許多生命的悲憫。生命短暫,河水流長。這位詩人以“萬事付之一笑”的達觀和高潔,面對歷史興衰、人生沉浮,給讀者提供了豐富的人生啟迪。
4
除了小說、詩歌,在散文、戲劇等文學體裁以及民間傳說中,書寫黃河的作品,同樣數不勝數。古往今來的作家、詩人們,在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的奔騰與沉淀中,孜孜以求永恒的價值,探尋深刻的人生哲理。經過無數作家、詩人的奮筆疾書,對黃河的認知逐漸化為一種原型意象,具有了人格化,從而凝聚了中華民族心理、性格的共同因素。
世界文明史上,曾發生過文學成就一個民族的事例。一個弱小的民族憑借他們編纂的一部關于自己文明的文獻《圣經》,團結一致,固守古老的民族傳統,于破壞和蹂躪中重建家園。而我們歷代的作家詩人們,努力在文學中營造生動的黃河意象,所展現出來的生命情愫,又演繹出生命之美,傳達生命之憂,千百年來一直激勵著中華民族昂揚向上,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我們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完善。
黃河西出昆侖,流淌至今,我們每個人的成長仍在直接或間接地承受著這條大河的浸潤滋養。
美國著名詩人艾略特,在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序中指出,馬克·吐溫寫作這部小說,“有兩個要素經過他的敏感和經驗的駕馭,構成了一部偉大的作品:這兩個要素就是那個孩子和那條大河。”哈克貝利·費恩給予這本書以風格,大河則給予這本書以形式。
同樣道理,中國文學史上那些書寫黃河的杰作,也是作家以個人認知給予的風格,黃河給予的形式。黃河,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流淌著我們民族精神的一部《圣經》。
世所公認,黃河乃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有人講得好,黃河的根,不僅在巴顏喀拉山,不僅在源頭,還在大海。也就是說,這條根一頭扎在黃河頭,一頭扎在黃河尾。
文學中的黃河入海流,絕不是消失。黃河的全部,既包括它的開始,也包括它的結束,既包括動,也包括靜,既包括它的九曲十八彎,也包括它的飛流直下。在它身上,有悲愁郁結,也有豪邁曠達,有焦苦哀怨,也有勇敢抗爭,有蒼涼蕭瑟,也有雄渾壯麗。正是這些情感元素,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性格。
有人說,真正的高人,光而不耀。黃河洶涌澎湃,流經萬里,在流入大海之前,漸漸平靜下來,就像一個絕世高人,把鋒芒斂藏不露。黃河有心情。杜甫《秋詞》中說:“心平能愈三千疾。”又有人說:“心靜可通萬事理”。靜,是一種力量。
靜水流深,對人來說,也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對中華民族性格來說,從容有度,肯定是一種成熟的標志。
責任編輯 趙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