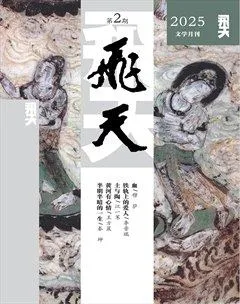高臺印象
弱水三千與長河落日
我進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時候,沒在課堂上領略詩人和學者林庚先生的風采,但給我們上古代文學課的老師,不止一人提起林庚講授唐詩宋詞時的俊逸風采。比如,講到王維的《使至塞上》,稱林庚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中看出了一幅簡潔的幾何構圖:大漠和長河是橫線,孤煙是豎線,而落日則恰是與縱橫兩條線相切的一個圓。《使至塞上》有種幾何般的視覺美感——這是林庚先生獨到的闡發。
如此解釋,真是絕了!
對林庚先生,我們既佩服又仰慕。以后每見到西北大漠的字樣,腦海里浮現的,也是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以及林庚先生勾勒的“幾何圖形”。但從沒有細想“大漠孤煙”“長河落日”這般風景究竟具體出自何處。潛意識里,我想當然地把“長河”想象成黃河。
來到高臺,想象中的“幾何圖形”才得以校正糾偏。
這次應邀參加中國作協組織的學者作家赴張掖高臺采風活動,隨團陪同的縣文化工作者跟我們介紹說,王維詩中的“長河”,實際上是流經高臺的黑河,也是僅次于塔里木河的全國第二大內陸河。黑河以前叫弱水,沒錯,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弱水。
聽罷,我不禁恍然,頓有身臨“王維詩意”其境之感。原來“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的居延,就是今高臺的羅城鎮往西,延伸到酒泉的金塔縣,再北折向內蒙古額濟納一帶。隨著在高臺參訪的進一步深入,有了越來越多的“發現”:王維詩中的“孤煙”,也不是一般注釋家們所謂的“炊煙”“狼煙”,而是大漠上隨小股龍卷風而起扶搖直上的沙塵柱。
看來,所謂詩和遠方,唯有來到遠方,才能真正理解那些遠方的詩。
此番來高臺,雖沒有親眼目睹“大漠孤煙直”的奇特景象,但“長河落日圓”的浩瀚蒼茫,幾乎每天觸目可及。在高臺九頭胡楊林的沙丘之上遠眺,在駱駝城古遺址的觀景臺上憑欄,夕陽西下,弱水緩緩西流,大漠戈壁一望無際,山河實景比古詩想象更為震撼,而直抵心靈深處的自然光影,也似乎遠比林先生描述的幾何圖形來得更為真實。
祁連皓雪與天地正氣
陌生處才有風景。
來高臺之前,對這座西北小城并無多少了解。很多年前倒是去過一次敦煌,但并不記得那次在去敦煌的路上是否聽到過高臺的縣名。弱水河畔,祁連山下,這個坐落在祁連山和黑河濕地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上的現代綠洲城市,全境海拔在1260米至3140米之間,總面積4346平方公里,總人口15.8萬人——這些縣情概況,都是高臺當地的同志告訴我的。
高臺,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上的商賈重鎮和戰略要塞,素有“河西鎖鑰、五郡咽喉”之稱,在古絲綢之路和新亞歐大陸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今更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西煤東運的戰略通道。而這次高臺之行的巔峰體驗,就是深入祁連雪山,近距離瞻望雪山峰頂。
來之前也略做了點功課,在古詩文里集中讀到了不少對“祁連雪”的吟詠。比如徐陵的“祁連不斷雪峰綿,西行一路少炊煙”,王昌齡的“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以及晚近林則徐的“我與山靈相對笑,滿頭晴雪共難消”,林則徐與祁連山的相對一笑,似乎更像是壯志未酬的苦中作樂。
一代代文人把對祁連雪的觀感凝練入詩,也就把詩心鐫刻進了歷史,融入了巍巍祁連。散文家王充閭在游記《祁連雪》中因此得出“觀山如讀史”的感興:
觀山如讀史。馳車河西走廊,眺望那籠罩南山的一派空蒙,仿佛能夠諦聽到自然、社會、歷史的無聲的傾訴。一種源遠流長的歷史激動和沉甸甸的時間感、滄桑感被呼喚出來,覺得有許多世事已經倏然遠逝,又有無涯過客正向我們匆匆走來。
祁連山有文化,有歷史,堪稱凝聚了漢唐以來的中華魂。以往周游江南水鄉時,在心頭泛起的往往是柔情的漣漪,而在河西高臺的這幾天,心中則始終充盈著一種雄渾闊大的豪氣,事實也的確如此。只有來過大西北,親臨河西走廊、弱水之濱,看大漠長河展開新時代的新畫卷,閱盡現代綠洲新城煥發出的新容顏,你才能真正領略那縱貫千古的漢唐氣象。
“千山空皓雪,萬里盡黃沙”,漢唐氣象,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
據高臺新壩鎮的《紅沙河村志》記載,當年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復新疆,在酒泉坐鎮督戰時,聽聞紅沙河村村民有習武傳統,彪悍忠勇,當時正以平叛保國需武為要務,為鼓勵該村永葆練武保國之風,左宗棠欣然命筆,題寫“天地正氣”四字及對聯兩副為贈。百余年前的天山腳下,就流傳有高臺人保家衛國奮勇殺敵的英雄事跡……
何謂漢唐氣象?在千里狼煙的河西走廊,高臺人的天地正氣,或許也是其中的一種注解吧。
地下畫廊與文化高臺
高臺融媒體中心的記者,問我對高臺的總體印象,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以前對高臺知之甚少,這次親臨高臺,看到大街小巷各種‘紅色高臺’的標識,我覺得除了‘紅色高臺’,‘文化高臺’也是名副其實。”
如果說“紅色高臺”和“綠色高臺”在眾多新聞記者的報道、文人墨客的書寫以及大V播主的微博和短視頻中得到了豐富的闡釋,那么“文化高臺”則是我這次親臨高臺,才得到了鮮明的印證。
何以文化,何謂高臺?在高臺縣博物館,文化高臺的前世今生,有著最為詳實,也最為有力的注解。
據工作人員的介紹,高臺縣博物館是由高臺籍的優秀企業家陳正國先生捐資近四千萬修建而成。矗立黑河濕地公園之旁的高臺博物館,是一幢漢唐風格的三層高仿古建筑,天青色的歇檐屋頂,占地面積約9000平方米,這規模在全國縣一級的博物館中,應該可以排到前列。
高臺縣博物館的館內展陳豐富,尤其是數量驚人的魏晉畫像磚,更是堪稱該館一絕。
在《古冢丹青——高臺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壁畫藝術陳列》展室,講解員跟我們介紹說,高臺博物館館藏的魏晉彩繪壁畫磚,主要出土于本地的駱駝城、許三灣魏晉墓葬群。作為地下墓室四壁上的裝飾,魏晉墓室畫像磚與莫高窟、馬蹄寺石窟等絲綢之路沿線的地上石窟壁畫,上下呼應,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地下畫廊”。
看著展柜內一塊塊畫像磚,千年以前的農耕、牧獵、宴樂等各種生動的生活場景,在方寸間一一再現,畫像磚的畫面色彩則以黑、白、紅為主,歷經千載也沒怎么褪色。據介紹,前幾年,高臺博物館館藏的畫像磚,還被國家文物局選調,到國外進行展覽展出,展示河西走廊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漢唐雄風吹遍的龍城古道上,高臺的地下畫廊熠熠生輝,在那一塊塊栩栩如生的魏晉畫像磚上,我們仿佛能聽到西涼樂舞的慷慨激昂。
駱駝城遺址的廢墟之美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現代教育家和學者羅家倫,在1940年代來過張掖,曾經寫過一句詩:“不望祁連山頂雪,錯將張掖認江南。”大意是,假如不去留意祁連山頂的積雪,會誤以為自己來到了江南,這或許是對“綠色高臺”最早的稱頌。
但在我看來,張掖高臺既有江南的水鄉之美,同時又有江南難以得見的大漠氣象和雪山風光,除此之外,更有數不勝數的廢棄的烽燧、垛口、長城舊跡以及古城遺址。
在短短幾天的游覽過程中,我對高臺的漢唐遺址及其所深蘊著的文化傳統印象尤其深刻。
驅車在高臺境內,縣里的工作人員不斷把車窗外的烽燧、垛口、長城遺跡指給我們看,古老的軍事工程設施密布,再一次印證了高臺“河西鎖鑰、五郡咽喉”的戰略要塞地位。
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還是享譽華夏的駱駝城遺址。遺址呈長方形,面積近三十萬平米,甕城、腰墩、古井等殘垣斷壁在夕陽中,呈現出更為古舊的色彩。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駱駝城是絲路上的大型漢唐古文化遺址,它曾是漢唐時期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是絲綢之路的必經樞紐。但到了明朝初期,就已變為“龍荒朔漠之區”,留給后人一片廢墟景象。
“廢墟”之中天然沉積著歷史、文化和審美的地層。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曾經在他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里充分書寫了對廢墟的體悟。他所集中傳達的所謂“伊斯坦布爾的憂傷”,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對廢墟的狀寫以及由此而來的廢墟體驗。“廢墟”在帕慕克的書中也堪稱是一種體驗歷史的美學形式。
高臺的駱駝城廢墟遺址,也同樣為我們當代人的思想和審美注入了無限蒼涼的歷史感。在某種意義上說,已逝的歷史,恰恰是凝聚在廢棄的遺跡以及荒涼的廢墟里,這也是高臺之旅所見的一個個風化了的烽燧、垛口,尤其是駱駝城遺址令我感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絲路駝鈴悠長,大漠長河雪山。在返程去機場的連霍高速上,望著窗外綿延不絕的祁連山,不禁想反用羅家倫的詩,來概括我對高臺之行的總體觀感:“卻望祁連山頂雪,反認高臺勝江南。”
責任編輯 晨 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