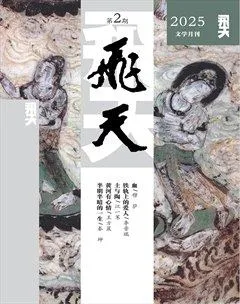半明半暗的一生(組詩)
與父夜飲
有一年大雪,酒后
父親在院里磨刀
一邊磨,一邊發誓
要宰了欺負我們的仇人
那時的他,二十多歲
有著公牛一般的脊背
和閃電一樣的脾氣
現在,坐在我對面的父親
已被歲月的溪流,沖刷出
滿臉溝壑。他膽怯、寡言
低著頭,自顧自喝著酒
夜色中,像一件喑啞的酒器
現在,又有大雪撲窗
與我對飲的男人
頭上的白發越來越多
幾乎就是剛剛,我才發現
對面這座沉默的大山
在時間的大雪中,已慢慢
白了頭
酒"器
一生嗜酒的人,會把酒
當作這世上另外的親人
一生嗜酒的人,酒杯或碗
會長成他身體里的器官
一個無依無靠的人
整日以酒度日
現在,平整的進村道路上
多了一只,踉踉蹌蹌的酒器
夜"雨
拉開窗簾
看燈光撲進雨聲中
平靜、舒緩
神的催眠曲
有一種沉甸甸的安寧
讓我想起白天的稻田
金色照亮河谷兩岸
這是收獲的季節
玉米的骨頭長滿黃金
如果祖父活著,他將跟隨
此起彼伏的鳥群重返田野
土地慈悲,深秋的田野
又一次安撫了,一個農人
半明半暗的一生
回多樂屯
我們在黃昏之時抵達多樂屯
父親站在昏暗的庭院里迎接我們
他剛剛從地里回來
衣服上沾滿泥巴和鬼針草
那個固執寡言的人
朝我們笑著
院里的暮色是銅質的
他臉上的笑也是銅質的
我們空著雙手,沒有什么
需要遞給彼此。只有他
還習慣性地握緊拳頭
還習慣性地,緊緊攥著
剛從地里帶來的,暮色和秋風
繁"花
落在溝渠里的花,覆蓋了流水
又被流水交給了河流
落在瓦片上的花,覆蓋了屋頂
又被屋頂交給了春風
落在祖父臉上的花
也落在懷里的孩子身上
春風慈悲
吹醒了村莊
也吹醒了屋后的山坡
滿山繁花,把祖母的新墳
又往天空的方向,抬了抬
暴雨來臨之前
一場暴雨來臨之前
會讓滿天的烏云
提前告知
那件佝僂在地里的衣服
直起身子
找到一處可供避雨的地埂
或者灌木。一場暴雨來臨之前
會第一時間,提醒斗笠和蓑衣
在電閃和雷鳴中,找到那個
驚慌失措的人
一場暴雨,會下在清晨
讓準備出門的水牛和犁鏵
再歇一歇。一場暴雨
也會久久地,懸停在黃昏的天幕
等牛羊從山上歸來
等鋤頭和竹籃到家了
才灌下來
過白水鎮
這個午后
再次經過白水
工業時代的小鎮
有一座火電廠
一座鋁廠
兩只巨大的胃
不分晝夜地反芻著
人們按部就班的一天
頭頂是即將坍塌的烏云
320國道上
行人稀少
操著不同口音的貨車師傅
忙著運輸各自的生活
火電廠的煙囪
像幾根高聳的柱子
支撐起白水鎮搖搖欲墜的天空
白色的煙霧往上攀爬
讓大地對天空的支撐
獲得了一種堅實的延伸
過白水鎮
我也只是匆匆一瞥
路上奔跑著鐵
賣菌子的人還沒有下山
驟雨初歇
就在剛剛,那個坐在山坡上
痛哭的女人,哭塌了天空
那么多傾瀉而下的淚水和哀嚎
那么多令人驚懼的閃電和雷聲
從她的身體里,噴涌而出
她那么瘦小,卻裝得下
那么多悲傷和絕望
她那么膽怯,卻敢一個人
坐在昏暗的墳地里哭
現在,驟雨初歇
雷聲消散。驚魂未定的人間
只剩頭上的閃電,還在
一刀刀,割著天空的皮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