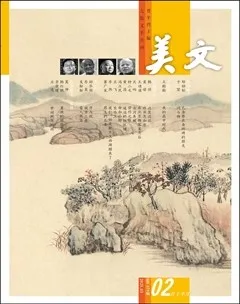在北京搬家五次后
一
外地來北京工作的人剛開始大多數在北京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所以我們稱自己為“北漂”——在北京漂泊著的人。作為一名年輕北漂,來京五年,我輾轉租住了五次房子,剛對一個地方產生些許歸屬感,便又要離開。
第一次在北京租房是為了求職。彼時我還是一名年僅24歲,還沒畢業的碩士應屆生。由于預算有限,我租了一間終日不見陽光的地下室,600塊一月,地處北京昌平區的一個村子里。
昌平本身就不算繁華,進入那個村子之后,更會讓人感到無比恍惚:這里真的是北京嗎?村子的整體景觀和我老家那個東北十八線小縣城極為相似,低矮的樓房,骯臟的街道,路邊垃圾桶堆砌的垃圾太多,漫溢到周圍。因此,走在路上常常能聞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不過,村子也有其優點,物價十分低廉。村里的餐飲大多是蒼蠅館子,衛生不敢保證,但價格親民。村口的一家面館,一碗雞雜面只需要8塊錢,雞雜管夠,分量十足,我去過多次,至今仍會懷念。
村子離昌平區里并不很遠。下了地鐵,轉公交坐二十分鐘就能到村口。我從村子去繁華的互聯網大廠面試,也只需公交轉地鐵坐兩站。繁華的CBD與破舊的城中村理所應當地在所隔不遠的區域共存著,北京著實是一座包羅萬象的城市。
為了找工作,我在地下室住了4個月左右。在那兒住了沒幾天,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深切體會到了陽光對生物的重要性。那陣子出門時,即便日頭很烈,我也不會打遮陽傘。自己的身體似乎化為了一棵植物,貪婪地吸收、渴求著太陽的照射。日照于我,成了和水、食物一樣的物質和資源,每當陽光照在我身上,我的身體就在進食,感到如一名終日饑餓的窮人正大快朵頤一般幸福。
地下室永遠漆黑一片,那是一種隔絕了一切光源的純粹黑暗,連人的影子都會被深深地吞噬進去。打開燈,室內瞬間被老舊的白熾燈燈管那慘白色的刺眼光芒籠罩。這個房間的晝夜就在這兩種顏色間交替。我自覺這樣的環境無益于身心健康,總是盡可能減少待在屋里的時間。但不出1個月,我還是患上了皮炎,手臂上有幾塊皮膚日日瘙癢不堪。4個月后,我找到了工作,就換了地方租住,胳膊上那幾塊瘙癢不治而愈。
二
汲取上次的教訓,我在尋覓新房之際,對房間的采光格外在意。要求并不苛刻:要有窗,射得進陽光。最后,我覓得一間由廢棄的經濟酒店改造而成的公寓房。
公寓房的格局和原本的酒店相比沒什么變化,和常見的便宜酒店中18平方米左右大床房的配置幾乎相同。房間的墻涂成了綠色,床、桌椅、衣柜皆為紅木色,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大件家具。唯一和酒店不同的是:衛生間里塞進了一臺舊洗衣機。沒有廚房,我帶了電磁爐和簡易的廚具,將屋里唯一的桌子布置成了做飯的地方。房子雖然又破又小,因在市區,有獨衛,房租高達2900塊一月。我在此地住了一年有余。
平心而論,在那里住的一年我生活得還不賴。那一片兒歸屬于北京南城,煙火味很濃。夏日的晚上,總有推著小車賣烤串、烤冷面的商販在公寓附近出現,價格實惠。下班回來我常常會買上幾串,再從附近的水果店拎回半個西瓜,幾罐可樂,將空調開足,電腦放上視頻,窩在小房間里,慢慢地邊看邊吃。縱使房間破舊,墻皮有礙眼的幾塊脫落痕跡,倚靠著的木質床頭已經掉漆,空氣也因為通風不好飛舞著細碎的塵埃,但在吃著西瓜和烤串的那些時刻,我仍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作為酒店改造而來的住所,這里的住客們呈現出一種奇妙的關系。首先,大家互不聯絡,毫無鄰居的概念。這很好理解,公寓按月簽合同,人員流動性強,沒有必要發展鄰里關系。其次,大家對彼此的生活又常常了如指掌,這是因為房間的隔音和大部分廉價酒店一樣,實在是太差了。
在各家的嘈雜聲之中,一對兒小夫妻的聲音最引人注目。我幾乎每天下班都能聽到那對兒夫妻吵架,有時還伴隨著摔東西和打斗的聲音。鬧得最兇的一次,女方叫來了警察。
“哪里人?”警察問。
“北京的,身份證110……”女方回答。報完自己的身份,她聲音響亮地說:“他打我!”
“是她打我!”一個男聲回應道。一男一女開始了無止境的互相責罵,試圖向警察證明對方的惡劣行徑。責罵聲中穿插著警察無奈的聲音:“好了……好了……”
由于我急著出門,未能聽到后面的情況。只是第二天,那個房間里又照常傳來了那對夫妻的吵架聲。我腦海中浮現出很多聯想:為什么北京本地人妻子要和老公租住在這樣狹小的房子里?為什么兩個人感情到了如此地步還不選擇分開?這背后想必不是什么美好故事,尤其對于那位經常被打的妻子來說。我有些同情她,卻也無能為力。一直到某天,他們吵架的聲音消失了,我便知道這家人搬走了。
我甚至猜測了他們搬走的原因,是經濟情況變好了,抑或是妻子終于下定決心離婚?后來我才發現,和個人意愿無關,他們必須搬走。我也必須搬走。原因很現實,經營公寓的老板突兀地準備把公寓翻新成一座辦公樓,并要求租客們兩周內搬家走人。
搬家通知在樓下貼了很久。我活得稀里糊涂,從未注意過樓門口張貼的告示內容,直到有一天回家發現樓道和走廊的燈全滅,暖氣也摸著冰涼,我才意識到大事不妙。當天,我在床上裹著被子凍得瑟瑟發抖,覺得自己就像電影里命運凄慘的女主角,馬上就要無家可歸,萬分憐憫自己。實際上,之后我不到三天就找到了合適的房子搬走。足見遇到危機時,人往往比自己想象得要強大很多。
臨搬走前,我站在衛生間的鏡子前對自己揮了揮手,嘴角向上扯出了一個微笑,并用手機錄下了這一幕,權當與這個小屋告別。隔了很久以后我路過附近,曾專程去那里又看了一眼。大樓已經煥然一新,成為了我不認識的耀眼建筑。小區里有個往日我買水的水站,如今已被廢棄,留下了一些空桶殘骸。門口那家好吃的燒烤攤不知道晚上還會不會來,無論如何,我等不到了。
三
我耗費了三天時間找到的房子是公司附近的一間老破小一居室,面積大概40平,相比我此前居住的房屋寬敞許多,月租3300元,考慮到西城區二環里這個地段,算是很便宜了。
當然,便宜自有其緣由。此房處于大部分人都不待見的一樓,戶型極為奇特,整體形狀接近于一個很扁的長方形,陽臺、臥室、廚房和衛生間這四個房間依次相連排成一排。陽臺位于那個長方形朝南方向的頂端,采光極佳,然而這也是這間房唯一的光源,其他方向皆無窗,也無陽光射入。臥室緊挨著陽臺,能蹭到一些陽光。廚房和衛生間則需要一直靠燈光照明。
另外,房間基本談不上有裝修。毛坯大白墻、拉繩才會亮的燈泡、不銹鋼臺面的廚房……處處透露著一股八九十年代房子的氛圍感。
北京到處都有這種格局奇奇怪怪的老房子,而且很多價值不菲。我于2022年住進此處,當時正值北京房價的巔峰。由于這個小區對應的學區尚可,該小區房價一平方米高達12萬元。記得那時我隔壁的房子被一對年輕夫妻買下,夫妻兩人和裝修工人聊天時,語氣興奮地說:“這房子公攤小,得房率高,好得很!”他們說話時眼中有光,滿載著對未來小家的憧憬。而我卻心中略帶苦澀地思索著,花掉全家積蓄在這樣的房子里安家,真的值得高興嗎?
2024年的當下,那個小區的房子已經降到了7萬元一平,甚至有低層的掛牌價給到單價6萬多。我回想起那對小夫妻,回想起他們興奮的語氣和眼里的光芒,茫然地揣測著他們現在會不會很后悔那時買房的選擇。
在這間老破小里我也住了一年。房子空間變大給了我極大的幸福感。與之相比,房子老舊只是一些小問題。房東留下的布藝沙發特別臟,我費力地把沙發套換下來,買了一條沙發墊鋪上。臥室的瓷磚松動并破裂了好幾塊,我便網購了淺灰色的地毯蓋好。經過我的努力布置,破爛的房間也增添了幾分溫馨。
不過,這種平靜的生活隨著天氣逐漸轉暖、家里的小動物開始活躍而被打破。某天我起夜上廁所時,猝不及防和幾只油光水滑的蟑螂打了個照面。北京的蟑螂大多是德國小蠊,棕色、身軀小巧、靈活性和機動性高,爬得飛快并且很擅長鉆進各種縫隙。我強忍著懼意嘗試著找了本書試圖拍死它們,因為緊張,拍得并不果決,于是這場戰斗的結局以它們鉆進墻壁瓷磚的縫隙里消失不見告終。
隨著時間的推移,蟑螂家族壯大起來,繁育得越來越多。我始終很怕它們。在與蟑螂的戰斗中,怯懦的性格讓我落了下風,即便下定決心去踩它們,也經常因為恐懼失手。蟑螂們不知道是不是洞察到了這點,態度愈發囂張,活動范圍甚至擴大到了我的床邊。
戰爭的轉折點發生在某次我自己下廚做飯的時候。幾只蟑螂就在菜板旁邊來回爬動,似乎正等待著我做好食物它們開餐,完全不把我這個活人放在眼里。看著它們自在晃動的觸須,我覺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挑釁,嘴上高喊著:“我的飯你們敢搶?!”拿了本書把它們一個個都拍成了蟑螂餅。我想,應該是我體內的貪吃屬性蓋過了我的怕蟲屬性。很正常,民以食為天嘛。
在此之后,我不再懼怕蟑螂,通過各種殺蟑手段取得了戰爭的基本勝利。不過一些后遺癥還是留了下來,比如放假回到我那一只蟑螂都沒有的東北老家,母親疑惑地發現我動不動就彎下腰盯著地上一塊黑點兒出神。
“你干什么呢?”母親狐疑地問我。
黑點沒動,不是蟑螂。我松了一口氣,苦笑著回答道:“沒什么,沒什么。”
四
坊間傳言,沒有體驗過與人合租的北漂人,其北漂生活是不完整的。在北京生活的第三年,我換租到了合租房,讓我的北漂生活完整了起來。
這次換租實乃無奈之舉,原房東在租期滿后坐地起價,我實在無力承擔獨居一室一廳的房租,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公司附近找了間合租房,房租每月3100塊。和我共享房子的室友是兩對小情侶,我們建了一個微信群,每月在群里分攤水電費。
搬家之前,我還憂慮著如何與合租室友相處。事實上完全不用擔心,回到家后,大家紛紛鉆進自己的那間臥室,緊閉房門。好巧不巧,我和他們上下班的時間似乎也沒有重合。大家雖同住一個屋檐下,對彼此而言卻像幽靈一樣。據我的多位朋友反饋,這是北漂合租的普遍相處狀態。
那段時間我談了戀愛,男朋友每周末都會來陪我一起住。由于擔憂房間的隔音問題,我們兩個人關好房門后,常常無聲地擁抱親吻。隔壁房間大抵也是如此,我從未聽過另外兩對兒情侶發出什么刺耳的聲音。合租房中的愛情是靜悄悄的,年輕的戀人們守著屬于自己的小小陣地,像兩株安靜的藤蔓纏繞在一起,愛在房間中靜靜生長。
當然,無論如何努力避免接觸,合租房的廚房與衛生間還是需要共用。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公共區域的衛生情況往往取決于所有合租人中衛生習慣最差那個。
就拿廚房來說。我和男友數次在廚房的水槽發現了腐爛的食物殘渣。我們雖然覺得惡心,卻絕不會為未知的室友進行清理。久而久之,我干脆放棄了在廚房做飯。
共用的衛生間情況顯然更糟。我住在帶獨衛的主臥,僅在某次清理走廊衛生時借用了下室友們離走廊更近的公衛。一推開門,我便聞到了一股惡臭:密閉空間里積攢多日的濃郁屎味。我拎著拖布,不由自主地開始干嘔。仔細觀察后,衛生間的環境讓我膽寒。垃圾桶沒有套塑料袋,用過的紙團已經把垃圾桶堆滿,還有不少紙團散落在垃圾桶附近的地面,上面帶著顯眼的屎黃色。無論是味道還是畫面,這里都超過了我的承受極限,我立刻關門逃離了那個地方。
一直到第二天吃午飯時,我依舊忘不掉那個味道,總覺得那股臭味在我周圍若隱若現,食欲也寥寥無幾。我并不算對環境衛生耐受力很差的人,小時候老家縣城的公共廁所都是旱廁,里面也是骯臟不堪、屎尿橫飛,但并未引起我嗅覺上太大的不適。恐怕是因為旱廁通風很好,而合租房那個衛生間沒有窗戶,幾乎相當于一個封閉空間,味道著實比旱廁濃郁數倍。合租室友中有一對情侶已經在此租住了三年,每天都在使用這間廁所,我只能在心里暗暗佩服對方。
五
合租生活半年后,隨著我和男友感情加深,我再次收拾好家當搬家了。這次是搬到男友租住的一居室,與他共同生活,通過分攤節省房租成本。
搬家之際,我熟練地拿出塞在衣柜后面的大紙箱。這幾個紙箱已經默默陪伴我快四年,平日里,它們總是被折疊成扁平的紙板,塞在家里的角落。到了要搬家的時候,我會把它們展開,用膠帶封好。它們變得可靠而堅固,裝滿形形色色的物品被搬進小貨車上。車子啟動,紙箱們安靜地待在貨車黑漆漆的車廂,隨我去往我在這座城市的新住所。
行李擺放妥當后,我和男友迅速地布置和整理房間。那幾個紙箱被我們拆開疊好,又變成紙板放到了新家的衣柜后面。當把衣柜向墻面推、夾緊那幾塊紙板時,我突然想到,真的有“家”的那些人,房間里大概不會特意留出放置紙箱的位置吧。
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了些許悵然若失之感。男友似乎察覺到我的異樣,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問我:“怎么了?”
噯,你當初為什么選擇留在北京呢?我輕聲問道。
“碩士畢業后,北京的公司給的工資最高,就留下了啊。”
但是這座城市,好像任憑外地人怎么努力,都很難在這兒安家……
理工科的男友笑著說:“從法律意義上講,租房也是家呀。付出了金錢換取了房子一定時間的使用權,租的房子在那段時間是完全屬于你的。”
那不一樣……我下意識地反駁,又突然愣住了。陸續換租了這么多次房子,我從未用“家”這個詞來形容它們。下班之后和父母、朋友聊天,我都羞于講“我回家了、我到家了”這樣的話。因為我潛意識里覺得,我在北京沒有家,房子是房東的,我住的不是家,是出租屋,我只是一名外地租客。
但這個想法真的正確嗎?
“你不但在這座城市有家,你的家還越來越好呢。”男友說道。
我回想起這五年在京住過的房子。從一開始黑漆漆的地下室,到有獨衛的小公寓、寬敞了不少的一居室。此后忍耐了半年的合租生活,如今我和男友即將住進這間新屋。
和男友一起負擔房租的新房有著明亮的落地窗,坐北朝南,陽光明媚耀眼。房子裝修很新,臥室天藍色的墻紙一塵不染,上面畫著一個很可愛的宇航員小人。床品按我的喜好挑選,床單和被罩上印著手捧郁金香的小兔子。男友送我的幾只毛絨玩具也被擺在床上,小熊、小狐貍和小獅子一起朝著我微笑。我也朝它們露出笑容。
而且,越來越好的不只是“家”。仔細回想,五年的時間,我在這里認識了我最好的朋友與陪伴一生的愛人,學了不少知識和技能,經歷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從稚嫩的學生,變成了能妥善照顧好自己、有著自己交際圈的成熟大人。
我似乎一邊罵著北京,一邊在它的給養下飛速成長著,我已經熟稔國圖的借書流程,在小西天的電影資料館看過幾十場藝術電影,隔三差五會去鳥巢外蹭聽一場免費的演唱會,并在白塔寺附近的胡同里拍下了好多張北京的火燒云晚霞。我已經習慣并沾染了這座城市的味道,習慣并有些依戀上了在這座城市的生活。
下午,我和男友一起在小區樓下散步。我們不約而同地抬起頭,望見了纖云也無的湛藍天空。風吹過來涼涼的,夾雜著淡淡的草木味道,讓人不禁想大口呼吸。此時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這里或許有全世界最美的秋天。路邊的銀杏一樹金黃,在秋日的陽光照射下有些耀眼。我牽著男友的手,拉著他朝便利店走去,打算選購一點冰箱貼裝飾下我們的小屋。我仍然不確定自己未來是否會在這里定居,仍然因為這里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居住成本而感到苦惱。但是我現在清楚地明白,我與這座城市確確實實已經產生了深刻的鏈接,這并不需要一間屬于我的房子來為此證明。
(責任編輯:王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