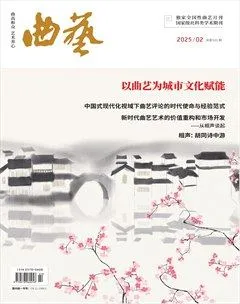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略論民國時期蘇州評彈的都市化
傳統(tǒng)藝術(shù)在市場環(huán)境下面臨的生存困境是我國文化產(chǎn)業(yè)綜合發(fā)展亟待解決的關(guān)鍵問題。盡管近年來依托政策支持與業(yè)界努力,劇場、書場獨見“銀發(fā)族”的情況已有所改善,但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守正創(chuàng)新之路依然任重道遠(yuǎn)。雖然越來越多的民族文化瑰寶被列入非遺保護(hù)名錄,但我們的欣慰與擔(dān)憂仍然是并存的。困局來自許多方面:作品囿于一隅,演員青黃不接,觀眾日漸流失,以及諸多各家難言之經(jīng),但若要究其根源,仍應(yīng)回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這對矛盾中尋求答案。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報告,截至2023年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已達(dá)66.16%,而該數(shù)據(jù)在1949年尚只有10.64%,這表明,在70多年間中國經(jīng)歷世界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然而,當(dāng)中國不斷向現(xiàn)代化社會邁進(jìn)的同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間的矛盾也在各個領(lǐng)域逐漸凸顯。而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形式,幾乎無一例外地發(fā)展成熟于“過去”,這是由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歷史發(fā)展形態(tài)決定的。所以要探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間的糾葛,僅聚焦當(dāng)下難免身在此山而為一葉障目,不妨回到歷史中尋找答案。事實上,作為中國社會整體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組成部分,傳統(tǒng)藝術(shù)在近代上海的發(fā)展歷程無疑是一個極好的樣本,已有的研究多關(guān)注傳統(tǒng)藝術(shù)進(jìn)入上海后的新樣態(tài),但對新樣態(tài)與傳統(tǒng)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間關(guān)系的討論明顯不足,而后者恰恰是考察傳統(tǒng)藝術(shù)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江南代表性曲藝曲種蘇州評彈為對象,通過考察其在近代上海的發(fā)展歷程,探討該時期評彈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特點、程度和局限,以期為當(dāng)下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守正創(chuàng)新提供借鑒。
一
要考察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首先應(yīng)對傳統(tǒng)時期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做一討論。傳統(tǒng)藝術(shù)產(chǎn)生、發(fā)展、成熟的過程根植于傳統(tǒng)社會,這不僅直觀地表現(xiàn)在形式或內(nèi)容上,更體現(xiàn)在藝術(shù)生產(chǎn)的邏輯與藝術(shù)本體的特征中。以江南地區(qū)代表性曲藝曲種蘇州評彈為例,明清時期江南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水路交通和鄉(xiāng)鎮(zhèn)布局)以及農(nóng)業(yè)為主導(dǎo)的生產(chǎn)方式(農(nóng)事節(jié)律)從根本上塑造了她的藝術(shù)本體——在書場說演長篇書目的演出形式和以說表為核心的演出技巧。前者是空間關(guān)系,環(huán)太湖流域密布的水網(wǎng)不僅構(gòu)筑了江南地區(qū)星羅棋布的市鎮(zhèn)格局,也為藝人往來鬻藝提供了交通的便利;后者是時間關(guān)系,所謂“菜花黃,說書像螞蟥;菊花黃,說書變大王”,民眾以農(nóng)事節(jié)律為主導(dǎo)的生活決定了評彈業(yè)的淡旺季,也間接影響了演出的周期與書目的長短。
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評彈藝術(shù)本體的生成規(guī)律。在交通成本與農(nóng)事節(jié)律的制約下,說書人以相對固定的節(jié)奏在江南鄉(xiāng)鎮(zhèn)間“背包囊,走碼頭”,短則數(shù)月,長則半年。到書場排日聽書,是江南民眾最日常化的消遣,而長篇書目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與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正是吸引聽客循序漸進(jìn)連續(xù)聽書的關(guān)鍵。加之礙于文化水平,舊時有編新書能力的藝人比較少,且成本頗高,如若持中短篇演出,便只有兩種選擇——在一家書場不斷更換書目,或持一部書目不斷更換書場,這在當(dāng)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不具可行性。在此基礎(chǔ)上,為適應(yīng)走碼頭過程中不同聽客群體差異化的審美需求,淡化同一書目反復(fù)說演帶來的審美疲勞,說表在演出中的比重不斷提高。說表賦予了說書人對書目或芟蕪汰冗,或細(xì)致描摹的拉伸空間,也令演出的藝術(shù)呈現(xiàn)能夠根據(jù)聽客的審美需求適時而變,由此發(fā)展出了評彈“各家各說”“常說常新”的獨特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
當(dāng)依托于傳統(tǒng)社會的藝術(shù)形式與現(xiàn)代社會發(fā)生接觸,勢必產(chǎn)生諸多復(fù)雜的矛盾。中國在近代的艱難轉(zhuǎn)型,顯示了古老國家欲圖掙脫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農(nóng)耕文明桎梏是何等困難。即使在近代江南,明清以來發(fā)達(dá)的商品經(jīng)濟(jì)也始終未能帶來實質(zhì)的內(nèi)生性轉(zhuǎn)機(jī)。最終,西方鐵蹄在19世紀(jì)中期叩開了看似牢不可破的國門,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化生產(chǎn)方式裹挾著歐風(fēng)美雨式的現(xiàn)代生活,向以上海為首的港口城市發(fā)起了前所未有的入侵。不到百年,上海這座江南小鎮(zhèn)便一躍成為執(zhí)全國經(jīng)濟(jì)文化之牛耳的國際都會,并在20世紀(jì)30年代達(dá)到頂峰,如忻平所說:“就建國前中國現(xiàn)代歷史而言,20-30年代的上海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發(fā)展得最快,社會生活的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得最為突出,歷史進(jìn)程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矛盾表現(xiàn)得最為強(qiáng)烈,歷史的進(jìn)步與歷史的痛苦展示得最為明顯,外在與內(nèi)蘊(yùn)兩種現(xiàn)代化動力在此的契合程度凸顯得最為深刻。”①無論時人還是后人,對近代都市上海的直觀印象,都直接地與霓虹閃爍、光怪陸離的摩登生活聯(lián)系在了一起。豐富、發(fā)達(dá)的娛樂產(chǎn)業(yè)無疑是上海最引人矚目的現(xiàn)代化標(biāo)簽,“晚清以來,上海聚集了京劇、越劇、滬劇、評彈、淮劇,以及滑稽、昆曲、揚(yáng)劇、粵劇、錫劇、紹劇等幾十個劇種,成為了近代中國最大的戲曲舞臺”。②此外,電影院、舞廳、歌場、跑馬場、跑狗場、彈子房、游樂園等一眾新式娛樂場所的加入更為上海的娛樂生活增添了摩登氣息,也令滬上娛樂產(chǎn)業(yè)的市場競爭愈發(fā)激烈。在此過程中,以蘇州評彈為代表的傳統(tǒng)娛樂形式普遍經(jīng)歷了不同程度的變革,生發(fā)出了諸多前所未見的新特征,逐漸形成一套匹配都市社會的市場邏輯,深刻影響了評彈在近代的發(fā)展。
二
上海在蘇州評彈藝術(shù)史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于直到今天關(guān)于“蘇州評彈發(fā)源于蘇州,發(fā)祥于上海”的討論仍令蘇滬二地的評彈愛好者們莫衷一是,爭執(zhí)不休。問題的核心在于持論雙方對“發(fā)祥”一詞解釋的差異,贊同者意欲借此強(qiáng)調(diào)評彈來到上海后的高光表現(xiàn),反對者則認(rèn)為其抹殺了傳統(tǒng)時期評彈在中心地蘇州的繁榮歷史。但可以肯定的是,雙方均不否認(rèn)近代上海在評彈藝術(shù)史中的里程碑地位。
相較于評彈的傳統(tǒng)中心地蘇州,上海的現(xiàn)代商品性娛樂業(yè)不論在市場規(guī)模、容量,還是經(jīng)濟(jì)效益、社會影響等方面,都是傳統(tǒng)中國歷史上亙古未見的。此種新舊間的過渡,得益于政治、人口、經(jīng)濟(jì)等各種內(nèi)外相繼因素的交織聯(lián)動,制造了一個有別于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的近現(xiàn)代城市空間,深刻改變了這座城市的社會結(jié)構(gòu)。正如周武所指出的,19世紀(jì)60年代以后上海對江南傳統(tǒng)中心地蘇州、杭州的取代,是現(xiàn)代城市對傳統(tǒng)城市的取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③近代上海的都市社會結(jié)構(gòu)帶來了有別于傳統(tǒng)市鎮(zhèn)的全新市場空間布局。傳統(tǒng)江南市鎮(zhèn)的間隔普遍保持在20至30里,而30年代的上海則擁有以西藏路、南京路和靜安寺路交界一帶的1個中央娛樂區(qū),與8個次中心娛樂區(qū)④,各次中心區(qū)與中央?yún)^(qū)間始終保持了1300米至2000米左右的距離。同時,娛樂區(qū)以消費(fèi)型娛樂為核心功能的街區(qū)屬性,也令其擁有遠(yuǎn)超傳統(tǒng)市鎮(zhèn)的娛樂場所數(shù)量,“三四馬路、大新街附近一帶以及南市城隍廟等處,簡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處,到處懸掛著書場燈籠與招牌”。⑤“此外附屬小茶館里的說書也普遍全市,無論是偏僻的地方,總能夠找到一二處。書場之在上海,大家已公認(rèn)是平民化的消遣場合了。”⑥
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就空間上看,上海龐大的市場體量使其在城市內(nèi)部形成了一個相較江南大市場的、縮放式的評彈市場網(wǎng)絡(luò),構(gòu)成了“大江南”“小上海”的市場格局。在上海,各娛樂區(qū)間的距離相較傳統(tǒng)市鎮(zhèn)間距縮短了約10倍,而城市道路的建設(shè)進(jìn)一步擴(kuò)大了個體的活動半徑,平整寬敞的馬路上往來的各式交通工具,突破了過去鄉(xiāng)鎮(zhèn)石路、土路中顛簸前行的獨輪車所能達(dá)到的最遠(yuǎn)邊界。據(jù)計算,20世紀(jì)20年代至30年代的上海市民通過交通工具(電車、公共汽車、黃包車、腳踏車等)出行,在同樣的半小時出行時間內(nèi),可達(dá)到的范圍已由步行的1.5至2公里擴(kuò)大到5至10公里,外出空間相較19世紀(jì)40年代至50年代增大將近4倍。⑦如鳳鳴臺書場,就有三路電車、十路公交汽車直達(dá)門口,“交通最便”。⑧活動半徑的擴(kuò)展對娛樂業(yè)發(fā)展的作用是雙向的,一方面意味著市民活動半徑中所涵蓋的娛樂場所的增多,便捷輕松的出行體驗也令市民更愿意外出參與娛樂活動;另一方面,從業(yè)者活動半徑內(nèi)的市場份額也相應(yīng)增加。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說書人以往在“大江南”網(wǎng)絡(luò)中的走碼頭活動得以在“小上海”的城市內(nèi)部網(wǎng)絡(luò)中實現(xiàn)。

新技術(shù)的應(yīng)用進(jìn)一步拓展了都市娛樂業(yè)的市場空間。除各類書場和私家堂會外,上海最先利用無線電技術(shù)開辟了空中書場,在不占據(jù)實體空間的狀況下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評彈的市場范圍。“20世紀(jì)30年代以后,隨著無線電播音的普及,上海的廣播電臺發(fā)展十分迅速,電臺設(shè)立眾多,最多時電臺數(shù)超過一百家”⑨。時人為之感嘆:“一到下午,說書節(jié)目,便陸續(xù)開始。待到晚上,聽到的不是唐大爺和秋香,便是樊家樹和沈鳳喜。說書先生一面叮叮咚咚地彈著三弦,一面逼緊著喉嚨唱著詞句,這時上海差不多要變成說書世界了。”⑩
龐大的市場、豐厚的報酬以及都市摩登的魅力,令上海釋放出了強(qiáng)大的虹吸效應(yīng),“上海先生”成了說書人們在“碼頭老虎”之上最高的追求。大量響檔紛紛赴滬鬻藝,書場場東為了招攬聽客,在爭聘名家的同時還創(chuàng)立了多檔越做的形式。越檔,指一個書場同時聘請多檔藝人,通過壓縮每檔的演出時間實現(xiàn)合作演出的表演形式。雖然早在上海以前,蘇州就已有二檔越做的歷史,但越做真正意義上對傳統(tǒng)形式的突破,則是在20世紀(jì)初的上海完成的。多檔越做最先由游戲場“樓外樓”推出。為吸引游客,“樓外樓”經(jīng)理一改評彈“一日一檔”的演出慣例,轉(zhuǎn)而同時聘請三四檔說書人同場演出,將每檔的時長壓縮至45-60分鐘,首開多檔越做先例。這一演出形式下,聽眾的花費(fèi)只是略高于在舊時書場的,就能欣賞有如年終會書般響檔云集的盛況,時人為之感嘆,“目前上海各書場,平常每場都有四五檔之多,好像天天在那里說會書”11。多檔越做在“樓外樓”的成功,很快便為各大游戲場所效仿。據(jù)張健帆回憶,“小世界的說書場,……日夜兩場,好像說會書一般”12“尤其在盛夏之夜,邀上兩三知己,登上瓊樓高處,泡上一壺清茶,彼此把茗清談,聽聽說書,望望夜景,乘風(fēng)納涼,是為當(dāng)時上海人所公認(rèn)的賞心樂事。”13
多檔越做的興起大大加快了說書人在都市中的流動速率,并逐漸將說書人從傳統(tǒng)的農(nóng)事節(jié)律中抽離,納入到現(xiàn)代工業(yè)節(jié)律中。多檔越做通過壓縮每檔藝人的演出時間來實現(xiàn)多檔同臺的效果,這意味著藝人也會同時接下多家書場業(yè)務(wù),頻繁地在各書場間流動,這種流動的實現(xiàn)不僅需要依托市場的體量與便捷的交通,更需謹(jǐn)守時間的規(guī)則:
現(xiàn)在說書一檔,限定四十五分鐘,上下檔銜接都有一定時間,不能或遲片刻。如有一檔誤卯,便要牽動大局。照舊式慣例,前面一檔說書,須看下面一檔先生到場后,才可落回下臺,趕別一家場子,無須再顧這邊的冷場,所以目今的說書人,絕對不能誤卯的。14
由是,以時、分、秒為單位的更為嚴(yán)格、精確的工業(yè)時間取代了以年、季節(jié)、節(jié)氣為單位的農(nóng)業(yè)時間,乘著黃包車在書場間奔波的說書人們就如拉爾夫金所說的那樣:“時間世界不再與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節(jié)的變化相聯(lián)系。相反,人類創(chuàng)造了一個由機(jī)械發(fā)明和電脈沖定時的人工的時間環(huán)境:一個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預(yù)見的時間平面。”15
龐大的市場規(guī)模與更快的演出節(jié)奏,令上海儼然變成一個縮放式的江南市場,說書人以更快的速率在各式書場、堂會、電臺間流動,停留滬上的時間大大增長。如周玉泉“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二十年中大部分時間在上海,偶然出碼頭,也是短時間的”。16 1930年的《大光明》報曰:“吳小松、吳小石、魏鈺卿等輩,情愿作滬上寓公。其次亦不憚繁瑣,流轉(zhuǎn)江湖。”17徐云志因上海業(yè)務(wù)太多,索性把家遷至上海,“書場演的太熟,就在電臺播唱。最忙的時候,一天要做八家電臺,人家叫我‘八面威風(fēng)’。等到電臺又太熟,就專做堂會”。18
正是因為都市市場強(qiáng)大的內(nèi)循環(huán)能力,大大加快了評彈的都市化。盡管在此之前說書人同樣會到上海鬻藝,但30年代評彈所表現(xiàn)出的都市化氣質(zhì)遠(yuǎn)超過去任何一個時期。張健帆在憶及自己中學(xué)時(20世紀(jì)20年代)的聽書體驗時,曾談到被同學(xué)嘲笑“喜與老人為伍”,并被冠以“說書先生”的綽號取笑19,而短短十年,評彈已然搖身一變成了都市流行文化的一員,引領(lǐng)著都市的摩登風(fēng)氣。薛筱卿創(chuàng)造性地為彈詞加入伴奏,加深了上下手間的互襯,增強(qiáng)了彈詞的音樂性。周云瑞在《珍珠塔·唱道情》中,借鑒了流行歌曲《人魚公主》的音樂,發(fā)展了伴奏過門,使聽客耳目一新。《啼笑因緣》《秋海棠》等現(xiàn)代書的編創(chuàng),令評彈跳脫出了傳統(tǒng)題材的桎梏,“西裝旗袍書”風(fēng)靡一時。范雪君在小落回時,彈唱流行歌曲和最新電影插曲,活躍書場氣氛。聽書的場所也開始由桌椅板凳、閑散悠然、滿是市井煙火味道的舊式茶館轉(zhuǎn)移到裝修考究、配備沙發(fā)座椅、音響設(shè)備與空調(diào)冷氣的專業(yè)書場,說書人的日常演出空間逐漸與這座城市的氣質(zhì)融為一體。1932年的《社會日報》曾談到說書業(yè)在上海的轉(zhuǎn)變:
說書之于上海,在十幾年以前,簡直也是一班老先生們專有的享樂,現(xiàn)在是慢慢地普及起來了。……二十世紀(jì)化的東方書場的情形,卻不同于前面所說的了,那邊簡直跟南京大戲院差不多,有摩登風(fēng)流的年輕姑娘,有脂粉滿面的青年子弟。20
廣告是消費(fèi)主義的重要載體,相較于霓虹燈廣告牌帶來的視覺沖擊,無線電則以聲波的形式將廣告投放到了都市社會的各個角落。借助評彈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廣告常常能有更強(qiáng)的表現(xiàn)力。說書人的“三寸不爛之舌”不僅能讓聽客為之捧腹而不致生厭,還可以將廣告用開篇播唱,使人耳目一新。這種對有聲廣告的藝術(shù)化加工,不論是流行歌曲還是地方戲曲都很難做到,而評彈卻能在插科打諢中靈活地加以穿插,或是專作廣告開篇,以藝術(shù)化的方式加以表達(dá)。這無疑是商業(yè)廣告進(jìn)入無線廣播時期后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新,如盛利食品公司的廣告開篇:
連天烽煙說申江,赤日炎炎火傘張,卡德路邊人影眾,中心地點鬧洋洋,(君可見)一幟獨懸高屋頂,盛利兩字露鋒芒!四川路中名早揚(yáng),老店新開營業(yè)興,喬遷更加生涯旺,同行眼內(nèi)出紅光。物美價廉人皆知,大名鼎鼎可稱王!冰淇淋,與冰棒,橘子楊梅觸鼻香,各式刨冰件件有,憑君選擇滋味嘗,(保你是)贊譽(yù)連連呼清涼。價錢巧,品質(zhì)良,清潔衛(wèi)生味芬芳,電話三八三八九,出門送貨用冷氣裝。代價券印成美術(shù)化,親朋饋贈最相當(dāng),萬千主客都稱好,有口皆碑永不忘,盛利飲冰播上洋。21
20世紀(jì)30年代的上海市民,在酷暑之日閑坐家中,享受著收音機(jī)畔隨電波傳遞而來的弦索叮咚之聲,若有解頤之念,只消照著廣播中一個電話,便有商販將刨冰飲品送貨上門。如此都市生活,何嘗不叫人神往?
三
盡管20世紀(jì)30年代后評彈在上海的發(fā)展表現(xiàn)出諸多新氣象,但是否意味著該階段的評彈已完成了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仍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評彈在都市市場中的內(nèi)循環(huán)依舊延續(xù)了傳統(tǒng)時期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即攜一到兩部書目在各個演出空間之間流動,只是頻率更快,周期更短。然而盡管上海有著遠(yuǎn)超一般碼頭的市場體量,卻依舊無法滿足評彈長期演出的需要,為了消解聽客的審美疲勞,即便是名家響檔也仍需定期離滬跑碼頭。最典型的例子是“孤島”時期,特殊的歷史條件令該時期租界內(nèi)的娛樂業(yè)畸形繁榮,評彈也不例外。為避戰(zhàn)亂,大量名家響檔久居租界不愿他往,初期生意自然紅火異常,但不到兩年,大批書場的經(jīng)營便開始每況愈下,即便是身居行業(yè)金字塔頂端的沈儉安、薛筱卿、蔣一飛等,開書數(shù)月,賣座也毫無起色,以致被迫提前剪書22。到1943年,即便是“執(zhí)書壇牛耳”的“描王”夏荷生業(yè)也遭逢了“抽簽”23的窘境,究其原因,是“在滬之時日較久,隸‘東方’連做‘復(fù)檔’,無怪聽客如食炒熟之韭菜,淡而無味,不足為奇矣”24。由此可見,上海市場的都市內(nèi)循環(huán)并不足以使其脫離傳統(tǒng)江南市場獨立存在,評彈演出也隨著說書人的赴滬、離滬而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間徘徊。
在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未發(fā)生變革的前提下,評彈的諸多都市化特征實際與其藝術(shù)邏輯相悖。多檔越做壓縮了每回書的時長,要求說書人更頻繁地在書場間輾轉(zhuǎn),1947年劉天韻、謝毓菁師徒一天需隸“書場七家,及電臺二處。自午后至深夜,所拼鐘點前后銜接,幾無片刻寧晷”25。而各家書場、電臺的開書時間不盡相同,導(dǎo)致說書人在各家說的回目也前后相異,往往厘清混雜交叉的書路便要費(fèi)去大把精神。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更多的說書人選擇將重心由說表轉(zhuǎn)向與書情關(guān)聯(lián)較弱的彈唱與放噱,或借精致華麗的衣飾勝出:
(新型書場)聘請說書藝人,但求外表,不務(wù)實際。有許多響檔,書藝并無骨子,只是噱頭多,年輕漂亮,能夠吸引煙視媚行的女聽客,色迷迷的男聽客,為飽耳福兼飽眼福起見,也會趨之若鶩。所以新型書場主人,為生意眼著想,非多聘較有噱頭,衣飾華麗的男說書人不可。若是不修邊幅,落拓不羈,而有真才實藝的說書人,反在擯棄之列。26
空中書場的特點——視覺缺失、聽覺放大同樣弱化了說表的效果,助長了“重唱輕說”的傾向。“起腳色”的受限尤其顯著,“書場上,聽客親見其人,若有言不達(dá)意之處,可以面部表情及手勢為之。如《玉蜻蜓》中之‘金大娘問卜’,《雙珠鳳》之‘堂樓詳夢’。書中之瞎子,并不開口,而作暗中摸索狀。至于無線電中,則完全不能,須詳細(xì)表明,而聽者反味同嚼蠟。至于評話中打武,更非手勢解數(shù)不可,刀來槍去,如身歷其境。在無線電非細(xì)細(xì)交代不可,故較難于書場也”。27視覺的缺失對評話的打擊尤為明顯,因“評話注重現(xiàn)行,書中既多開打,狀兩軍交鋒,刀來槍去,雖在臺上,手執(zhí)扇柄,虛張聲勢,描摹一剎那之神情,能使座上聽客,為之動容。惟在播音室中,傳聲不能傳影,乃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況開講評話者,須狀叱咤風(fēng)云,慷慨激昂之志士壯漢,粗聲大氣,于電波聲中,震耳欲聾,故于播音初期,獨多彈詞節(jié)目,評話絕無僅有”。28
“重唱輕說”促成了彈詞開篇的獨立,進(jìn)而推動了流派唱腔的大發(fā)展,在這一層面是值得肯定的,但需注意的是,二者的繁榮實際上也掩蓋了“重唱輕說”埋下的隱患。在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未改變的情況下,開篇和流派唱腔并不能達(dá)成市場邏輯與藝術(shù)邏輯的自洽,而是仍需依托長篇為基礎(chǔ)存在,一旦脫離書情,便只是用吳語演唱的流行歌曲,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余論
毫無疑問,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力,是任何一座城市都無法比擬的。“這個字眼如同興奮劑一樣激發(fā)著人們的想象,點燃了人們的希望。”29如同張鑒庭“七進(jìn)”上海一樣30,評彈在上海站穩(wěn)腳跟也絕非一蹴而就。經(jīng)歷了清中后期到20世紀(jì)30年代的漫長探索,評彈才逐漸由老氣橫陳、慢條斯理的舊式茶館中轉(zhuǎn)移至最時興的游戲場、新式書場,再經(jīng)由無線電滲透至上海的每一條尋常里弄,這些身著長衫、手握紙扇的老派說書先生,在商業(yè)文化的包裝下竟搖身一變,同時髦的影星伶人一起占據(jù)了大小報章雜志的各色版面。說書先生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員。然而在這種摩登氣質(zhì)背后,評彈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完成了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卻是值得深思的。筆者認(rèn)為該時期評彈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仍是有限的、不成熟的,并集中表現(xiàn)于表演形式、內(nèi)容等外在結(jié)構(gòu)上對都市文化的適應(yīng),并未觸及內(nèi)在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于是我們便看到外在結(jié)構(gòu)的革新在很多時候?qū)嶋H是對內(nèi)在藝術(shù)邏輯的消解,而由于更廣闊的江南外部市場仍處于傳統(tǒng)社會之中,這對矛盾關(guān)系的沖突又在流動中得以緩和。如今,當(dāng)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不斷提高,傳統(tǒng)藝術(shù)賴以維系的社會基礎(chǔ)已日漸瓦解,如何從根本上實現(xiàn)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現(xiàn)代化變革,同時避免流于表面的盲目創(chuàng)新造成的異化侵蝕,是所有傳統(tǒng)藝術(shù)共同面對的時代命題。
注釋:
①忻平:《從上海發(fā)現(xiàn)歷史—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頁。
②熊月之:《上海通史·民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頁。
③周武:《太平軍戰(zhàn)事與江南社會變遷》,《史林》,2003年第1期。
④次中心娛樂區(qū)有外灘地區(qū);四川北路、乍浦路與海寧路地區(qū);淮海路、陜西路與茂名路地區(qū);南京西路與江寧路地區(qū);靜安寺地區(qū);城隍廟地區(qū);曹家渡地區(qū);兆豐公園地區(qū)。參見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3939》,華東師范大學(xué)2004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192頁。
⑤唐鳳春口述材料,上海評彈團(tuán)藝術(shù)檔案,第24卷第24件。
⑥德惠:《有閑階級的消閑地,平民階級的娛樂場—書場在上海》,《生報》,1938年3月15日,第1版。
⑦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3939》,華東師范大學(xué)2004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第21-22頁。
⑧聿修:《上海各書場寫實》,《申報》,1941年10月23日。
⑨申浩:《雅韻留痕:評彈與都市》,商務(wù)印書館,2014年,第264頁。
⑩微言:《聆余漫談(三) 國內(nèi)播音界之現(xiàn)狀》,《申報》,1933年11月4日,第14版。
11百批:《說會書》,《錫報》,1938年12月26日,第3版。
12橫云閣主:《小世界中小書場》,《鐵報》,1946年6月21日,第3版。
13吳申元:《上海最早的種種》,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9年,第117頁。
14《說書人的誤卯》,《上海生活》,1939年第5期,第81頁。
15 Rifkin.J,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87, p12.轉(zhuǎn)引自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123頁。
16評彈研究室:《周玉泉談藝錄》,《評彈藝術(shù)》第7集,中國曲藝出版社,1987年,第139頁。
17青獅:《書壇瑣話》,《大光明》,1930年4月18日。
18徐云志:《我的藝術(shù)生活—學(xué)藝和演出經(jīng)歷》,《評彈藝術(shù)》第25集,內(nèi)部印刷物,1992年,第57-58頁。
19橫云閣主:《老傷》,《社會日報》,1940年1月19日,第2版。
20逖修:《上海的書場》,《社會日報》,1932年7月12日,第1版。
21茜萍戲作:《盛利開篇》,《上海日報》,1938年7月2日,轉(zhuǎn)引自《中國蘇州評彈社會史料集成》(第一卷),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第650頁。
22笑鳳:《書場生涯衰落原因》,《正報》,1939年5月25日,第3版。
23抽簽:舊時書場中有竹制籌碼,作為聽客入座憑證,上端有孔,散場后收回套入一如燭盤之鐵簽內(nèi)。倘聽客因臺上說書人藝術(shù)平庸,味同嚼蠟,不待終場,即先離座,堂倌例須向其收取書籌,故曰“抽簽”。
24橫云閣主:《抽簽與漂檔》,《海報》,1943年3月27日,第3版。
25橫云閣主:《謝毓菁飛車趕書場》,《上海人報》,1947年10月26日,第2版。
26橫云:《書場中的聽客》,《鐵報》,1946年7月20日,第3版。
27潘心伊:《書壇話墮[五]》,《珊瑚》第1卷第9號,1932年。
28橫云閣主:《評話播音節(jié)目》,《導(dǎo)報(無錫)》,1947年10月22日,第3版。
29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jì)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0頁。
30彈詞名家張鑒庭曾在30年代末多次嘗試進(jìn)入上海市場,盡管此時已在江浙一帶小有名氣,但仍經(jīng)過7次嘗試才最終在上海站穩(wěn)腳跟。
(作者:上海體育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講師、上海市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師范大學(xué)中國評彈文化研究中心成員)
(責(zé)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