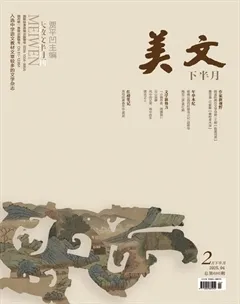梅花三弄
處處陽關三疊,夜夜梅花三弄。一曲琴音,清聲彈落冰梢月。
一弄起
清亮的笛音從遙遠的晉朝傳來。
那是黑暗中潛藏志趣與浪漫、霜威下菊花盛開和青松傲立的時代,那個時代有陶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悠然恬靜,有阮籍“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的嘯歌傷懷,還有王羲之《蘭亭序》墨痕的輕盈流暢,更有嵇康的“參譚繁促,復疊攢仄”之“廣陵”絕唱。魏晉風度或許就是因此而來,壓抑下潛伏的是思想的火花和精神的靈光,更是人性張揚的暗流涌動和知音者的高山流水。
長亭外,古道邊,笛音悠遠,兩個人,一文一武,穿越時空,踏馬而來,這二人是東晉大將桓伊和王羲之之子王徽之。
這日,狂狷博聞的王徽之進京。春風輕揚,陽光閃著金色的波線從對面青山直鋪清溪。清溪兩岸楊柳依依,道上人來人往。當王徽之將船只停泊在清溪碼頭休息時,敦和儒雅的武將桓伊從岸上經過。他們二人互不相識,恰好船中有客人認出岸上走過之人就是音樂才子桓野王。野王是桓伊的小字。王徽之聽說過野王的名聲,便命人對桓伊說:“聽說你笛子吹得好,能不能為我演奏一曲?”
此時的桓伊已是有地位的顯貴人物,但仍然十分豁達大度,他也久聞王徽之的大名,于是即刻下車,蹲在胡床上,出笛吹奏了一曲“梅花三弄”。曲風悠揚,從容舒緩,平和順暢,實乃天地間正氣之音。野王吹奏完畢,即刻上車走了,賓主二人沒有直接交談過一句話。
這則令人稱道的故事源自《晉書·桓伊傳》。《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記載:“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根據晉書介紹,桓伊是武將,被封為右軍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是東晉赫赫有名的“王、謝、庚、桓”桓氏大家族的成員。桓伊不僅有文韜武略,且音樂素養頗為深厚,也許音樂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為人謙虛樸素,個性不張揚,曾立大功而未招忌。正是由于這樣的性格,他才能靜下心來精研音樂,并且做到了舉國聞名——“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蔡邕是東漢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嗜琴如命,他發現柯亭椽是良竹所制,便取下來做成笛子,命名柯亭笛,聲調極美。后來人們以“柯亭笛”“柯亭竹”“柯亭椽”稱良笛或比喻良才。桓伊吹柯亭笛,足見其精深的音樂修養。
桓伊和王徽之二人性情曠達不拘禮節、磊落不著形跡,二人在清溪畔的不期而遇,成就了一首千古琴曲《梅花三弄》的誕生。
二弄承
梅香細細,笛音悠遠,《梅花三弄》始為笛音,后為琴曲,多個琴譜提及桓伊出笛吹《梅花三弄》之調。明代朱權《神奇秘譜》中輯有《梅花三弄》琴曲,曲前小序云:“桓伊出笛為梅花三弄之調,后人以琴為三弄焉。”《杏莊太音補遺》題解云:“桓伊善吹笛,作梅花三弄,后人因其聲,遂擬入琴。其曲一名梅花引,一名玉妃引。”《重修真傳琴譜》題解:“桓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調,高妙絕倫,后人入于琴,其音清爽,有凌霜之趣,非有道者莫知其意味也。”
仙風和暢,琴聲清悠。最早提及琴曲《梅花三弄》者為宋末元初楊公遠,詩人在《友梅吳編校壽宮之側筑庵曰全歸有詩十詠敬次之》其五寫道:“屋瞰梅間倚竹林,一爐香篆一張琴。有時月上黃昏后,三弄寒梅夜正深。”之后元代中期馮子振有《琴梅屋》詩:“三弄花間小院深,玉人遙聽動春心。清聲彈落冰梢月,喚起高懷共賞音。”元代后期葉颙詩道:“琴張甌茗伴爐薰,三弄梅花月下庭。香影孤高音調古,空階誰許鶴來聽。”
月夜、竹林、小院、香爐和玉人,古人于月輝下品茗、聽琴。庭院深深,夜寒霧濃,梅花綻放,琴意綿綿,幽涼的空階上白鶴佇立,諸人莫不春心萌動,而這皆因香清而色不艷的梅花和音調高古的《梅花三弄》。
傲雪之梅乃詩人筆下之魂,歷代文人的筆墨里皆有梅花之英姿,尤其唐宋以來。唐白居易詩曰:“三年閑悶在余杭,曾為梅花醉幾場。”唐張祜有詩:“桓伊曾弄柯亭笛,吹落梅花萬點香。”宋李清照詞云:“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陸游詩云:“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梅、蘭、竹、菊”四君子,梅為四君子之首。梅花傲雪獨立,凌寒而開,其花清麗而不媚,其香清甜而不烈,其枝勁瘦而不蕪,其氣清雅而不俗,它與風雪相連,不與人同流合污,它連接著情緒和意蘊,乃傲骨錚錚、高潔不屈之文化符號。
琴曲《梅花三弄》和賞梅風尚概受宋初林和靖孤山詠梅之影響,日漸引起文人雅士廣泛關注與喜愛,至南宋后期,發展到登峰造極之地步。至元代,文人普遍邊緣化,幽隱野逸情結彌漫士林,琴與梅以其古雅幽逸之格調,成為士大夫文人最為心儀的兩個精神寄托。南宋饒州鄱陽人洪皓,出使金國曾被扣留十余年,面對威脅和利誘,不屈不降,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氣節,最后返回南宋。臨行前夕,他寫下了《江梅引·憶江梅》詞,其中有“斷回腸,思故里。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的句子,表現了詞人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操起綠綺古琴,演奏一曲《梅花三弄》,借梅花的傲霜凌雪比喻自己的堅貞不屈,并以回憶江南的梅花寄托自己對南宋的深切懷念之情。
據考證,琴中大曲《梅花三弄》有
40多個版本,從宋、元,穿越明、清、直至今日。人們將吳景略和張子謙演奏的版本分別稱為“新梅花”和“老梅花”。“新梅花”節奏規整,旋律明朗,曲調激昂;“老梅花”則給人以跌宕不羈之感。
作為笛音和琴曲的《梅花三弄》,飄蕩在歷史和人文星空里的不僅是千年前的名士風范,也因其傲然風骨走進了尋常百姓的情感生活。
多年前的暑假,整日窩在擱幾上的電視機前看瓊瑤著作改編的愛情電視連續劇《梅花三弄》,時至今日,對劇中姜育恒演唱的主題曲仍念念不忘:“紅塵自有癡情者,莫笑癡情太癡狂;若非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許。看人間多少故事,最銷魂梅花三弄。”代表三個動人故事的《梅花三弄》:一弄梅花烙、二弄鬼丈夫、三弄水云間,梅花一弄斷人腸,梅花二弄費思量,梅花三弄風波起。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瓊瑤的《梅花三弄》看得人心潮起伏。
三弄轉
走出歷史典故、文人筆墨和電視劇情,琴曲《梅花三弄》和我之前學的曲子一樣,已在我的靈魂深處緊纏并幽居。
最早接觸《梅花三弄》是初學古琴時,老師發下來的一段泛音練習曲,這是吳景略演奏譜即“新梅花”的選段。拿到選段之前的泛音練習皆為音階訓練,左手食指和名指交替爬弦、觸弦,要求眼睛看左手,不能看右手,更不能左顧右看。按要求練一段時間后,輕盈的泛音果然從指尖流逸而出。隨后老師讓我們練同音不同弦的泛音,左手大指和名指在一弦到七弦的七徽和九徽或七徽與五徽之間輕靈跳躍,初步領略了雙手在高山和流水間閑情放飛的意味,不知不覺不看右手也能觸弦了,對琴的感覺越來越好,學習熱情也越來越高。
火候已到,老師開始讓我們練習《梅花三弄》節選,這是一段旋律完整的泛音片段,可謂濃縮的琴曲。在練習這段旋律時,反復聽《梅花三弄》曲的CD錄音,查看曲意題解,因曲子是以這個泛音節選為主旋律,在低、中、高不同徽位上重復三次,故稱“三弄”,分別描寫了梅花含苞、綻放、舞羽三個場景,喻示梅花在寒風中次第綻放的英姿和節節向上的氣概。
明代楊掄《伯牙心法》云:“梅為花之最清,琴為聲之最清,以最清之聲寫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韻也。”膝上橫琴,梅與琴在《梅花三弄》中達成了至上的默契和最完美的演繹。現代浙派古琴藝術大師徐元白在《游湖》詩中道:“不問升沉且問梅,一枝紅傍水云隈。”從詩中但見一枝紅梅傲立于冰雪和云水間,讓人心生無限遐想和敬意。自此,內心無比向往《梅花三弄》的學習。
頗感遺憾的是,習琴多年,但進展極其緩慢,堪比蝸牛速度,目前正學習已半年過去,竟才學到一半。業余時間總在寫作和古琴間彷徨游離,往往顧了寫作,把琴耽誤了;練了琴,又無暇投入寫作,正可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也。當寫下上述文字,對琴曲的來龍去脈有了基本了解時,尚不能整曲彈奏《梅花三弄》,原因在于心里總想著要先扎實基礎,將好的大曲留著,待日后琴技熟練了再精心研習、打磨。千草萬花,各有其勝,此憾定當于日后彌補。
某日在俱樂部“春之韻”古琴雅集上,一位琴友從容地彈奏了雅集的壓軸曲《梅花三弄》。初夏的陽光透過窗欞,悄無聲息地棲在室內的綠植和書畫作品上,全場肅靜。時光將每一個鮮亮的日子曬成了一束束干花,而《梅花三弄》依然鮮活。
屏息聆聽。十分鐘的曲子,洋洋盈耳。對照譜子和琴友的彈奏,一個靜謐祥和的冬景在眼前徐徐展開:沉寂的大地上,皚皚白雪如一床大棉被嚴嚴地蓋住了山川原野,遮住了萬籟之聲。突然,一簇鮮紅躍入眼簾,那是紅梅。滿樹紅梅,一朵一朵,在冰雪世界中傲然開放。琴友在曲中反復使用的泛音,亦是我彈得最熟練的那個片段,空靈、淡雅,猶如紅梅經歷了風蕩雪壓后正次第綻放。
神思一恍惚,竟隨了賈寶玉從俱樂部往蘆雪庵走去。“行至山坡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數十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也便跟著寶玉立住,細細地賞玩一番。之后,和寶玉一起看眾姐妹在蘆雪庵爭聯即景詩,又悄悄地跟了去向妙玉討一枝二尺來高的紅梅,這枝梅花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花吐胭脂,香欺蘭蕙。等回到諸姐妹身邊時,邢岫煙、李玟、薛寶琴三人已吟成“紅梅花”詩了。“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云來。”踏雪尋梅,梅花,有世間最美的顏色,也有最好的香味。這場景是《紅樓夢》里冬天生活中美的記憶和青春的相處,也是我反反復復最愛看的片段之一。
靈魂歸竅,初夏的陽光與冬日的梅花在琴曲《梅花三弄》里邂逅交集,無限意味盡在曲中。不禁微閉雙目,靜靜感受絲絲縷縷的梅香迎面襲來。
風蕩梅花,欲罷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