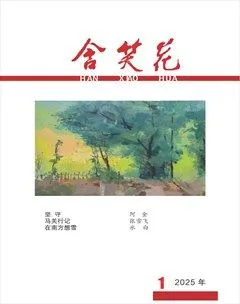如塵
一想到一粒塵埃將從我的身上飄走,飄向不知名的地方,似乎就有什么東西正從我的生命里被抽走。在鄉下,最不缺的就是塵埃,最容易被忽視的也是塵埃。天地碩大,我們僅僅把目光放在作物、牲畜、林草、天氣、疾病,以及被命運驅趕的人事平衡中。人世稍有失衡,便能激起他們的語言、表情和動作的激變,你甚至聽見一個人的咳嗽,腦中便還原出一幅斜肩駝背的老人,在地頭倚靠鋤頭咳嗽的樣子,像黃鼠狼站起來似的古老畫面。
農人習慣關注一些大的事情,大的事情能夠直抵他們的生存境況。你不得不去關注它。盡管這些事情在時間簡史里看起來很老派,但越是古老的東西越有用,關乎生存。麥子長了幾千年,用舊了一批又一批的種麥人、收麥人,麥子依舊站立在土地上,按時令返青和灌漿。麥子不相信隨著日子的輪轉,一年會比一年好起來,人卻相信。所以農人每一次的耕種,都抱有莫大希望,盡管不盡如人意。行走在田間地頭,看到綠油油的麥子,再看看小麥膚色的農人,反而覺得農人才是麥地里最挺拔的那一株麥子,在一天天的日子里瘋長,明知道自己長不好長、不飽滿,還偏要放開一切與生活對賭一把,一生只等待一個秋天的來臨,得到一個好收成。
在日落時候,我曾多次問起農人今年的收成如何,他們總是大老遠笑著搖頭,朝我擺了擺手。他們心事重重的樣子斯文極了。我們一起走過麥子地,穿過玉米地,路過菜畦。他們背上沉重的背簍拖著落日一起下墜,額頭上的汗珠比落日還要大,他們一無所有又兢兢業業。對于時刻縈繞身邊的塵埃,視而不見。事實上塵埃加重了他們的腳步,行走起來不是那么健朗。
塵埃的一生,是極度塵埃的一生,和農人一樣,有著相同的恩澤也抱有相同的命運。
在我人生的前十多年,是目前我最為閑散的一段時期,大風沒有吹過山梁,我可以像一粒塵埃一樣安穩地留在這個村子,哪里也去不了。除了不太感冒的學業,其他的事情貌似沒有以沉重的重量壓在我的肩膀上。上不需要奉老,下不需要伺小。沒有結婚,更沒有任何的家庭負擔,不用擔心以后要怎樣才能活得人模人樣,讓人看起來一副事業有成的樣子。不管未來會走到什么樣的田地,最起碼我還有幾畝零幾分的薄田薄地,那些土地最終會從父母的土地承包合同上回歸到我的土地承包合同上。一個在鄉下成長起來的人,土地是最能安身立命的陣地。有退路的日子讓人心安理得,仿佛一只松鼠儲存滿能夠熬過一個冬天的栗子,可以不懼風雪地睡上一個冬天。
以一粒塵埃的視覺窺見一個村子,村子如塵埃一樣古老,并且在古老的時間里繼續古老,什么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時間的刻刀最多是把這個村子做了一些外部的微調和雕刻。路還是原來的路,淹沒了一些腳印,又增加了一些新鮮的腳印。或者一群人讓路改了道,讓路的指向又充滿更多的撲朔迷離。很多人走上那些條道,有部分人最終回到村子,走上父輩的老路,讓大家明白世界是圓的,你再怎么掙扎,最終還是要回到原點。有的人從這條道走向那條道,一生走成一段不可逆的旅程,回不來了。有的人走進城市,成了他們自己也不認可的城市人。
路的使命,好像更多的是送出去,反而很少迎回來。
還有的人,不是自己走出去的,是被一群人抬出去的,他們的歸宿一般距離村子不遠,村子里終將不會再有他們。他們莽蒼于山河深處,和萬物握手言和。其后多少年,在夜晚風的嗚咽中,會聽到他們咳嗽,在風中傾訴,在田邊地頭看莊稼的長勢,始終不會讓你看見。哪怕是一個逝去的人,他都不肯承認坎坷一生得到終了。
塵埃在風中,風中滿是塵埃。大風還是那些大風,吹過村子的風吹了幾百年幾千年,仍然停不下來。風是最沒有愧疚感的,把人吹沒了就吹沒了,它不會刻意停下來給人以安撫,告訴你這個人被它吹到了哪個地方,茅廬是否被吹破,灶臺是否被吹舊。我們也不會把所有的念想寄托于一粒塵埃,讓塵埃從風的肚子中帶回來消息。一粒塵埃飄搖不定,它沒有支撐但骨頭早已生銹。
人不會因為在風中走漏了人世的風聲而內心沉痛,一陣風的背后是另一陣風,另外一陣風的更遠處,是看不見的風在吹拂,斷然沒有太多的人世冷暖,你察覺得到的事情也不會放逐在風中。風僅存在人的意識里,那一陣涼爽的感覺往往就發生在懷念一陣風的時候。當你張開雙臂面對一陣風時,我們不一定會想到村子,想到老屋搖搖欲墜,想到山林葳蕤,想到貓慈狗孝,但是父輩在風里向即將遠行的你招手示意的畫面,會刻畫在你的一生里。
在沒有學會告別的年紀,他們以這樣的方式教會你告別。像一粒塵埃告別一陣風,讓孤獨的云陪著一陣風遠走,讓一粒塵埃落在另一粒塵埃上。離開風,塵埃缺少了本該有的歡騰,承認了自己的平凡和渺小。我曾在一個午后離開這個村子,在我收拾行囊時,一束光從窗戶爬進來,陳舊的沙發上抖動起陳舊的灰塵。那些塵埃飄浮在空中,從較暗的角落飄進光束里。我看到塵埃如此微小,如此輕浮,我側身攪動的細微氣流就能讓它們快速飄向遠處,那些塵埃給我以很深的印象,像在丁達爾效應下看見了失落森林。每一粒塵埃似乎都在躲避我,又似乎在更遠處窺視我,我們相互嫌棄又相互吸引,我盡量遠離它們。它們不危險我反而不敢靠近,對待善良也應該是這樣的。
一束光讓我看清楚了它們,多么廉價的相會。在這之前,我的關注點從不會是它們。我從出生就住在這個老房子里。房子不大,該有的門窗、沙發、神龕、壁畫是有的。母親很多年前最渴望擁有的縫紉機、收音機也是有的,那是母親的嫁妝。多年不使用已被銹跡占領,一堆遲鈍的零件,依然擺在顯眼位置,成為老房子中零星家具的重要組成。之前神龕最右側還掛有一幅老式掛鐘,機械式的那種,三兩天就得上一次發條,晝夜獨裁著我們成長的細節。如今老掛鐘已停擺多年,時間卻沒有停擺。
一些塵埃悄悄爬上掛鐘去,一片片時間悄無聲息從掛鐘上掉下來。
那時,屋子里的一切就是我的全部,埋著我太多的往事。那些年,我從沒有想過要去創造什么往事,要在這些老物件里碰撞出多少故事,這些通通沒有,僅僅是我需要依附它們生活,讓它們托舉著我活下去。累的時候我可以躺在沙發上,炎熱的時候可以躲進正堂得到陰涼,困的時候可以毫無忌憚地把自己交付給帶著霉味的木床。老物件如此被需要,像母親需要那些嫁妝見證她的愛情。其實母親的一生很苦,愛情并沒有為她帶來什么,因為她曾多次抱怨入錯行與嫁錯郎是多么的不堪。在人世的漩渦里,母親如塵埃,她的愛情亦如是。她的抱怨越來越多,她抱怨時我總要找一些可有可無的事情來做,轉移話題和注意力,讓耳朵拒絕聽見聲音。所以在我眼里,把一生的時間延展來看,有一些時間是殘缺的,母親的抱怨讓我的一部分時間銹跡斑斑,我以為是我拖累到她。
村里的農人命運也不過如此,如一粒塵埃一樣來到這個村子,在這個村子里安定下來,讓許許多多的農活把自己遮蓋得嚴嚴實實。當有一天,農人與農活的拉鋸戰接近尾聲,他們又如一粒塵埃一樣悄無聲息地離開這個村子。誰都不會覺得這是很宏大的事情,他們集體奔向衰老,出生和死亡均是一樣的平常。
在那么多一天一天累積起來的時間舞臺上,他們咬牙熬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即使有個大病小災也不會停下勞作,如果是因為身體原因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他們就等于公開承認自己年老無用。他們的不屈與忍耐,讓我們在顫巍巍的日子里活了下來。他們不會像一朵花一般,想著要無限地熱愛新的一天,努力抽蕊抖粉,不說活得光彩但不暗淡。現在,他們只想讓自己坐穩在人世人倫的風俗里,準備優雅的衰老。
倒是一粒塵埃,在大風的助推下,從農人的莊稼地經過,從牛馬牲畜的脊背經過,從鐮刀鋤頭的銹跡旁經過,甚至從墻壁的裂縫里偷偷溜進正堂或房間,它看到了生活中的汗水和淚水,聽到了哭聲和笑聲,撫摸過傷痕和皺紋,一粒塵埃便有了生活氣。當一粒塵埃降落在農人的衣襟上時,也是輕輕的,一個人的肩膀,再也經不起任何的生活重量,他們亟需片刻的清閑。一粒塵埃能夠壓倒一個活生生的人,像四袋谷子就把騾子壓倒,一背簍玉米就把農人的脊背壓塌,一顆淚珠就能把一個人活生生抓在這片土地上。一粒塵埃的重量,不是因為它里面藏有多少金屬和骨骼,而是取決于生活的熔鑄和鍛造。這樣的事情仍在發生,在這個村子是如此,在看不見的村子,看不見的生存場域亦如此,總有生活的裂縫爬出不屈的靈魂。
在鄉下,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你很難做一個閑人,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苦楚,誰也照顧不了誰,誰也指望不了誰。每個人頭上都頂著一個共同的太陽和暗夜的星辰,誰從生活里走出來,也算不得是棄暗投明。若干年后,等到大家都老了,才會萎縮著身子骨集中到房檐下曬太陽,遠遠看去,和一堆堆經霜的草垛子沒有太大區別。路過的人,僅是瞟了他們一眼,最多以禮貌性的微笑代替打招呼,誰也不會俯下身子去一一辨認。直至有那么一些場景,他們才會從邋遢的日子里抖擻精神,從某種古老的祭祀儀式上集體起身,脆弱的身子骨突然支棱起所有的血肉,仿佛他們還能活更多年。是的,村子里祭龍祭天,最老的他們,將承擔起鏈接現實與神域的使命,操持著與神對話的秘語,與神交流,得到精神鎧甲和護佑。他們朝天跪拜時,我仿佛看到一粒粒塵埃瞬間虔誠起來,排隊飛過村子的上空。
一粒塵埃在空中飄了太久,終究要降落到地面上。
我眼睜睜看著年少時仰望的那些座“大山”,一個個身強力壯,讓農活看見他們都會害怕。春天,他們集體脫去厚實的棉衣,甩開膀子,如一塊犁鏵一樣插入地塊,荒地里的鐵鏈子草,扁毛草、小葉艾草等將永遠與農人為敵,最終它們在鋤頭和耙子的運動戰中把根部交出來。一片土地變得毛光水滑。在一塊土地上,在一段時間里,農人需要土地專一地愛著同一種作物,種玉米的土地,土地就只能無理由地愛著玉米。種麥子的土地,土地就只能愛著麥子,不可以愛著其他的作物,你不能既長玉米,也長高粱,莊稼地沒有太多的自由。如果非要找一塊較為自由的土地,那一定會是菜地,小小的一塊菜地可以同時生長白菜、青菜、花菜、芫荽、香蔥。胃口重的,還允許菜地生長折耳根和茴香菜。栽種這件事不管有多么的復雜,最終都要在春天發生。
春天,農人的身上沾染最多的就是泥土,干干凈凈的靈魂被一層干干凈凈的塵土包裹著。最先走入田地的農人,那時他們二三十歲,已是長大成人的兒女,接替了家里的事情。一場春雨過后,土地表層溫潤,經歷一個冬天的蟄伏,一群年輕人躍躍欲試。他們迫切需要土塊為他們做點什么。幾天的農活下來,犁地的牛累個半死,他們也累個半死,雨水濕不透地層,表層以下的土塊堅硬如鐵。雨水欺騙不了年長的農人,此刻,他們正安然地端坐在家里,下透了雨水他們才會帶上農具從家里向著土地出發。反倒是沒有經驗的年輕農人,他們歇了下來,坐在地埂上,抖抖褲腿上的泥土,陽光下抖落的泥土被分解成若干小顆粒,隨風飛揚,有的落到臉上,被汗液捕捉,有的落在頭發上,水泥漿般把頭發固定直指天空。很少有落在眼睛里的塵土,沙子才容易掉進眼睛里,塵埃不會。
身上的塵土不用抖落得太干凈,帶著土黃色的衣褲,再配上一支不太好的香煙,天地一農人的形象如此具體。一個年輕的農人,勞作一番后,抽煙的時間就是最放松的,淡藍色的煙霧從口中吐出,向著身后吹散。煙霧的走向,也是塵埃的走向。在大坡上,風力強勁,塵埃的流動一直不會間斷,天空有一條道供塵埃流動,只要風不停下,地塊上那么多的塵埃將繼續遷移位置,命定似的。這群年紀輕輕的農人也不會去想,這樣的春天未來還要來上幾個,這個地塊上的莊稼,未來還要青幾次黃幾次,哪怕是農人自己,還能在這個地塊耕作幾次。有一條道是為塵埃準備的,有一條道是為農人準備的,農人如果沒有什么變故,一直往這條道走下去,他們將獨自面對衰老和死亡。
對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農人談論衰老和死亡,顯得有些不道德,任何一處地塊都需要年輕勞動力用自己的汗水從地塊里兌換出相應的糧食,讓自己果腹,然后才能有更多的汗水從汗腺被擠出來,勞動繼續在季節里輪轉。其后的夏天和秋天,是大雨,大風,冰雹,薄霧,也有干旱和洪災。是藥水,鋤頭,鐮刀,背簍,也有耕牛和馬匹。是夜晚的星月,黎明的雞鳴犬吠,娃娃的哭鬧,村里人群的喧囂,也有烏鴉的鳴叫和麻雀的叫喊。只要救護車急切的呼叫聲不從村子里出來,或者救護車的車子不從醫院返回到村子,再大的苦難也很難浸染到農人的內心。
又到一年的冬天,他們才肯放過土地,放過塵埃。落下的塵埃,又加厚了土層的厚度。這個厚度幾乎可以忽略,一顆細微的塵埃放在這偌大遼遠的荒原,算不得什么。一個人多次縫補這些地塊,擦亮偉大的生活,也算不得什么。
其后的那么多年,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很平常,沒有任何可以特別記錄的,也沒有任何雕刻的價值與期許,誰也不會指望著這些農人會把生活過成很美好的樣子。生活是農人的,他們升起炊煙做飯,從自由的土地上采摘蔬菜輔以自己種的稻米下飯。他們允許自己在忙碌的時間里抽出一段空閑的時間,讓牛馬等牲畜解開束縛,走進自然,獲得食物和舒緩。在農人的圈舍里,一群不羈的靈魂總會在一個早晨或者一個午后得到放縱。孩童從小沒有接觸過蹦蹦床、席夢思,他們的溫暖襁褓除了母親的懷抱,就是土地,他們可以在土地上打滾,在地塊間捉蛐蛐螞蚱,蝴蝶的翅膀上載滿孩子童年的夢。在土地上打過滾的孩子長得更加茁壯。
孩子同樣想不到,在未來的某一天,他們也許會擯棄父輩的土地和耕作,尋路進城,或者順江而下,拾取某種活計謀得自己的營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區域,不同的陰晴圓缺下,父與子,母與女,會用著相同的時間做著不同的活計,以此來告慰祖先,我們都活下來了,沒有風調雨順也能飽腹。他們和我們的身邊,那一顆顆不受待見的塵埃,一直緊緊貼著我們的身體,看到了生活的真相,我們卻是眼前空空如也什么也看不見。
當有那么一天,我回到那個村子,當年那群二三十歲的年輕農人,已經白發上頭,粗糙和油質,塵埃順著汗腺進入他們身體的內部,他們小麥膚色更深了,時間均沒有放過我們。曾經那株青綠挺拔的麥子,終于抽穗灌漿,進入了泛黃的階段。而曾經那些更老的人,已經放平心態,允許更多的塵埃爬上自己的身上,先是埋住自己的腳踝,然后是膝蓋,后來是埋住腰部,再后來是埋住脖子……時日不多。到這個年紀的人,開始想到死亡及死亡之后的事,他們先是從山林中請出最粗壯的杉樹王,從山中采來最好的木漆,再從鄰村雇來最優的木匠,為自己建蓋另一種居所。到了鋸木削木漆棺過程,他們隱蔽進行,讓孩子躲得遠遠的,圖個吉利。所以,人活著,必須時刻為死亡這件事去做準備,好在他們已然接受了這一切。死亡來臨的時候,他們打算跟著它去。
他們不老去,孩子怎么長大。孩子長大,卻從沒有想過要把他們推向衰老。
照管自己,將成為他們下一個生活階段需要做的大事要事。一切水到渠成,他們隨著病衰老弱的大部隊,集體回歸到屋檐下曬太陽。人知道死亡世界的陰冷、黑暗和潮濕,所以接近死亡的時候,要拼命地曬太陽,把體內骨頭里的寒氣和潮氣逼出來,讓陽光進入體內,讓體內蓄滿陽光、能量和光明,保證在開始另一種生活的適應期,可以從百無聊賴的黑暗世界里抽出體內的光與火,照亮自己,讓其看清楚周圍的世界。事實上無論他們怎么曬太陽,陽光也很難進入到他們體內了,他們身上有太多的凹陷和深淵,小小的生命也僅能偏居在他們雜亂不堪的器官里,隨時可能崩塌。如果偶爾有一兩天飯食突然劇增,身子骨突然健碩起來,反而讓他們心驚。有一種說法叫回光返照,他們比誰都清楚。人在離去時,能夠讓所有的器官開啟最優模式,就為了吃飽人間的最后一口飯,顯得體面和溫暖。
多年前,他們就在等待一個時刻,內心早已經埋下伏筆,特別是過了六十歲,七十歲,甚至八十歲,每隔十年一次的生日盛宴都能引來親朋好友、門里族內的慶賀,慶賀老人家在塵埃般的生活里又走過了五年十年,實屬不易。對生的慶典像是一場迎接死亡的盛宴。
當你想念一粒故鄉真實的塵埃,以汽車代替打馬再次如一顆露珠般融入這個村子,村子的冷清會讓你短暫忘記生活的事情正一樁接著一樁來到這個村子,你將成為一個局外人,所有的農事與你無關卻是在真實地發生。農村的生活如一陣大風,你就好比木門,你死死抵住洶涌而來的農活,農人的生存境況又讓你不得不把自己完全打開,讓生活穿過你的身子,現實還原農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你胸前永遠別著草木標簽,你將很快變得敦厚樸實和自然。盡管他們會三番五次詢問你的生活現狀、家庭情況、發展狀況,不會作出評價。他們不會在乎你現在正在做著怎樣的重大或微小的事情,即使這件事情才剛剛開始或者走向正軌。他們僅僅是關心你,看見你好好地活著就行。他們不會認為你身上失去了鄉土味的塵埃就把你從這個村子除名。在他們看來,一只鳥落在一個村子,在一個村子筑巢繁衍,那它將永遠屬于這個村子。這只鳥從村子領域之外的地域捉回來的蟲子,也隸屬這個村子。
走進他們中間,呆呆看著這些熟悉且慈祥的面孔,你容易想到幾十年前,那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農人,在與莊稼、農活和老天多年的博弈中趨于平和,他們曾經坐在地埂邊掐滅的煙頭,似乎再次在這個村子復燃和蔓延,如炊煙,如薄霧漸次上升,在天空之上鋪就了一條行走的道路。誰將走上那條道,去向成謎。這次,他們勇敢跨過中年奔向老年,逐漸到了總結的年紀。你不會想到一生中他們做了什么驚天動地的事,甚至當我想寫一寫他們的“偉業”,卻什么也寫不了。倘若我是畫家,倒是很容易記錄他們面部的變化,記錄這個事情將變得容易。可見,遺忘是人間的常態。
我輕描淡寫的一筆,就是他們顛沛流離的一生。當你思考他們為什么活得這么艱難,筆下才會光明磊落地為其留出活路。窮巴巴的日子,你不忍心把他們寫死,你要寫他們的生,寫一個取名返青的村里人把日子活成了人名。
他們以后會到哪里,有著共同的指向,最終的答案不言而喻。每個人都有一道命定的死命題,一邊握定敗北的信念,一邊和這沒有意義的斗爭死磕到底。因為對這個世間愛得太滾燙,所以,天堂還是地獄都成了最不想去的地方。
我以后會到哪里,我也不清楚。有一次,我把自己丟在荒野中,平靜地躺在黃土坡上,我看著頭頂的云朵一片接著一片飄過來,云朵因缺少水汽而內心干癟。在幾分鐘后,它們消失在天際。云朵消失的地方,什么也沒有,寡藍寡藍的天空有些恐怖。天空的任何想法都將落空,我的自我詰問顯得沒有意義。
還是躺在地面上讓人踏實,我的身下和身邊是柔軟的土層,松松軟軟的,散發著泥土特有的味道。我隨便抓起一把土,從左手顛向右手,又從右手顛向左手,泥土越顛越少。一些很微小很微小的塵埃借此機會起飛。一粒粒塵土,將離開一個地方,飛向另一個地方。在這個地方的土,呵護了這個地方的莊稼,草木,雜草,為小動物建造過居所。它掏出自己所有的慈悲,全部付諸重構和生長,你不能說它就因此偉大。它需要這樣的承載方式。飛向另一個地方的塵埃,也許同樣需要做這樣的事。有可能飛到石礫中,成為一片堅硬之間的柔軟,有可能爬上瓦溝,在一陣大雨中被沖刷,也有可能滑進一顆露珠中,成為一顆露珠的主心骨。不管怎樣,一粒塵埃的流浪充滿驚險與浪漫。
我想到草木的搖曳和動物的歡愉,也看到農人侍弄莊稼。在夏天,他們還把稀泥涂抹在牛背上,讓牛可以得到暫時的溫涼。泥土變換著不同角色,滋養著這個村子,以及這個村子之外的村子。那天直到日落我才從那個黃土坡上起身回家,當我撣盡身上的塵埃,看到手掌心細密的土粒,突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我似乎從泥土和塵埃身上弄懂了一些什么。多年以后我再次想起那次雜糅的想法和含混不清的感情,我才肯定,不是我弄懂了土地和塵埃,其實是我弄懂了我自己,我應該如一粒塵埃一般的活。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我弄懂了土地,以及飄搖在土地之上的億萬顆塵埃,我常把它們與溫暖溫潤包容之類的詞語混雜在一起。事實也是如此。每年的清明,我都要撇開案牘之事,陪著父輩去給祖先上墳,祖先的墳地距離村子不遠。小小的幾個地塊,地塊與村子間的億萬粒塵埃,就把兩個世界遙遙相隔,如果需要有一條路串聯起兩個世界,那就只能是心路,它將通向自己。
我們內心有許多條心路,每一個親人的離開,將會有一條心路被重新挖掘和鋪就。走上這條心路的人,都將會成為先行者。先行者沒有任何的獎賞,反而是誰走到最后誰就是幸福的,因為他比別人擁有了更多的時間,享受了更多一點的年歲。最終,誰也走不到最后。幾年時間后,我們先前遇見的那些年紀較大的農人,那些鉆進時間空隙,在時間里刨食的農人,那些抽旱煙流汗水的農人,誰不比誰早,誰也不比誰晚,他們已經走上了我們的心路。從此,有一條塵埃鋪就的心路將通往他們,這是一條不可逆的路子,你的所有想念都將得不到回應。
只有等到清明,我們帶上飯食,穿過地塊,來到他們的墳前,在一年中與他們彼此打了一個照面。雜草長起來了,野花開起來了,墳堆土塌陷了,碑文模糊了。淺顯的幾種自然點綴,讓一個人的一輩子變得多么狹隘和具體。我們向他們的墳堆培土,一鏟一鏟的鮮活泥土從莊稼地回歸到他們的墳頭,仿佛生活的缺陷部分被一針一線縫補。倘若是干旱時節,鏟上墳頭的土將在大風中飛向更遠處。你將會幻想到親人的又一次飛升,得到心理安慰。事實上,這個地塊,這個墳堆將永遠等著你,你來不來它都不會在乎的,就像季節經過村莊,你來不來季節都要穿過村莊,季節不是從你經常走過的那條路上來的,季節是從天空來的,和我們沒有半點的關系。
一粒塵埃沒有選擇從天空逃跑,就會回歸到大地。它的一生就兩個去處,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人的一生也就是一個來處一個去處,中間部分才是生活。你能在生活的中間部分游走多少年,得看自己,也得看造化。在時間里謀求生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你得學會如一粒塵埃一樣的孤獨,習慣一粒塵埃似的飄搖。孤獨不是拿來塑造的,也不是拿來享受的,孤獨就是孤獨,孤獨與熱鬧隔著數條鴻溝。而飄搖讓命運轉折不斷。
在鄉下,你不僅要習慣孤獨,還要了解其他生靈、其他事物的孤獨。你首先得以你的孤獨去摸清一粒種子的孤獨,任何一顆喧鬧的種子,最終都會讓自己孤獨下來。一粒種子,唯一從母體繼承下來的就是孤獨。在農人的糧倉里,農人讓它們躺在樓板上,它們就得一直躺在樓板上。農人把它們裝進袋子里,它們就要接受壓抑和抑郁。不可能翻身,它們金黃色的膚色將不會再改變。可以預見的是,它們將從農人手中獲得好幾種帶著可能性的命運,或許被當作牲畜的口糧,或者被賤賣,從這個村子離開,到另一個地方,讓自己變成酒精或飼料。最好的應該算是成為一位“母親”,重新回到熟悉的土地上,重新把那些土地和塵埃再認識一遍。最好的往往也不能如愿,被選作種子的玉米粒越來越少,就像一個農人,夢想著好日子有一天會回到自己身上,哪怕時間把他熬倒了,他同樣不能如愿。
這是關于莊稼人的孤獨。多少個日夜,他們把癱軟的自己投放到月光和星光下,手捧自己半滿的人生,準備揮霍。
第二天,他們又很正常地回歸到生活中,繼續用自己的孤獨,驅趕著耕牛的孤獨,去侵擾地塊里雜草的孤獨。最終讓你看到的就是,一個孤獨的農人扛著犁耙,趕著一頭孤獨的老牛,在一片孤獨的地塊,翻動著孤獨的地塊。太陽碩大,孤獨蔓延。耕牛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慢條斯理的走路,不緊不慢地咀嚼枯草,地塊在時間的漏斗中逐漸翻個身,像大地翻開關于種養的經書。一整天,農人和耕牛,在時間里比較誰比誰還慢,他們將在那片地塊度過,時間的韁繩拴住他們一整天,有雨的天氣也不能讓他們停下來。這一天過后,這些事將成為蒙了塵的舊事,可以不管不顧。明年,這樣的事情還會繼續在這里發生,只是不會是現在,它們藏在遠遠的未來。
四季的輪轉里還有很多的孤獨等著他們,其后的栽種管理和收割,農人三三兩兩,把自己撒向大地各個角落,拾取前人的舊生活,做著前人所做的舊事。哪怕是一家子人,在勞作中也不會找一些話題和樂子供彼此消遣,他們的口頭交流換成了肢體語言,似乎每一句語言都是多余,每一個動作都不多余。他們描述不出來苦生活的樣子,卻在經歷著苦生活。從他們身邊經過,便能看到塵埃圍繞著他們飛舞,孤獨又加深了鄉土的特質。
除了習慣孤獨,農人還要習慣難能可貴的熱鬧,他們不可能在孤獨里長久地消失了自己的語言功能,得感謝紅白事的主家。紅白事上,他們依照風俗和禮數,幫助主家做著分配給自己的事。忙活下來,一群婦女圍坐下來,就著日常事擺著鄉土話,時代卸掉了她們手里的針線,她們只能撥弄自己手頭的老繭,一雙無處安放的手。一群男人圍桌而坐,用搪瓷碗喝大酒,主家人不停地斟酒,酒過三巡,他們熱鬧起來,互相接近,讓兩只耳朵門對門打開聽彼此的話。說到高興處,彼此拍著彼此的肩膀,塵埃起舞。宴會散去,他們將回到各自小房子,推開斑駁的木板房門,又把月光、星星、蟲蟻關在門外。有許許多多的夢將在這個小村子的上頭匯聚,有的夢多年后會成真,有的夢僅僅是夢,夢里夢外是不一樣的天地。多少年來,人們都在學著做好夢,始終沒有人能夠學會一輩子只做甜美的夢。
一粒依附在人身上的塵埃,間接地見證了新生宴、喬遷宴、新婚宴、壽慶宴以及白事宴。一個人,似乎就是為了幾場宴會來到人世間,宴會完畢,一生蓋棺論定。
白事用來收尾,一個人撇開全部農事,褪去所有人情世故,隱入九泉,從此什么事也不會再和他有關系了,他將永遠孤獨。牛馬還在圈舍,雞鴨悠然散步中庭,貓狗換了主人,依然能夠從新主人那里獲得食物。莊稼可不行,沒有農人的耕種,一塊莊稼地如同菜蔬地一樣得到了自由,雜木雜草自由生長。在村子里,任何一塊地塊都有姓氏,這是張家的地,那是李家的地,隔壁還有陳家的地。農人在,土地就在,農人不在了,土地放荒,失去姓氏的土地流離如塵埃。荒蕪的土地,將和流浪的塵埃在一起,它們的孤獨需要鳥雀來檢驗。
一粒塵埃的一生,其實就是一個人的一生。習慣了孤獨,也習慣了喧鬧,還要習慣飄搖。飄搖同樣是人生常態。從村子出發遠行的人,常處在漂泊中,一生飄搖如燈火。我年輕時隔壁的鄰居,十多年前從村子飄向滇東南的省會,從工地上拾取一輩子也捆扎不完的鋼筋,一輩子也挑不完的水泥砂漿。在八年前的春節后,又被一場大風吹向貴陽,實現了從一個高原向另一個高原遷移的壯舉,依然是挑不完的磚頭,拌不完的砂灰,奮不顧身地給城市的樓房增磚添瓦,還想扎根做個真正的城里人。又在五年前,被一條江運抵江浙,理織不完的線。有一次,她誤把上班時的照片發到家族群里,她的身邊是運轉的機器,可以想象得到絲線在機器中來回穿梭的畫面。她,正在作繭自縛。一個蟬蛻的形象在我腦中浮現,在飄搖的生活里,她終于為自己造就了一個遮風擋雨的居所。讓自己活下來,完成了活下來這件天大的事情。
至今我對她敬佩有加,一個女人,一個老實本分的農村婦女,在生活的小船里擺渡,全然把擱淺的風險撂在一邊,獨自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我想,當有一天,她轉身回望自己的一生,會不會想起那段艱苦的青春,一個人拼了死命地勞動,像一株長在沙漠里的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結籽的壓力上。
村子里的飄搖,更多的是命運的飄搖,雨水什么時候來,冰雹為什么來,持久的干旱,推門而入的疾病,等等,都將左右一個人的命運。我們常聽到耕牛在耕地時倒下便死亡,某個年紀輕輕的農人,在勞作間倒下,留下一生的遺憾卻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在一場大風大雨里,在一場冰雹雷暴里,多少顆心懸掛在村子的上空。所以農人不會去想,明天要去干什么,一個星期、一個月、半年后要去干什么,一年后某塊地要有多少收成,某個大牲畜要賣多少錢,要在某年某月某日為家里的長輩辦個壽慶。這些都不用去管,先把今天活好,就從命運的手里扳回了一局,贏得了新的二十四個小時。后天的賭局會是什么樣子,等后天再說。
在村子里的那幾年,我一直以為這是農人懶惰的表現,隨著人生的船滑向生活的險灘,我才知道以這樣的生存哲學應對生活,很是智慧。農人也好,莊稼也好,草木生靈也好,甚至還有那些離開家鄉遠走他鄉的人也罷,不管如何去討生活,最終,仍舊是與塵埃握手言和。千百年來,一粒粒塵埃收藏了多少舊人舊事,從不言語。好在,每一種生活都沒有自行慚穢,每一個生命都不曾卑微。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平庸和不易,面對生活的悲戚,沒有誰選擇逃離,從這片土地上拾取生活并使勁深耕下去,養活自己,照顧好家庭,遼闊的土地因此欣欣向榮,讓每一個故事在結束時,都擁有完整的尾聲。
行走人間,我們避免不了與一粒粒塵埃撞個滿懷。塵埃里,我看到了生活,看到了百態,看到了命運,看到了眾生,更看到了隱忍和接受,不屈和堅韌,也看到了自己。幸好光陰是大方的,被萬物平均分取,讓生命的圖景因此而遼闊,即便洋相百出也讓人充滿活下去的欲望。捧起一抷土,想到一個村子的命運,想到一群人的來去,我常常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空氣中,一粒粒塵埃從粗糙變得柔軟,似乎研磨了一個人間。
【作者簡介】張一驍,男,云南文山人,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美文》《滇池》《散文詩》《青少年文學》《鄂爾多斯》《牡丹》《含笑花》等刊物,有作品入選《中國當代詩人代表作名錄》《云南文學年度選本》散文卷、詩歌卷、文藝評論卷和兒童文學卷等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