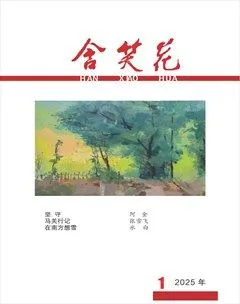半世鄉愁花非花
于故鄉,從屈原的秭歸、卡夫卡的布拉格,再到木心的烏鎮,他們總是在追隨著血脈的印記,渴望回到那難以歸去的故鄉。故鄉是假的故鄉。因為是假的,才會有人肆無忌憚地揮霍;因為是假的,才會有人小心翼翼地端起手中的酒杯;因為是假的,所以在他們喝下哀怨和滿眼情仇的時候委屈流下了不甘的淚水。然而,故鄉是真的故鄉。因為是真的,矗立在北回歸線秘境北緯24度的黃金緯度生存帶;因為是真的,孕育了源遠流長的稻作文化;因為是真的,早在五千至一萬年以前,就有先民在此開拓繁衍。一樣,我也坦然地生在這里,勞碌奔波地活在當下。
有人說,故鄉像不停旋轉的魔方,以獨特的氣質煥發出誘人的魅力,以超凡脫俗的姿態對峙整個世界的喧囂。我思考再三,欣然默許。
其實單純用眼睛無法觀懂故鄉的深厚底蘊,故鄉像一朵縹緲的云彩,得借助時間和空間的維度。
廣南稻作銘
句町故地秀山佳水,平川平壩無暑不寒,古生野稻福圣離離。
百越之族食之馴之,仰以天時得其地利,耕之作之嘉禾猗猗。
千頃其碧百里其馨,民以為天國以為珍,春生南畝獻冬帝京。
有日有月歲貢百擔,谷之秀者玉粒清芳,稻之美者古品其秈。
有上畦者辟為御田,稼稿之功傳以千年,米中之花貴為八寶。
清風搖穗膏雨抽苗,往來種作勤我民人,盛世無饑豐歲無饉。
飲水思源落實思樹,刻石以銘懷古祈福。
崇禎四年八月十四日
據載,故鄉的米因其米粒雪白透青,粒大飽滿,潔白油光,隔夜不硬而享有盛名。清道光五年《廣南府志》記載“歲貢百擔”,是故鄉人背馬馱到縣境西洋江下游的板蚌碼頭用木船運至廣西百色轉運朝廷。其實,故鄉大多時候是溫暖濕潤的,充沛的雨量,適宜稻谷生長,是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地,是傳播稻米之路的起點。與河畔樹碑立傳的石碑對證,背后竟是一段壯鄉人民水運貢米進京的歷史。
故鄉的春事,是忙碌的,至少童年的我是這樣以為。過完年,初五,天氣晴朗,家里便組織鋤糞、攤曬、敲打破碎、堆漚腐熟有機肥料,多半會在正月十五前后開始種植大豆和花生。其實一年的時間里,該做什么在奶奶那里都是慣性勞作,其實大多時候她更像鄉村的農事地圖,她能清清楚楚聽到第一場春雷,在那個電閃雷鳴大雨瓢潑的夜晚起來,找出年前備好的良種用簸箕拍種子,嘴里念叨著“醒來了,醒來了……”她總是害怕種子醒不過來,像我害怕祖父、父親、奶奶、母親和二嬸再也沒有醒來一樣,這些從我半世人生中消失的親人,總是我久久不能平靜和忘懷的心事。如果生命有輪回,他們一定是化作了故鄉的蘆葦,要不我怎么會在蘆花飛飛揚揚的日子多次夢見過他們。
人活一世,終要直面功名利祿。那些看似繁華熱鬧的表象,往往會讓我貪戀和紙醉金迷。故鄉的童年都很純真和守信。那時候鄉村還沒有電視機,錄音機也是個奢侈的物件,是那群會唱《把根留住》半大孩子的專屬空間,他們擠在土坯房的木樓板上,不輕易讓我們這群吵鬧的小孩靠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童,在傍晚玩著一個叫“打噠噠”的游戲,對半分成敵我兩派,看見敵方用手比成手槍模樣能及時喊出“噠噠”對方即被消滅,靠邊等待全軍覆沒,然后開始下一局。口吃的伙伴在這游戲中很是吃虧,本就先看見敵方冒頭,用手比成手槍模樣就是喊不出一個字來,白白當成活靶子被對方消滅。大部分時間,主要還是協助家里干些簡單的農活,比如撿豬食和干柴火。撿豬食多半是姐姐的活,我不貪玩的時候偶爾能撿撿干柴火,每次背回干柴火不管分量多少,奶奶總夸獎我進步很大。但是貪玩的劣根早早形成,砍自己家石榴樹修陀螺,割開整條自行車胎做橡皮槍、造竹魚槍。喜好在河邊捕魚撈蝦的我常常是誤了家里的晚餐,誤了農事,更是誤了如今半世過往還碌碌無為的人生。
歲月悠悠,故鄉漸老,對萬物的期待從熾熱變為淡然。總希望炎熱夏天綠油油的稻浪再長高一些,晚些成熟,再晚一些,家里就不會這樣忙忙碌碌。事實是,故鄉的人生下來就永遠地忙碌著,都埋在無休止的農活中。一場雨后,曲線婀娜的河流漫過河堤,是個捕魚的好季節。放學歸來,奶奶用裝化肥的塑料口袋剪出三個小洞給我套上,剪開另一個口袋套上麻繩做成披風,扣上斗笠我仿佛我成了無所不能所向披靡的俠客,提著小桶穿梭在風雨中撿拾一些隨洪水上岸的小魚和泥鰍。有時候我常常想,那些年我的奶奶怎么就不擔心我迷失在風雨里呢?或許,她只是不想阻攔我快樂的童年。那年我從縣城讀初中暑假歸來,半個勞力的年紀承擔家里最輕的活計放養耕牛,久病臥床的奶奶吃力地起身坐在老屋的木梯上等我回家,她想多看看我,看看這個還未長大失去父親的孩子。那一年夏天,她坦然地走了,像當初她不擔心我迷失在風雨中一樣釋懷。
如故鄉的風般行走人間,在這半世的旅途中,坦然地想放下無所窮盡的絕望與孤寂。每一個人,都有只屬于自己的獨立和孤傲。就像我的父親,一生平凡卻又坎坷的一生,初中畢業想要參軍報國,在祖母強勢的阻攔下淡然接受。接受了結婚,接受了生兒育女,也接受了他坎坷而懊悔的一生。為能給子女更好的生活,他在我母親生我的前幾個月參加外縣架線組扛電桿,不幸倒地中風終生偏癱,同時也傷及五臟六腑。我出生后他常抱著我依坐在老屋的石凳上,看護著他少年時種下的檸檬樹,對著夕陽沉默不語。往后的日子他再怎么堅強和努力也無濟于事,可能是擔憂異樣的目光他極少外出。偶爾,也是顛顛簸簸匆匆忙忙歸來,似突然長出了條尾巴被人踩在腳下,三十七年簡單走完他的一生。我童年的時光,家里不斷找尋郎中、求取偏方為父親治病,形形色色的藥,記憶中最深刻的是一個郎中要求找來白色的茄子作為藥引。而如今想來,種種的努力都有悖于科學常理,只是那時的我們都愿意相信他能夠好起來。
是時候停下來,看晨光熹微,看星云散落。是的,不是所有的人生章節都有好的結局,但串聯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一生。很多年的夢里,奶奶和母親的織布機仍在凌晨與拂曉交替之際“吱吱呀呀”作響。每天的睡眠僅四小時卻辛苦勞作的一生,她們積勞成疾,過早離世。挑水、砍柴、栽種、織布就是她們簡單的一生,把艱難困苦過成豐衣足食樣子。其實我沒有理由沮喪,她們不希望看到我沮喪的人生。于情于理,都應該拋開世俗快速成長,長成故鄉有堅實脊梁的男人。家庭之重,人情之重,社會之重,需要填補。果未熟而葉落,葉落而歸根,豈止是無可奈何。于自己而言,把過往揪出來縫補后撕碎,再縫補再撕碎,撕開一道前進的路。那些伴隨生活的疑惑,無法彌補的遺憾終究還是要辨明方向從蒼茫煙雨中走出。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過是心不在焉時的短暫休整。喜怒哀樂未發,終于還是接受了這份安寧,半世的漂泊,讓鄉愁在歲月的長河中逐漸沉淀。對于故鄉我不曾離開,每一步前行的腳印,都承載著對這片土地眷戀深深。兒時的歡笑,伙伴們的追逐打鬧,田間小徑上的野花芬芳,成了記憶中最珍貴的寶藏。那熟悉的山川、河流、炊煙和至親,是心靈深處最為永遠的慰藉。早已缺失那些赴火的勇氣,偶爾心血來潮,也習慣了不去觸碰那些所謂的糾結于心的往事。大多時候,我佯裝倚在墻院里,故意不回頭,讓身后的半世鄉愁漸漸塵封、腐朽直至支離破碎。不與過往針鋒相對,不與過往糾纏不休。不亂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將來。最后只剩下熱血沸騰的情愁,溶解在故鄉的河流里。
【作者簡介】王遠速,文山州作家協會理事,廣南縣文聯兼職副主席、縣作家協會主席。作品散見于《農業工程技術》《云南日報》《云南經濟日報》《魯西詩人》《含笑花》《文山日報》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