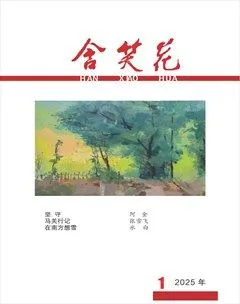壹角錢
深秋時節(jié),大地寒氣森森。
換季,也該換裝。我在臥室翻箱倒柜。
當我埋頭苦苦尋找自己的厚衣服,一堆舊書無意中與我產(chǎn)生碰撞,頃刻間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攤滿一地。其中一本,嘩啦啦地翻開它的肚子,呈上來一張壹角錢紙幣。我將那張壹角錢的紙幣正對著傍晚的光束仔細端詳。它老舊,平整又殘缺。突然間,我透過這張壹角錢捕捉到有關于大伯的記憶。
我的大伯有點特別,他是個農(nóng)民,又跟其他農(nóng)民不一樣。
在過去,生產(chǎn)隊隊員都要參加集體勞動,我的大伯也不例外。別人鋤地犁田,他跟著鋤地犁田,別人割草打谷,他跟著割草打谷。但是別人干完活回家納涼休息,他還要拎起一只紅十字診箱,走家串戶。是的,我的大伯既是一個農(nóng)民,也是一個村醫(yī)。大伯長久目睹鄰里鄉(xiāng)親久病不治之苦,初出茅廬的他便意識到,疾病比貧窮更易奪人生命。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成為赤腳醫(yī)生。
在擔任赤腳醫(yī)生的幾十年里,大伯一邊給人治病,一邊自學醫(yī)書,床頭柜上總擺著幾本厚厚的醫(yī)學書籍。坐在門后的竹椅上歇息的間隙,他都沉浸在書海里。村里的道路一片坦途,我的大伯在十里八鄉(xiāng)仍享有威信,沒有在時代更迭中黯然退場。
當赤腳醫(yī)生的幾十年里,大伯總結(jié)出一套獨門絕技,專用來治療小病小痛。有人發(fā)燒、咳嗽,他會開幾服藥,或是打一針藥水,不出幾日,病人便能恢復往日的生龍活虎。有村民在上山或下地時不慎被割傷,大伯會用乳膠橡皮筋扎緊創(chuàng)口往上的部位,緊接著用浸泡碘附伏的醫(yī)用棉清理血污,倒上土黃色的藥粉后再用紗布包扎。過個兩三天,那人的傷口就結(jié)上一塊血痂,又過四五天,血痂就像老掉的樹皮般慢慢剝落,傷口漸漸痊愈。
有一陣子,山里大雨連天。我們幾家人聚在大伯家吃飯,樓梯口突然響起一陣急促凌亂的腳步聲,緊接著門口出現(xiàn)一個狼狽的病人。他一只手緊緊捏著另一只手上通紅的小臂不放。他的臉、眉毛和鼻子緊擰成一道道溝壑,雨水流淌其上。
“在地里磕到了石頭,孩子他大伯快來給我弄一下。”
話語伴著他急促的喘氣聲艱難地吐出,顯得十分吃力。
實際上,門口剛有動靜,大伯就站了起來。一聽這話,他立馬沖進臥室倒騰起來,只聽見房間里“哐當、哐當”地響。又一眨眼,他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那人身邊。
“保子(堂哥的名字)他娘,創(chuàng)傷粉用完了……”
大娘匆匆跑出屋外,折回時手里帶著一大把被揉碎的綠葉。刺鼻、苦澀,熟悉的味道,使我瞬間認清它的名字——青蒿。大伯一把接過青蒿葉,敷在那道被涂成黃褐色的傷口上,又用紗布纏繞起來。起初,那里還有一點兒血色滲透出來,后來就像被定格一樣,停了。
來人慢慢熨平了痛苦的神色,他說:“多虧有你,真的太謝謝了。”
大伯說:“這兩天雨大路滑,鄉(xiāng)鎮(zhèn)上的集市去不得,青蒿到底不如創(chuàng)傷粉,你就先別干重活了。”
還有一次,一個嬸子抱著孩子來找大伯。我好奇地往她懷里打量,一個圓嘟嘟的兩歲孩子昏昏沉沉地躺著,臉色有點發(fā)黃。
大伯仔細端詳了小孩子的五官后,又抓起小手反復檢查。恍惚間,小孩子用身體輕微地擰動手臂,爾后,依舊昏沉睡去。
大伯問:“這樣子多久了?”
“兩三天了。”嬸子的回答滿是憂慮,她說,“他大伯,趕緊給娃兒開服藥吧。”
大伯搖頭,似乎已經(jīng)找到癥結(jié),他說:“扎一下就行。”
只見他用手指使勁一壓,小孩子的大魚際肌就像一塊布料緊繃起來。嬸子一只手從腋下穿過,將孩子的身體往深處摟,另一只手牢牢抓住孩子的小手臂。
當時兩人突如其來地流露出嚴陣以待的姿態(tài),讓我倍感好奇,內(nèi)心因此產(chǎn)生無限的緊張和期待。大伯從診箱里翻出一把小針刀,隨著刀尖閃電般地扎進皮肉,一聲清亮的啼哭,瞬間打破沉悶的空氣。
“有白白的東西跑出來了。”我大呼小叫起來,滿眼驚奇。
大伯充耳不聞。他越發(fā)用力地捏,那哭聲旋即更加高亢。但是越來越多的乳白色絮狀物,也跟著從針刀扎破的口子跑了出來。
包扎好了之后,嬸子如釋重負地離去,我迫不及待地問:“那團白色的東西是什么?”大伯說疳積,挑疳積。我繼續(xù)追問為什么要挑疳積。大伯又說,因為營養(yǎng)不良,不挑出來就沒胃口吃飯。
大伯說的果然沒錯。兩天后,我專程跑去嬸子家,嬸子告訴我小孩子又吃飯了。
對于孩子來說,還有比挑疳積更害怕的治療手段,比如打針。打針時,大人們會架起粗壯的胳臂,如同鐵鉗將他牢牢控制。大伯則會用指腹反復按壓那露出的半截屁股,尋找最合適的注射位置。
如我當時那般年紀的孩子正受制于人,只能被迫聽著后腦勺傳來的,那些酒精盤子與藥瓶碰撞的雜亂聲響。那聲音尖銳而刺耳,一下子咬住人心底的恐懼。
“我不要打,不要……”
膽小的孩子終于忍不住,放聲大哭,開始拼命掙扎。
“聽話,可不能亂動啊!”
大人們生怕針頭扎偏或弄斷,勒得更緊了。
一針下去,孩子捂住屁股,哽咽聲斷斷續(xù)續(xù),他像是一臺破舊的拖拉機,在艱難地啟動。臉上,也全是凌亂的淚痕了。這時,大人們也會露出疼惜的神色,哄著孩子。
“沒事了,不哭啦,不哭啦……”
但無濟于事,因為孩子已經(jīng)看到大伯從臥室走出,手中又多了幾包用廢報紙裝好的口服藥。于是,哭聲沖出了屋外。
我的大伯在行醫(yī)治病時不茍言笑,固執(zhí)認真,可是他在私底下又是另一個樣子。
小時候,我和弟弟妹妹常喜歡到大伯家玩。大伯總愛坐在門后的竹椅上,一見我們,便笑瞇瞇地說:“快來給大伯拔白頭發(fā),快來。”
那時的大伯,才五十出頭,身體硬朗,腦袋就像一只長滿尖刺的刺猬,拔起來頗為費勁。
“略略略……”一群調(diào)皮鬼沖他扮鬼臉,然后自顧自地玩鬧起來,要么在堂屋追逐嬉戲,要么躲在家具后面捉迷藏。大伯也不生氣,任由我們鬧騰,任由我們野蠻探索。
等到我們玩累了,大伯又開口說話了,還是笑盈盈的。
“快來給大伯拔白頭發(fā),快來。”
這回,大家不再置之不理了,爭先恐后地跑過去。一群小腦袋轉(zhuǎn)眼間就將大伯圍得水泄不通,橫七豎八的小手像一群覓食的小鳥,在黑色的發(fā)叢中扒來扒去,眼神專注地搜尋著任何可疑的顏色。
大伯的白頭發(fā)本就不多,因此得像開荒一樣,劃清界限,分配到人。左邊側(cè)面歸他,右邊側(cè)面歸她,后腦勺的“坡地”歸你……分好后,大家便趕緊找、趕緊拔,生怕別人趁自己低下頭去找白發(fā),一時間還不能抬起頭來留意周圍的時候,偷偷越界。
一旦越界,免不了又是一番爭執(zhí)。
“走開,你怎么能跑來搶我的?”
“明明是我的,哪有搶你了!”
任憑你磨破了嘴皮子,對方也絕不承認,因此爭執(zhí)愈演愈烈。但大伯從不制止,反而饒有興致地看著我們。于是,兩邊吵著吵著,高亢的聲音就沉落下去了,手腳也變得更加利索了。
不一會兒,白發(fā)絲就被我們掃蕩一空。大家互相環(huán)視一圈,發(fā)現(xiàn)每個人手里也沒攥著多少白頭發(fā),多的才四五根,少的也就一兩根。于是,大家的目光又從手中的白頭發(fā)上爬到了大伯的下巴。
“我們給您拔胡子……”
拔胡子就不能再劃分歸屬了,只能看誰的動作更快更準。很快,昨天才冒出來的胡子就被拔光了,前兩天長出的胡子也早在昨天的胡子被拔光前,就被拔掉了。只有今天新長出來的胡子太短,不好拔,才幸免于難。
拔完白頭發(fā)和胡茬后,大伙兒站成一排,滿懷期待地等著大伯來清點。大伯數(shù)起白發(fā)和胡茬來有板有眼。他先咳兩聲潤潤嗓子,再掏出隨身攜帶的那副黑色老花鏡戴上,最后才神色肅穆地開始數(shù)。因為大伯數(shù)白頭發(fā)和胡茬的時候極為專注,所以我們沒等他數(shù)完,就打心底里認可了他得出的結(jié)果。
“還得是你們眼睛靈光……來來,每個人拿好了。”大伯挨個數(shù)完,就像對待敵人一樣,一把將他的白頭發(fā)和胡茬摔進垃圾桶里。接著,他心滿意足地賞給我們一筆零花錢,有的給一張壹角錢,有的給了三四張壹角錢。
“大伯,要不然我再給你拔點?”我們心頭火熱,又笑嘻嘻地圍住大伯,作勢要拔掉那些變白跡象并不明顯的發(fā)絲。
“你們幾個小家伙,真要把大伯頭發(fā)拔光啊……”大伯抬手往我們腦袋上拍了一下,大家見狀一哄而散,拿著他給的零錢買零食吃去。躥出門的一瞬間,我清楚地聽見身后傳來爽朗的笑聲。
大伯的白發(fā)一天比一天多,給他拔白頭發(fā)也漸漸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情。后來我一進大伯家門就問:“您要拔白頭發(fā)嗎?”
大伯從不拒絕,總是笑著回答:“好呀!”
不知不覺間,這件事就變成了我們之間的默契了。
再后來,我家從山腰搬到了山腳,我又時常離家求學,這份默契便悄悄地躲藏到了回憶的深處。
今年入秋,母親告訴我,我的大伯又到鎮(zhèn)醫(yī)院住院去了。她叫我抽空去看望。掛斷電話,我不敢耽擱,立刻驅(qū)車踏上前往鎮(zhèn)醫(yī)院的路途,去探望我的大伯。
那日,夕陽用橘黃的色彩在天邊肆意揮灑,而病榻之上的大伯,卻仿佛一抹暗淡的影子,對外界的一切呼喚,只能報以微弱的回應。我看到大伯蜷縮在歲月的縫隙里,他那原先像刺猬一樣的腦袋,現(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絲稀疏、滿頭花白。我猛然驚覺,我永遠也不可能再為他拔光那些白頭發(fā)了。
【作者簡介】劉應平,小學語文教師,青海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作品見于《中國青年作家報》《西海文藝》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