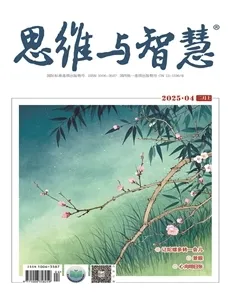舊時的別離
年幼不經事,悟不了詩里別離意。少年時,愛上看閑書寫閑字,喜歡為賦新詞強說愁,某日讀到了柳永的“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忽然就頓悟了別離的情緒,連帶著有關別離的畫面在腦海里都具象了起來。
在那些車馬慢,跋山涉水見一面,一別可能就是永遠的年月里,離情別緒是可以無限放大,可以恣意渲染的,千種離愁萬種哀傷唱成歌的別離。一切都那么情有可原,那么入詩入畫。
直到后來,成年后遠離了故鄉,別離于我也成了家常便飯,才知道普通人的別離,哪有那么多的詩情畫意,更多的是煙火溫情與來不及訴說的傷感。
小時候生活在總也走不出的小村子里,一門心思急切地盼著長大,真正長大了才知道要面臨那許多的別離,與朝夕相處的家人別離,與形影相隨的同學別離,與熟悉的故鄉山水別離……那時候交通不便利,最早的時候村子里連條像樣的能通車的馬路都沒有,出遠門要到鎮上去坐大巴車。
第一次出門,父親和母親三四點就將我叫起床。其實行李在前一天的晚上就收拾好了,起那么早是因為要走兩個多小時的路才能到鎮上搭車。帶著母親備的干糧,父親幫我挑著行李,我們在天未亮時的桃花山腳下走著,光繞著山腳都走了近一個小時,那樣幽靜的山邊的晨,那一條條還未蘇醒的鄉間的窄窄的沾著露珠的田間小路,偶爾還伴著不知名的動物的咕咕的叫聲。父親走得急,走得快,我走一段就要跟著小跑一小段,那樣急促地跟著,哪還有沉溺于離愁別緒的心境?到了車站,腳酸腿酸,遠遠地就看到大巴車來了,匆匆地拎了行李上車,汽車絕塵而去,等到坐好,看到父親的身影在視線里越來越小,直到小得只剩下一個模糊的點都還沒有挪動一點點位置時,別離的傷感才后知后覺忽地涌上了心頭,滿懷酸楚,眼里的淚便跟著順勢而出,止也止不住了。
后來,一次又一次地離鄉歸鄉,交通一年比一年便利,再也不用起大早走遠路去趕車了,定著鬧鐘提前些起床,收拾好行李,父親和母親幫著將大袋小袋的行李拎到家門口的大馬路邊,一起停在路邊等車,一邊等著,一邊和父親母親聊聊天,聽著他們絮絮叨叨著:出門要照顧好自己啊,在車上顧好自己的東西,尤其是錢,火車上有扒手……偶爾會有到田里做事的鄰居經過,停下來打個招呼就加入了一起聊天的行列。然后,遠遠的車子到了,停在了身邊,因為就是附近村子里的人開的車,自然也多了份人情味,下車打招呼,幫忙提行李,關車門,在親切而熟悉的鄉音里,故鄉熟悉的山水田地在視線里漸漸遠去,父母的身影也一起在視線里漸漸遠去。許是年歲漸長,別離已成常態,縱然心中彌漫著不舍,卻很少再淚濕眼眶。
再后來,因為我遠嫁,父親和母親偶爾也會從安徽到福建住一段時間。對于父親和母親的到來,每每是接時歡喜,別時傷感。好在那些年的老車站、老站臺,慢慢的綠皮火車,緩慢了別離的時光,也緩解了那份傷感。
記憶里,火車由近而遠,長鳴的汽笛聲里火車慢慢駛離車站,能很清楚地看到母親在車窗前不停揮手。現在想起從前那些在熙熙攘攘的火車站前或者夜靜時分清冷的舊站臺前,輕揮的手,抬眼可見的微笑,依然有深深的懷念與彌漫于心的溫暖。那舊時的交通,緩慢有緩慢的好,別離的時光也跟著慢了起來。那些慢時光里的別離,是那么地真實,雖然少了一些詩意,卻帶著溫度,帶著真真切切的人間煙火氣息。
如今,火車越來越快,站臺越來越大氣也越來寬敞,出行越來越快捷了。只是,母親年歲大了,認識的字又不多,我們再也不敢讓她獨自一人乘車來福建,或者獨自乘車回安徽了。那舊時的車站前,緩慢行駛的列車,和在車窗前輕揮著手的,尚年輕著的母親,再也不會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編輯 兔咪/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