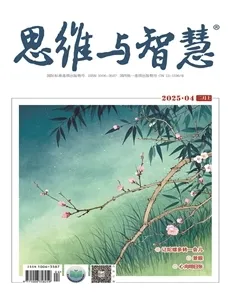俏生生的紅窗花
進臘月,娘像換了個人:往常,她的臉上帶著疲憊,不停忙碌,隱忍勤懇,像一頭耕作的牛;而到臘月,迎年的熱情點燃了她,娘有時竟哼起了小曲兒,玩起了剪紙。
其實,娘平時也做剪紙,左鄰右舍的嬸嬸大娘經常來向她求鞋樣子、襖樣子。她把舊報紙拿在手里,問清多大的鞋號、多大的尺碼,略一沉思,便操起剪刀下手剪,左繞繞,右繞繞,一張鞋底子或碩大的襖片子就出來了。大家夸娘手巧,娘笑說,是剪多了,熟生巧。
我最喜歡看娘剪窗花,像變魔術似的。她能從一疊平板板的紅紙里,眨眼間掏出活靈活現的紅窗花來。記憶里,我們的窗紙上總有一幅艷艷的“喜鵲啄梅花”;炕圍子上總有十幾個翹尾巴狗兒,馱著“福”字繞成一圈;而門板上的兩個“福”字,都是有故事的:“福”的“衣字旁”里,是大公雞昂頭看一盞燈籠,右邊的“田字底”里,是小羊在吃草……
其實,臘月的日子也不能說清閑。從喝了臘八粥,日子就被排好了程序,天天有主題。置辦年貨趕大集,吃的穿的,貼的用的,鳥銜枝一樣,東一枝西一枝往家搬;撣塵掃屋,清洗衣物,給家里每個人做新衣新鞋,做豆腐,蒸年糕,灌粉腸,蒸饃饃,煎炸各種吃食……娘和爹一項項完成著迎年的項目。在這些活計間隙里,娘會在一個下午或晚上,說:“咱們剪窗花吧。”
于是炕上安一張小方桌。我們脫鞋上炕,在炕上嘰嘰嘎嘎,邊打鬧邊看娘剪窗花。
娘把柜頂上的彩紙取下,認真地疊成方格、三角形或菱形,然后將剪刀插進紙里。我們好奇地看著,看剪刀一張利口之下,那艷艷春意是怎么被掏出來的。嘿,那剪刀好像有自己的路,它不疾不徐、緩緩前行,左踟躕,右停頓,行一步,退一退,這兒掏掏,那兒裁裁……最后,那個銳銳的紙角,被娘咔嚓剪去。紅紙層層展開,一幅“喜鵲啄梅”便簌簌脫胎而成。娘雙手端著,將它在窗格子上比畫。白生生的窗紙,映得那“梅”鮮艷炫目。我心里“咯吧”響了一聲,被那種鮮明的搭配震驚了。
娘剪窗花,是從小跟姥姥學的,姥姥又是跟太姥姥學的。擱現在,算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了。然而,我娘總不滿足于姥姥教的花樣,總想自己創個新。姥姥說,你娘啊,心性高哩。
我們年年跟娘剪窗花,也不覺學會了剪些簡單的樣式。我發現,娘有時剪著剪著,手上會停下,剪刀好像迷路的孩子,不知道要走向哪兒。娘蹙眉遲疑著、琢磨著,又左右比畫著,還不讓我們大聲嚷嚷。她那入神的神態,很嚴肅,我們不敢再聒噪。終于,娘的剪刀再次起步了,簌簌簌簌,七拐八拐。這拐來拐去的會拐出什么好玩兒的花樣呢。
娘抿著嘴,也不言語。最后謎底揭曉:娘剪的是一頭老牛,牛身上三朵梅,牛犄角上三道紋兒,眼睫毛長長的,牛頭低著往前猛拱。那年,我們迎來的是牛年。
現在想,我娘一個普通的農婦,整日做的就是撫養兒女、操持家務、喂雞喂牛、下田跟土地莊稼打交道,而她的精神世界里還珍藏著一派美的世界,真是難得。
娘剪完窗花,就指導著我們去貼。我們爬上窗臺,抹糨糊,貼窗花,貼好了,用手細細地撫平。娘又讓我們到屋外去看看。那時,昏黃的燈光,透得窗紙一片朦朧,就在那方朦朧上,隱隱透出一枝梅,梅枝上喜鵲昂著小巧的頭;窗紙四角,是四只流蘇飄飛的紅燈籠……簡陋的小院子里雪花飄著,一切單調沉寂,而這洞溫暖的窗口,傳遞給我們的,像夢里的世界……
如今,娘不在了,剪窗花的事,我卻鐘愛著。我沒有娘的巧手靈心,只會一些簡單的花樣,但我年年都要買紅紙,剪窗花。稚拙的,吉祥的,紅火的窗花,貼在玻璃窗上,有春天的一團喜氣,也有一種天長地久的傳承意味。
(編輯""""高倩/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