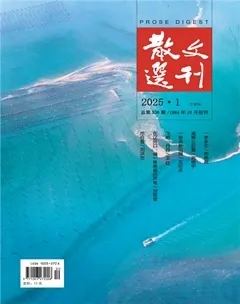古寧洋的色澤
褐色的詩意
走在雙洋古鎮,探尋古廊橋,太平橋、青云橋、登瀛橋、化龍橋,古廊橋的始建時間,便是它們的年輪,四座古韻廊橋,連著寧洋的前世今生。我仿若穿越時空,在那流水里找尋,找尋那褐色的詩意。
走在廊橋上,在寧洋河水之上,看流水如何優雅地流過,看著形形色色的鄉人從橋面走過。廊橋,為寧洋添著一道亮麗的景致。古褐色的橋身,古褐色的欄桿,泛透著古樸厚重的光。轉折地,或方或直,或剛或柔婉。清水間,橋身婉轉時,那一處景便多了委婉。你走過廊橋走進街市,那里的明清古厝與廊橋一樣透著大氣精巧而淡雅。
因了這橋,因了這唯美。小小的橋,給人有借景生情的空間。
四橋同暉,寧洋人是巧思的,用那靈巧的手,梳理著在橋面上的歲月與記憶。即使是一座不足幾步的小橋,也要取個讓你歡喜的名,在橋的兩頭一筆一畫地將字鐫刻在木板上,或篆或隸,或工整或飛舞,如蘭亭,如碑石,并用朱染漆。也讓我們的幾步出走的步伐有如蓮花步履,情韻纏綿。
寧洋古廊橋,當為景觀,如果你站立其中,也隨之入了景。如果你走在橋上,步履一定要很輕,心思一定會悠然的。抬眼間,是白云舒流,俯首時,是曲水緩走。水里的草,終是靜的,它走不出這曲婉,繞不出這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有人青絲變白發,有人在這里結姻緣。如若你有緣,往那橋上的亭子間輕輕一站,便會成了明清時的開頭詩。倘若你有緣手扶欄桿,雙眸眺遠時,便會是宋詞里的憑欄意景,水流千古,閑愁亦千古。
古寧洋人是喜歡繁麗與曲折之美吧,所以,那拱洞里的水也彎彎地美著。廊橋在寧洋人眼里亦是唯美的吧,所以,這里一定承載著情與愛的,他們在橋上相見,在橋上誓盟,又在橋上離別。
樸素的干草黃
干草黃,這也許在美術書上是難找的顏色,其實,亦是我或者許多人一直珍藏又忽視的色彩。
走進小鎮,這個百年老鎮。古老的城墻只余下一角,我立于那里,望向遠方,彼時的心,可以很安寧,可以很踏實。我的眼神游蕩著,發現一個在田里收拾稻草的婦人,很合適這樣的顏色。
那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五十歲光景,說不上漂亮,但絕對不難看。那是一種健康結實的婦女形象,是一種純樸、淡定的村婦。
她的家應是在鎮的周圍,或許在鎮上某個地方。也許她的家就在那一排排古厝里的某個屋檐下,也許,她一抬頭就能看到自己的家,那里也許一樣的收藏著她生活的所有點滴。
這時候,不是收成的時候,可我明明看到她在那里忙碌著。如今鎮上如她一樣地道的農民已經不多了,她在收拾田里的稻草,神情像極了服侍自己的親人那般的專注。金黃的有著同太陽一樣的色澤的干稻草,橫七豎八地躺在干田里,如此可見當初收割時的匆忙。她用有勁兒的手掌將稻草一一聚攏,整成一堆,扎成捆,放在田坎上。田埂上,放著三三兩兩的捆扎好的稻草,如嬰孩兒一般躺在一起,她的眼里流出溫柔敦厚的神情,有著母性的慈祥,她依然彎著腰在地田里不斷地拾揀。
我不知她這樣專注地揀拾稻草是為了做什么,背去當柴還是墊床鋪,還是鋪豬圈,還是為了燒灰做肥料?不管怎樣,這些稻草在她眼里一定是有用的。她一定是需要它們。
不久的時間,她把那些一束束稻草放在夾背里,不費力地背著它們在烈日中。那如嬰孩兒一般的稻草依偎在她的背上,她的腳步依然有力而輕快,我看著她一步一步消失在風中。
黛青色的暖
夏荷,在晨露中風姿綽約,遠處那一片黛青中一朵小荷,自顧自地盛開,纖柔,素雅,如此美好。
我推開那敞開的大門,水仙茶,老蒲扇,竹搖椅,在一片黛青色中顯得那么的祥和。老人笑著,古銅色的臉充滿歲月的痕,我走上前,拉著他的手,用寧洋語問候,他驚喜地抬頭,說:“寧洋人?”如孩童般的笑顏讓那暑氣也充滿清爽。
寧洋人是好客的,隨意推開個門,不管你是哪里人,只要上屋來,便是客,他看到推開門的我,快樂地呼喚老伴兒續茶,拿出西瓜,我們坐在老厝的木椅上,老人把目光投向屋外荷塘,喧鬧的人群,追逐的人們,他的眼中充滿溺愛,充滿平和。此時天井里投下了一束光,溫暖地投向我。
我們說著古寧洋話,聊著家常,聊著古寧洋故事,好似相識很久很久。續著水仙茶,好像在續著古厝與老人的前世和今生。風過,他起身,淘米水在嘩嘩地流,口里說:“兒女都在城里,我和老伴兒習慣了鄉村生活,守著這個家,孩子才有歸家的心緒,現在的生活千好萬好。”笑容里寫滿故事,這些故事深藏在皺紋里,綻開一朵歲月的花。
“孩子,在我家吃飯。”我笑著說:“還有好些人呢。”“哦哦,你們是一群的呀,他們都會說寧洋話嗎?”我說:“只有我會說。”老人說:“那就在這里吃,他們走他們的,呵呵!”他那彎曲的腰,蹣跚的腳步,有一種篤定的幸福。
我站在清時的屋檐下,黛色的青石板被歲月的水刷得沒有了棱角,閃著亮光,倒映著一些身影,如一撂撂厚厚的書,我將用更長的時間來細細翻閱;如一把油紙傘,把巷子里的過去和未來分開,一如一幀幀畫,掛在巷子的深處,讓我頻頻回望,以靜默,以安寧。
褐色,干草黃色,黛青色,這是三百八十九年沉淀的暖,是古寧洋人的氣質,是古寧洋的色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