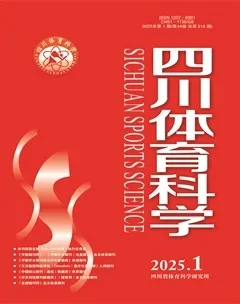巴蜀地區漢畫體育圖像探析























摘" 要:巴蜀地區出土的漢代畫像磚題材多樣,其中體育圖案引人注目。追溯到漢代,“體育活動”往往由軍事活動、生產勞動、娛樂活動演變而來。文章根據巴蜀地區出土的漢畫圖像內容,將體育圖像分為軍事性和娛樂性兩大類,同時分析了巴蜀地區漢畫體育圖像的淺浮雕藝術手法、夸張變形的動態造型技巧,以及視覺法不統一的藝術效果等。
關鍵詞:體育圖像;漢畫;藝術表現;巴蜀地區
Exploration of Han Painting Sports Images in the Bashu Region
CAO Xinfang1, WANG Lingjuan2
(1.College of Fine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Han Dynasty portrait bricks excavated in the Bashu region have a variety of themes, among which sports motifs are striking. Dating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sports activities\" often evolved from military activities, productive labor,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Han painting images unearthed in the area of Bashu, the article classifies sports images into two categories: military and recreational, and analyzes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of shallow relief, exaggerated and deformed dynamic modeling, and the inconsistent visual effects of Han painting sports images in the area of Bashu.
Key words: Sports images; Han painting; Artistic expression; Basho region
中圖分類號:G812.9"""""""""""""" 文獻標識碼:A
嚴格說,中國古代并沒有“體育”一詞。在大多學者論著中,提及“體育”,則是從其由來、藝術價值,形成的社會背景以及在現代漢語言語境下對其進行分析。以現代競技體育活動的定義來辨析,巴蜀地區符合其定義的漢代體育圖像并不多,但也不能否定中國古代有體育活動。通過漢畫圖像可以看到漢代巴蜀地區的體育活動。
顧森先生指出:“漢畫像在作為美術作品前,首先應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或社會現象來看待。”體育活動的開展與社會穩定發展有一定關系。漢代巴蜀地區民康物阜,人民安樂,巴蜀地區出土的體育圖像較多描繪娛樂生活方式。體育活動并未脫離人們生活,在其技巧展示上,增添了娛樂性與競技性。
漢代巴蜀體育圖像題材繁多,通過文獻整理和田野調查發現,巴蜀地區漢畫中的體育活動圖像主要表現有射箭、角力與角抵、田徑、武術武藝等。主要出土于成都平原、重慶各區縣。圖像造型方面,淺浮雕和線條結合展現參與者矯健的身姿以及精彩的對抗場景,創作出極富韻律、動感的畫面;視覺方法不統一的構圖特點,將圖像從二維空間向三維空間縱深。
1" 巴蜀地區漢畫中的娛樂性體育圖像
漢代巴蜀地區娛樂性體育活動在日常生產勞作,貴族游樂中產生與發展,主要有跳丸、跳劍、水上運動、棋類等圖像。其中,巴蜀仙道思想使棋類圖像造型獨具特色。通過圖像分析出巴蜀地區娛樂性體育活動大多是以表演的形式呈現,圖像一旁常有觀看者形象的描繪,這類體育圖像展現了肢體的技巧性,但作為體育活動缺少競技性。
1.1" 豐富多樣的百戲圖像
在《漢書·武帝紀》中就有描述舉行角抵戲時,三百里內的人都來觀看角抵的場景,足以說明漢代角抵戲規模盛大,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喜愛。巴蜀地區出土漢代百戲圖像數量較多,項目形式豐富。這類漢畫圖像發現于成都、新都、廣漢、宜賓長寧、樂山、重慶璧山、重慶九龍坡等地。主要有跳丸、跳劍、弄壺、疊案、舞輪、倒立、沖狹、旋盤、舉重等圖像。不同項目的圖像組成百戲圖,往往一幅畫面上有多種項目的圖像。
張衡在《西京賦》中就有描寫百戲項目:“鳥獲扛鼎,都盧尋撞,弄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其中,跳丸與跳劍屬于手技類雜耍,是指三個及三個以上的丸或劍在表演者雙手上進行有規律地拋接。跳丸與跳劍在形式上也分上肢豎拋與上肢橫拋,下肢站立與下肢跪式。表演者手持物體的數量與排列方式也有差異。在江安一號石棺石窟百戲圖中左側跳丸,跳劍圖像為上肢豎拋,三個丸呈三角形排列,相互間距較小,位于表演者頭部以上。懸于空中的劍則是劍首為內,劍尖朝外指向三角形內角方向。在造型上能與其區分的是彭州太平場出土的跳丸圖,圖中表演形式為上肢橫拋,表演者頭部和下半身為側面,上半身為正面,雙手呈托舉狀進行拋接。
巴蜀地區是否有三個球以上的跳丸圖?答案是有。在璧山一號石棺石刻百戲圖中表演者則使用五個球進行表演,表演形式為上肢側拋。表演者側身拋接,手中的球與空中的球呈規律排列。也有呈現不規則排列的,在永川石棺“雜技園”中三顆球體呈倒三角形式,劍的運動軌跡也未形成嚴格的三角形構圖。巴蜀地區出土跳丸,跳劍圖中并未出現嚴謹的程序化構圖,不同地方出土的圖像在刻畫中也有細微的差異成系列。如拋體在空中呈現不同的方位,物體固定的數量等細節。
在巴蜀地區出土的百戲圖中,弄壺這一形式僅有兩塊畫像磚刻畫,分別在合川石棺與成都市郊。表演者將常見的陶壺拋向空中,用身體各個部位連續地拋接在空中運行的壺,由此壺落于表演者肢體的不同位置。如成都市郊羊子山出土的百戲圖中,表演者赤裸上身,左肘弄壺,右手持劍,劍上又弄一壺,側身望向手肘處,下半身半蹲降低重心,展示了表演者高超的技藝和弄壺運動的驚險性。
漢代巴蜀地區疊案倒立圖像形式多樣:直立倒立、反弓倒立、彎弓倒立。疊案數量無固定數值,多則十二個,少至一個,無一不展現表演者矯捷身姿。表演者也有性別差異,可通過圖像中的發型與服飾來區分。如彭州太平場百戲圖中女舞者手肘置于十二層木案之上,支撐全身力量,身體呈“C”字形,刻畫出女舞者身體的輕盈與柔軟。值得注意的是,圖中疊案刻畫由二維向三維轉換,畫面開始講究透視關系。
百戲圖中也有沖狹圖像,沖狹分雙人手持和單人支架,指一人將竹席卷成一圈,圈內有小尖刀,表演者靈活地從中穿過。宜賓白溪石棺石刻圖中一人手持圓圈,另一人做預備沖刺的動作,雙手高舉合并,身體橫于空中,雙腳點地發力,一整套動作好似“鯉魚躍龍門”,靈活輕巧。
1.2" 多彩多姿的水上運動圖像
巴蜀地區地形、地貌復雜多樣,河流密集。獨特的地形使漁業成為漢代巴蜀人們獲取生活物資的主要來源。漢代巴蜀地區出土的水上體育活動圖像,也佐證了漢代該地區漁業發達。同時,軍事斗爭也刺激了水戰技能的提高,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戰國宴樂壺下腹部的水陸攻占場面中,船上三人前后排成一排,手持船槳,動作整齊劃一,在船下可見有人與魚游動。《西京雜記》中武帝作昆明池:“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習水戰。”描繪昆明池中船:“樓船各百艘。樓船上建樓櫓,弋船上建弋矛,四角悉垂幡旄。”漢武帝建昆明池來訓練,樓船上修建瞭望臺,裝有可刺可鉤的戟,升級作戰船的裝備,從而提高作戰的勝率。船這一造型頻繁地出現在畫像磚上,如在彭州出土采蓮圖中船呈彎曲狀,將人容納其中,進行采蓮活動。畫面左緊右松,疏密結合,線與形相輔,散落的荷葉賦予空間縱深感。這時,船從軍事作戰工具向生產生活工具轉變。
垂釣是一項古老的漁業生產活動,巴蜀地區豐富的魚類資源使休閑垂釣活動由生產性逐漸向娛樂性過渡。東漢班固《兩都賦》中:“揄文竿,出比目”文字記載表明東漢時期,人們就對魚竿進行花紋裝飾,注重漁具的觀賞性。在四川樂山麻浩一號崖墓出土的垂釣圖中,一名頭頂朝天小辮漁民手持魚竿,魚竿因魚的重量呈彎曲形狀。魚圖案的大小與魚竿彎曲的程度,都說明這是一條肥美的魚。
彭州出土的漁筏畫像磚中,竹筏上站立兩人,后者手持竹竿撐船,前者半蹲捕魚,水中動物在竹筏一側游動。通過畫像發現,巴蜀人們捕魚方式多樣,借助不同的工具。巴蜀地區豐富的水資源為人們提供更多的生活物資和娛樂方式,也展現該地區獨特的文化資源,悠閑的生活情趣。
1.3" 古老有趣的六博圖像
棋類運動作為益智類體育活動,是當時最受歡迎的游戲之一。《西京雜記》中記錄了許博昌善陸搏,樂于此而編寫了一套六博術口訣。巴蜀地區六博尤為盛行,六博又作陸搏,是一種通過擲采行棋角勝的古老搏戲,是一項擁有勝負之分的競技體育運動,因雙方對局各用六枚棋子,六枚骰子,故有六博之名。巴蜀地區出土的棋類圖像具有濃厚的仙道色彩。巴蜀是道教主要發源地之一,蜀地特殊的“巫”文化也為道教的傳播提供了基礎,人們把仙人的游樂比作神仙擁有的日子,希望在死后也過上逍遙自在的生活,從而形成的“仙道”思想也在畫像磚中體現。如四川新津出土的仙人六博圖,兩位仙人相對盤坐,肩披羽飾,神樹、棋盤、仙人位于同一高度。圖像刻畫了仙人夸張的動作和專注的神情,說明博弈過程的精彩程度。在仙人六博畫像中,除了有仙人形象,后人也會把“羽人升天”的思想傾注于鶴身,由此在巴蜀出土的六博圖中,常有仙鶴,仙草圖案交代創作背景。在成都市郊六博圖右下角,就有仙鶴這一象征性造型,畫面四人兩組飲酒下棋,瀟灑至極。
2" 巴蜀地區漢畫中的軍事性體育圖像
秦漢交際,巴蜀地區軍事地位上升,民間習武風氣濃厚,出現角抵戲、舉重、射箭等體育圖像。軍事性體育圖像活動是由軍事戰斗演變而來,對于勝負的定義更加明確。這些圖像起初出現于宏大的戰爭場景,社會逐漸穩定后,成為貴族和百姓增強體質鍛煉的體育活動,畫面內容更具趣味性。
2.1" 展現力量的角抵舉重圖像
南朝梁任昉在《述異記》中記錄:“秦漢間說,蚩尤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曰蚩尤戲”。角力是一種近戰肉搏的技術,也是考驗雙方耐力與力氣的競技活動。如郫縣石棺石刻角抵圖像,一人頭戴異獸面具,用頭上的角攻擊對方,右腳高抬發起進攻。重慶九龍坡區陶家鎮大竹林胡人相撲圖像,刻畫形象為胡人,這一新題材表明漢代美術從域外吸收養分進行創作。胡人夸張的高鼻梁,光腳赤足,赤裸上身徒手搏斗。獨特的服裝花紋,發飾都與漢代人物造型相區別。角力是一項競技性體育活動,在不斷發展與演變中,也成為一種職業,宋代出現了從事該項目的專業運動員,他們的任務就是研究摔跤,練習摔跤。
舉重物在圖像中因被舉的器物不同,運動項目名稱也有差異,如扛鼎、舉石頭等。綿陽三臺郪江的力士像,力士雙腳彎曲馬步狀,雙手高舉過頭支撐石頭。這些活動作為力量性活動,運用夸張的刻畫手法展示了力士強大的力量。
2.2" 方式多樣的射御圖像
射御活動歷史悠久,西周時期,教育體系中的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射、御”是修身養性的體育活動。秦漢時期,射箭活動更為普及,不僅作為貴族的娛樂活動且在軍事戰斗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西漢時期,禮射活動幾乎廢止,射箭作為軍事戰斗武器,在抵御邊防入侵中具有強大作用。在巴蜀地區出土漢畫像中射箭圖像造型包括弩射、弋射、獵射等。
2.2.1" 弋射圖像" 弋射是指在箭挺尾部系長繩,射中物體后引線而取,線上系矰。弋射的主要目標是天空中的飛鳥。在出土的漢畫像中不難發現弋射所發射的不是長箭,而是系在繩上的短箭。在成都羊子山弋射收獲畫像磚中,畫面下部分為收割勞作圖,上部分左側兩人跪坐于地面,左手持弓,目標為天空中大雁,兩人瞄準方向不同,畫面構圖完整,空中、水中、岸邊層次分明。弋射作為一種狩獵手段,具有實用性與娛樂性。漢代以后,弋射也逐漸被其它形式取代。
2.2.2" 弩射圖像" 最初弩的結構十分簡單,在一根木臂上安放一竹弓,木臂后方有一把懸刀。在發展中,弩的使用技巧、造型也在提高改進,木臂的造型由粗糙的圓弧向更利于發射的彎曲造型精進。巴蜀地區漢代蹶張圖像多出現于墓門上,也側面反映了蹶張具有保護和防衛的功能。蹶張圖也有不同的造型,如四川內江巖崖墓的蹶張圖,力士以雙足踏弓,手臂用力拉弦。上臂高隆足以證明操作此強弩并非輕而易舉。在三臺縣安居崖墓出土的擘張圖中,同樣將上臂刻畫更加粗壯來證實這是一項需要力的體育運動。
2.2.3" 獵射圖像" 獵射是早期人類生活獲取物質的主要方式,后發展為貴族娛樂的活動。統治者每個季度會舉辦一次大規模的射獵活動,以儉樸聞名史書的西漢文帝也經常是胯下千里馬,手中金雕弓,擊兔伐狐,可見他對該項運動的喜愛。成都西郊的鹽井圖中為確保工人運鹽過程的安全,一旁有涉獵者進行保護。扭曲重疊的線條表現出巴蜀地區山路崎嶇,野獸聚集危險十足。右上一人跪式持弓對準山間野獸,而另一人好似在一旁進行勘察。在重慶合川出土的荊軻刺秦王故事刻畫中,持弓者全神貫注瞄準眼前的惡虎,絲毫不敢懈怠,渲染出緊張的氛圍。
2.3" 動感十足的駕馭圖像
我國古代,車馬結合造出了世界最早的戰車,戰車在斗爭中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在使用時,須掌握駕車馭馬的技能。而今馬術競技是一項傳統體育活動,在內蒙、甘孜等地每年都會舉行聲勢浩大的賽馬節。在富順石棺駕馭圖中士兵在馬背用弓箭射擊敵人。戰射是一項難度很大的運動,不僅要求士兵熟悉馬術,并且需要足夠的勇氣與高超的射擊技術。畫面對中馬兒飛馳時狀態的刻畫,烘托出聲勢浩大的戰爭場景,展示了士兵高超的御馬技術和其英勇奮戰的精神。在眾多出土車馬出行圖,駕馭有多個形式:一人騎從、兩馬一軺車、三馬一軺車等。在車隊伍前也會有騎吹奏樂,騎吏來確保長途跋涉的安全。
2.4" 勇猛善跑的伍伯圖像
在前進的車隊中,最前端往往是被稱為“伍伯”的善跑者。他們不僅是王侯的隨行,在戰爭中也是前方戰況的傳遞者。在戰爭頻發的年代,通過大量培養善跑者來提高軍事信息傳遞的速度,有利于領導者對作戰布局進行調整,善跑仍是后來軍隊對士兵基本身體素質要求。在德陽畫像磚伍伯圖中,四人一腳前邁,一腳后蹬,身體重心前傾造成畫面重心前移,畫面也就有往前推的感覺,整個畫面像是正在行軍的隊伍,斗志昂揚地飛奔向前。與伍伯圖像構圖相似的四騎吏,也是采用同一物體多次刻畫,動作的差異使畫面富有起伏感。而馬匹作為珍貴的作戰、貴族出行工具,古代數量較少,伍伯也擔任了傳遞信件的送件員。
3" 巴蜀地區漢畫體育圖像的藝術特點和表現手法
“漢代畫像磚、畫像石是藝術品兼商品(喪葬用品);它們的制作,就兼有藝術創作和商品制作雙重目的。”“視死如生”的墓葬觀念,使漢畫像刻畫題材不再局限于祥瑞故事和勸誡故事,還有對于人世間的留念。漢人相信人死后還會在黃泉相見,黃泉與人間有著相似的社會結構,因此體育圖像的出現,是墓主人生前的娛樂與體育生活的寫照,也是希望在極樂世界有著同樣充實生活的愿望。
巴蜀地區畫像磚藝術表現手法有別于其他地區,很多學者在研究我國漢畫像時,常以地域劃分探討每一區域的構成特點。不同地區的經濟、政治都是導致其生產物質差異的原因,從而形成不同藝術特點的漢畫像。研究也由附屬文字研究轉向圖像內容本身的研究,從美術的角度來看漢代巴蜀地區體育活動圖像的藝術特點,對體育圖像造型藝術以及對圖像空間位置進行解析。
3.1" 夸張變形的動態造型
漢承秦楚文化,受陰陽五行是在不停交替變化的思想影響,在漢畫像繪制時賦予其強烈的動感。巴蜀地區漢代體育圖像呈“動”態,很少看到靜止的技巧造型。畫面上的動作可能是某一瞬間的呈現,在畫面之外該動作也有延續。“動”態在不同畫面中的處理也不同。如成都青杠坡四騎吏圖像,四匹馬均作跨步向前狀。有人回頭張望、有人緊跟其后,馬首不同的方向也使畫面更具起伏感,呈往前推的“飛動”感。馬匹奔馳中四肢奔跑交替地刻畫,是線與形結合,使得畫面顧盼有秩、張合有度。在跳丸與跳劍表演時,畫面中的丸與劍在空中呈現接讓關系,如江安二號石棺石刻百戲圖,同時出現下肢跪式側拋的跳丸與跳劍圖像。圖中兩位表演者單腳跪地,側身相對進行拋接,空中的劍與丸在手勢的接應下形成固定的運動軌跡,這樣的“動”態增強空間流動性。再如六博畫面中,羽人肩披的羽毛隨仙人的動作起伏,飛動的羽毛使畫面充滿激烈緊張的氛圍;沖狹時表演者懸于空中造型體現了瞬時性,“動”態是巴蜀地區漢畫體育圖像最顯著的藝術特點。
漢畫像磚、石對人有種震撼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夸張變形的藝術手法。藝術需要強調,更需要夸張變形。漢代巴蜀地區體育圖像運用夸張變形的藝術手法使畫面更為生動。如三臺擘張圖,畫面中將手臂夸大與細小的下肢形成鮮明對比,失調的比例證實拉動弓弦需要很大的力氣。仙人與百戲圖中人物相比,形象被拉長;在宜賓白溪石棺石刻雜技園圖中,不同項目分散在一塊畫像磚上,人物刻畫較為矮小,通過壓縮人物高度削弱雜技的驚險性,從而展現表演者穩健的身姿。
3.2" 寫實的淺浮雕手法
信立祥提出漢畫像的雕刻技法可分為線刻和浮雕兩大類。“線刻技法表現的重點是物象的輪廓,而淺浮雕表現的重點是物象的質感。”如彭州太平場的倒立疊案圖,女舞者形象用淺浮雕雕刻,浮起較低,腰帶和衣服褶皺則用陰線刻來刻畫。而疊案圖像僅用陰線條刻畫,突出清晰的物體輪廓。兩種雕刻技法形成繁與簡的對比。
漢代巴蜀地區體育圖像采用陰刻、淺浮雕、淺浮雕加陰刻等雕刻手法將圖像內容展現得淋漓盡致。如長寧7個洞崖墓中騎馬者圖像內容沒有邊界分布于畫面中,圖中陰線刻簡潔地勾勒出馬的造型,造型稚拙,粗獷的陰線刻更顯古拙之風;東漢成都羊子山出土的四騎吏繪制技術逐漸成熟,馬匹的刻畫更加寫實,馬蹄、馬嚼子、馬鞍都有細致地刻畫。淺浮雕與凸面上刻以陰線,增加馬匹的體積感。
從長寧七個洞窟的陰線刻,到成都羊子山墓四騎吏圖立體而生動的淺浮雕,巴蜀地區漢畫像雕刻水平在變化中發展,趨于成熟。一幅畫像所呈現的雕刻技法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技法組合。淺浮雕加線刻的技法使畫面更為精細,這是巴蜀地區體育畫像使用最多的技法,在璧山一號石棺石刻、成都羊子山弋射收獲等圖像都有使用。
3.3" 視覺法不統一的藝術效果
顧森在表述中國繪畫的構圖形式指出:“不受焦點透視的那種由固定視點引起的視角局限性制約,也不著眼于由特定光源而發生的明暗和色彩變化。努力表現其顯露在外而深藏不露在內的神韻”。漢畫圖像沒有固定的界限,圖像間距離隱含了漢人對于宇宙方位、尊卑倫理的理解。
“在漢畫像中,存在著等距離散點透視構圖法和焦點透視構圖法兩種空間透視構圖方法。”漢代巴蜀地區出土的體育畫像構圖大多采用底線橫列法,如長寧一號石棺石刻和永川石棺石刻中百戲圖像橫向排列在畫面的同一底線上。這樣排列的圖像形象幾乎都為正側面,更側重二維空間,無法表述事物間的縱深關系。東漢時期巴蜀地區體育圖像構圖技法更突出縱深空間。德陽出土的伍伯圖像和四騎吏圖像,圖中形象上下平行排列,鳥瞰透視法將視覺點提高,表現縱深空間中多層次的排列關系。在仙人六博圖中,雙方中間的棋盤則采用不同角度的鳥瞰透視,將棋盤上內容展現畫面之間。富川石棺射獵圖像上,騎吏與騎吏之間的距離表達出畫面遠近關系,畫面視覺點落于中間在涉獵的貴族騎吏。并且通過形象大小來表述遠近關系,在視覺點之外的騎吏明顯小于他。在畫面中,上下位置關系就轉化為遠近關系。再如四川樂山麻浩一號崖墓出土的垂釣圖中,魚的形象在釣魚者方位之上,通過上下縱深來表達透視關系。
在巴蜀漢畫體育圖像中構圖往往有兩種甚至三種表現形式并用于同一個畫面上。透視法不統一造成視覺矛盾。成都羊子山一號墓是東漢時期的一座磚石墓,畫面內容豐富,表現形式多種,透視法不統一。圖像內容和圖像留白間空隙將畫面分為三個部分,圖中奏樂者和觀舞者使用底線橫列法和底線斜視法,但表演者使用鳥瞰透視法來表現,圖中多個體育項目分上下兩行排列。整個畫面錯落有致布滿畫面而不顯混亂。采用多視點構圖,克服時空觀念,觀者、表演者、奏樂者、三者不同方向視覺點呈現一幅場面宏大享樂的宴樂圖。
4" 結" 語
漢代巴蜀地區體育圖像內容繁多,包含弋射、射獵、漁獵、垂釣等等。但并未從生產生活中分離,同軍事、娛樂、社會緊密相連,對于豐富巴蜀人們的精神生活,增強體質具有積極意義。水上運動圖案呈現了巴蜀獨特的地域風貌,散點式構圖使畫面由二維空間向三維空間調度,畫面中的上下關系也蘊含著空間中遠近關系。形象生動的體育形象展現了巴蜀漢代高超的刻畫技藝,豐富的體育活動反映了漢代巴蜀地區體育文化面貌。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巴蜀漢畫中的體育活動在現如今得到延續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崔樂泉. 《圖說中國古代體育》[M].西安:世界圖書出版社西部有限公司,2017:102.
[2] 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漢畫像磚[M].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
[3] 龔延萬,龔" 玉. 巴蜀漢代畫像集[M].河北:河北新華印刷,1998.
[4] 信立祥. 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81.
[5] 顧" 森. 秦漢繪畫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247.
[6] 朱俊全,李國紅. 從南陽出土的畫像石看漢代軍事體育活動[J].體育文化導刊,2008:121~122.
[7] 曹景川. 中國古代競技體育活動及其表現形式[J].成都體育學院報,2008:45~49.
[8] 黃雅峰. 漢畫像石畫像磚藝術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20~142.
[9] 奏立凱. 漢代西南體育地理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3.
[10] 陳樂樂.《愉林地區東漢畫像石體育圖像探析》[D].陜西:陜西師范大學.2015.
[11] 巫" 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M].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5:61.